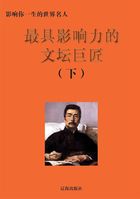艺术不愿意让人塞住嘴巴,钉上镣铐,牵着鼻子走;它高喊道:前进!它要放你们到诗歌的大花园里,那里没有禁果!
1830年以后,雨果除了写小说、诗歌之外,他还相继创作并上演了《国王取乐》《吕克莱丝·波基亚》《玛丽·都锋》等七个剧本。
雨果之所以如此钟情于戏剧,一是因为雨果的经济负担很重。他们全家每月要五百法郎的支出,雨果的哥哥欧仁因精神失常长期住院治疗,其住院费及治疗费也是由雨果负担的。
另一个原因雨果钟情于戏剧的,是他认识到戏剧对群众的影响最直接。七月革命以后雨果对社会,对政治越来越关注,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他总是希望牢牢地占据着戏剧舞台。
雨果的创作已经日趋成熟。然而,正因为日趋成熟,他的心理定势产生了动摇。艺术上的成就已经不能满足他的欲望。
在雨果早期的作品中,人们最为关注的往往是那些词藻优美的颂歌和抒情诗,仿佛他仅是一个唯美主义者。这当然是一种误解。实际上,雨果是一个非常入世的人。童年的不如意,少年的坎坷,青年的磨难,使他对政治有一种天生的敏感。他希望脐身于上流社会的政治生活,应该说是题中应有之义。
雨果极想脐身于那些治国安邦的伟人之列。他的榜样夏多勃里昂曾任法国贵族院议员、大使、外交部长。这正好是他今后希望走的光明大道。只是在路易·菲利普时代,一个作家想获得法国贵族院议员的尊贵头衔,必须首先是法兰西学士院院士。
1836年至1840年这五年,是雨果在文坛继续大踏步前进的五年。这种大踏步前进的态势,即使是那些对浪漫主义切齿痛恨的老学究,也不能再视而不见。
雨果的创作已经日趋成熟。然而,正因为日趋成熟,他的心理定势产生了动摇。艺术上的成就已经不能满足他的欲望。颂唱绿叶、太阳和亲爱者,虽然是一件赏心悦目的事,但一种新的渴望却更使他心驰神往。
他渴望成为“精神领袖”!他渴望在那些影响人民思想意识的人物中占有一个席位!他渴望能成为像他的老师、法兰西贵族、大使、外交部长夏多布里昂那样的人物!
在雨果早期的作品中,人们最为关注的往往是那些词藻优美的颂歌和抒情诗,仿佛他仅是一个唯美主义者。这当然是一种误解。实际上,雨果是一个非常入世的人。童年的不如意,少年的坎坷,青年的磨难,使他对政治有一种无生的敏感。
早在《克伦威尔》和《欧那尼》上演时期,雨果和他的朋友们虽对法兰西学士院进行过一些指责,但他对文学界过于了解,不认为法兰西学士院会因他们对那些才干的攻击而耿耿于怀。
从1834年起,雨果雄心勃勃,为自己订下的第一个目标便是进入法兰西学士院。
为此,他以顽强的意志发动了冲锋。圣佩韦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雨果想当院士。他关心此事;他郑重其事地与您谈论此事,一谈就是好几个钟头。当他和您谈学士院时,会心不在焉地把您从圣·安托万林荫大道带到马德莱娜路。雨果一旦有了打算,便会全力以赴去为之奋斗;于是,人们就听到他思想上的重型装甲骑兵、大炮辎重以及他的暗喻从遥远的地方开到。”
圣佩韦专门写文章对雨果进行了冷嘲热讽式的“赞扬”。雨果不想理睬。雨果是一个意志坚定的人,他认准了的“制高点”,那是一定要爬上去的!
法兰西学士院共有四十个院士,并且都是终身院士,因此替补的机会是相当少的。1835年,著名作家夏多勃里昂曾对雨果说:“研究院本身无足轻重,尤其对你来说,但为你打开政治途径,还是有其重要性的。”雨果显然是听进了这个话。
但是,法兰西学士院作为法国文学艺术界的最高圣坛,可不是谁想进就可以进的。除了造诣,更重要的是机会和人缘。学院只有固定的院士名额,只有当院士“缺额”的时候才进行补选。
而且文学不是自然科学,它不是一加一等于二,它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同一个作品,喜欢的可以说它是“天才创造”,不喜欢的也可以指斥它是“胡编乱造”,而且都可以引经据典、头头是道。因此,院士的补选,人缘成了很重要的因素。
1836年2月,法兰西学士院院士列昂子爵去世。根据“遗缺即补”的原则,学士院决定组织选举。
是梅尔西爱·赴巴迪,一个昙花一现的滑稽喜剧作家当选了。雨果不无伤感地说:“当初,我以为必须经过艺术之桥才可以进入法兰西学上院。我想错了,照这样看来只需迈过新桥便可入内。”
1836年11月,雨果又进行了一系列新的奔走。但这一次,泰奥多尔·帕维在给他兄弟维克多·帕维的信中又作了悲观的预测。
实际上,虽然法兰西学士院的两位举足轻重的人物拉马丁和夏多勃里昂都投了赞成雨果的票,但获胜者还是米涅。
德尔非娜·盖说:“事先若权衡一下选重雨果也许可以当选。遗憾的是,人们开初太乐观了。”
竞选受挫并没有使雨果灰心丧气。他又恢复了正常的生活,甚至比往常更加的关心他的几个孩子。
1837年3月5日,备受精神折磨的欧仁去世,终于得到了最后的解脱。
按照西班牙贵族的封赐习惯,雨果自然地取得了子爵的爵位。这个西班牙爵位虽然已经名不副实,但阿黛尔却看得很重,自此之后,她的签名一律变成了“雨果子爵夫人”。
雨果打不起精神。他念念不忘的还是那个法兰西学士院院士的宝座,因为他觉得,法兰西学士院就像希腊神话中的奥林匹斯山,此生此世,他是无论如何也要登上这座高峰的。
1839年,一位院士去世,机会又来了。这回的主要竞争对手是王朝正统主义演说家贝里页。雨果有皇室作靠山,过去对他一直持反对态度的检查机构转而支持雨果,因此,他当选似乎没有太大困难。
经过七轮角逐,仍然没有一个人能得到法定多数。选举只好推迟到三个月之后。
1839年12月31日,又一位院士突然去世,法兰西学士院又空出了一个位子。于是,1840年2月20日,学士院又举行了补选两位院士的双重选举。
结果又令人失望。在参加选举的31人中,有30票选莫连伯爵,有29票选弗鲁兰,雨果又一次名落孙山。
1837年,出现了一个转机,雨果认识了奥尔良公爵。
奥尔良公爵是所有期待自由政策的人的希望。雨果在替一个老教授求情帮助时,并非没有献媚之态。他说道:“亲王殿下,您会接受一个陌生人为另一个陌生人做祈祷吗?”
雨果当即得到了应允。于是一首感恩访问使导致了亲王和诗人后来的密切联系。
路易·菲利普为庆贺长子结婚,在凡尔赛宫的明镜长廊举行宴会之日,雨果也受到了邀请。起先,雨果表示不愿意去。出席一个有1500人的宴会,似乎并不显得十分荣耀,反倒有点叫人厌烦。
此外,由于国王长时期对待大仲马冷淡,拒绝邀请他。雨果说,不邀请大仲马,他也不会到。奥尔良公爵亲自出面,请求重新宠幸大仲马,由于公爵坚持,终于获胜。由于没有宫服,雨果和大仲马穿一身国民自卫军的制服,在凡尔赛宫遇见了装出贵族气派的巴尔扎克。
雨果并不为出席了宴会后悔。他被安排与奥马尔公爵同桌。国王在宴会上说了很多赞扬他的话。奥尔良公爵的妻子是一位学识渊博,心灵高尚,容貌美丽,胸襟坦豁的公主。
她对雨果说,见到他很高兴,并说她平日在和德·歌德先生交谈中常常提到他。她能背诵他的许多诗,她特别喜欢以“那是一座质朴的教堂,有着扁圆的拱顶……”开头的那首诗。
这位年轻美丽的德国公主,从16岁起就怀着酷爱的激情,开始攻读法国文学。她的愿望,是到巴黎,她崇拜的诗人,是维克多·雨果。
她还对雨果说:“我参观了‘您的’巴黎圣母院。”雨果当然很希望取悦这位显贵的主人,并且确实也如愿以偿。
婚宴三个星期后,雨果被委任为荣誉勋位团的军官。亲王的仆人给王宫广场的雨果送来了一幅带有浪漫色彩的画《依乃·德·卡斯特罗》。上面写着:“赠给维克多·雨果先生——奥尔良公爵暨夫人1837年1月27日。”
这样,雨果成了这位法国未来王后的诗人。在马尔桑宫,不论是星期三的正式集会,还是被人们称之为“壁炉集会”的亲近人的小聚,每次都少不了他。在这个亲近圈子里的人常常互相打听:“您明天去参加‘壁炉集会’吗?”
在集会上,他们总能见到雨果。雨果向比他小8岁的公爵说,诗人是上帝派到亲王身边的代言人。
奥尔良公爵,把雨果当成了可以一吐肺腑之言的朋友。有一回交谈中,公爵同雨果说道:“最近怎么没有看到你的剧本上演?”
雨果告诉公爵:“我没有自己的剧院,因为法兰西喜剧院都被死人统治着,而圣马丁门剧院又被蠢人占领着!”
公爵生气了,一个最优秀的剧作家,竟然没有剧院可以上演自己的剧本,这太说不过去了。他立即给文化部长写了一封信,要求授予雨果“拥有自己剧院的权利”。
王位继承人的指示得到了很好的贯彻,雨果有了自己的阵地,它被叫作“文艺复兴剧院”。
大仲马和雨果又将此事托给了一个叫做安泰诺·若里的报社经纪人去经营。雨果为此还写了一个诗剧来庆祝剧院的开张。
1840年6月7日,列迈斯埃先生撒手人寰,而就在1841年1月的选举中,雨果终于以17票对15票的微弱优势,取得了入驻法兰西学士院的通行证。
这一回,投票支持雨果的有夏多勃里昂、拉马丁、维尔曼、诺弟埃、库佐、米涅。政治活动家梯也尔、莫连等也投了他的票。
接纳仪式盛况空前。知名人士中有吉拉尔丹夫人、路易丝·高兰夫人、梯也尔夫人,以及一大群女演员。
十年来,亲王们第一次光临法兰西学士院。法兰西学士院的常务秘书维尔曼在马扎兰宫门口迎候奥尔良公爵暨夫人,这天,夫人戴着一顶衬着粉红色里布的白帽子,显得格外漂亮。
雨果进入法兰西学士院时真有一种帝王气派。棕色的头发精心梳理过,光溜溜的,衬出金字塔型的前额,一络发卷里落在绣着绿花的衣领上。微凹的小黑眼睛、闪现前抑制的喜悦。
仪式开始了,雨果微笑着向观众挥手致意,而后便口若悬河地发表了就职演说。
雨果满怀激情,观众也如醉如痴。虽然观众们早已从书本上领略了作家的才华,但那么近距离地倾听他的声音。观赏他的手势,仍然使人们感到欣喜与激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