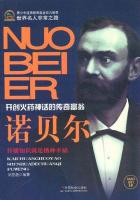他停顿了一下,然后说:“好的。”
半个小时后,我到了他家,J.P.正站在门阶处等我。
“真的很感激你同意见我,我真的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去了。”
“你需要什么?”
“我想,我们能不能,嗯,先了解一下彼此?”
他笑了。“听着,”他说,“我真的不大擅长扮演神父的角色。”
我点了点头,自嘲地笑了笑,说:“是的,是的,但是或许你可以给我安排一些任务?生活的任务?阅读的任务?”
“就像一个导师那样?”
“是的。”
“其实我也不大擅长扮演导师的角色。”
“噢。”
“聊天、倾听、友谊和陪伴—这些是我能够做的事情。”
我皱了下眉头。
“你看,”J.P.说,“我的生活就跟常人一样糟糕—或许更糟糕。我在引导方面或许真的不能提供很多帮助和意见,我不是那种类型的牧师。如果你想要一些建议的话,我很抱歉,但是如果你需要一个朋友,或许我可以胜任。”
我点了点头。
他打开家门,问我要不要进去。但是我却反问他愿不愿意跟我去兜兜风,因为我在开车的时候头脑会更清醒。
他伸长了脖子,看到了我的白色克尔维特就像一架小型私家飞机一样停在他的私人车道上。他脸上的光彩减淡了几分。
我载着J.P.在拉斯韦加斯四处闲逛,沿着霓虹灯闪烁的长街开来开去,然后开进了环绕着市区的盘山公路。我给他展示了克尔维特的性能,将油门踩到底,然后,向他敞开了心扉。我告诉了他我的故事。虽然我说话颠三倒四、毫无逻辑,但是他却能像佩里一样可以用流畅恰当的语言复述出来。他能明白我内心的矛盾,并且化解了其中的一些。
“你还是一个生活在父母羽翼下的孩子,”他说,“但同时你已扬名世界了。这是一件很艰难的事。你想要自由地展现你自己,想要发挥你的创造力和艺术性,但是每次都得不到认同。这是非常痛苦的事情。”
我对他说,人们都认为我赢得并不光彩,认为我从来没有打败过任何优秀的选手,我一直都是侥幸而已,我一直都有祥云笼罩,这让我遭受了巨大的打击。他说:“其实你一直都是在逆流而上,从来都没有搭过顺风车。”
我笑了。
他说:“挺奇怪的吧?有一群陌生人以为他们很了解你,并且毫无理由地支持你;而另外一群人却以为他们才真正了解你,并且无缘无故地恨你—而他们谈论的那个‘你’对于你来说都很陌生。”
“更反常的是,”我跟他说,“一切都围绕着网球转,我痛恨网球。”
“哦,是的,但是你并不是真的痛恨网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