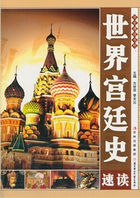凶犯死后的第三天,一辆旅行马车载着奥立弗向他出生的那个市镇急行。同车的人有梅里太太、露丝、贝德温太太和好心的大夫。布朗娄先生同一位不知姓名的人坐在后面的一辆驿车里。
马车到了镇上。奥立弗看到,索厄伯里的店面还是老样子,只是规模和气派比他记忆中要小些。那些熟悉的铺子和房屋都还在,当初他可是跟每一家都多少有些联系的。停在小酒馆儿门口的是甘菲尔德的驴车,还是原来那辆。啊,到济贫院了,这是他童年时代的监牢。那些阴惨惨的窗户,仍一如当初,皱着眉头悲哀地看着街面。他们驱车直抵镇上首屈一指的旅店。格林维格先生已在此等候他们了。他笑容满面,和蔼可亲,竟一次也没有表示要把自个儿的脑袋吃下去。晚饭已经摆好,卧室也已收拾停当,一切都如施了魔法一般妥妥帖帖。
经过半小时的忙碌之后,他们又像一路伴随而来的那样沉默和拘谨了。布朗娄先生没与他们共进晚餐,而是自己一人呆在房间里;另外两位绅士好像心事重重,不断地出出进进,即便他们偶尔逗留片刻,也只是在一旁交谈。所有这些都使得不知情的露丝和奥立弗异常紧张。
已经9点多钟了,他俩认为当晚是不会再发生什么事了,不料就在这时,洛斯本先生和格林维格先生走了进来,后面紧跟着布朗娄先生和一个男人,奥立弗见到此人,差点儿失声尖叫起来。他就是奥立弗在集镇上撞见,后来又与费根一起在他的小房间窗前张望的那个人——也就是他的哥哥蒙克斯。蒙克斯即使到了这个时候,仍怀着难以扼制的仇恨狠狠地瞪了这个孩子一眼,然后才拣个靠门的地方坐下。
布朗娄先生拿着许多文件走到露丝和奥立弗身边的桌子旁。“这是一个叫人难过的事情,”他说,“但这些在伦敦当着好几位绅士签了字的声明的要点必须在此重申一下。我其实很不愿意让你再次丢脸,但我们必须听你亲口复述一遍,这你也是知道的。”
“请讲,”那人催道,“快点儿,别把我拖在这里。”
“这个孩子,”布朗娄先生一手拉住奥立弗,另一只手抚着他的头顶说,“他是你的异母兄弟,是你的父亲、我的好友埃德温·黎福德的非婚生儿子,他可怜的母亲,年轻的阿格尼丝·弗莱明一生下他就死去了。”
“是的,那是他们的私生子。”蒙克斯说时对那个战栗不已的孩子怒目而视。
“你如此指责的人,”布朗娄先生厉声道,“早已到了另一个世界,这区区非难已丝毫无关紧要了。这种字眼除了能让你自己蒙受耻辱,对任何其他活着的人都毫无损毁。算了,就不提了。他是在这个镇上出生的,是不是?”
“在本镇的济贫院里,”他语调阴沉地说,“这里不都已经写清楚了嘛。”他不耐烦地指指那些文件。
“我要你在这里再说一遍!”
“那你们就听着吧!”蒙克斯说,“他的父亲病倒在罗马之后,早已跟他分开的妻子,也就是我的母亲,因看在他的财产的份上从巴黎赶去。因为据我所知,我母亲对他并无感情可言,他对我母亲也是如此。他根本没怎么认出我们来,他神志不清,一直昏迷,第二天就死掉了。他的写字台抽屉里有些文件,看那签字的日期,其中两份是他生病的当天晚上写的,文件封套上写着你的名字。”这时蒙克斯转向了布朗娄先生,“给你写的就短短几行;封套上还有附言,说要等他死后再转交。文件的一份是给那个叫阿格尼丝的姑娘的信,另一份是遗嘱。”
“信上写的什么?”
“你说那封信?就一张纸,涂了又涂,改了又改,有忏悔,有祈求上帝保佑那姑娘的祷告。他曾编了一套假话骗那姑娘,说他有难言之隐,眼下妨碍他们俩结婚,以后再向她解释这是怎么回事。那姑娘对他深信不疑,并一直痴心地等着他,可她信过了头,竟失去了谁也无法还给她的东西。那时候,她只剩几个月就要分娩了。在信中,他告诉她,要是他能活下来,他会如何去做以保全姑娘的名节;万一他死去的话,恳求姑娘不要诅咒他而让他死后蒙受恶名,不要以为他们的罪孽会给她或他们的孩子招来不幸,因为所有的罪责都应由他来承担。他还向姑娘提起他有一天曾送给她的一个小金匣子和一枚戒指,戒指上刻着她的名字,旁边留有空隙,好在那上面刻上他希望有朝一日献给她的姓氏;他还恳求她把小金盒保存起来,像从前一样挂在她的胸前。后面的是些疯话,好像他精神错乱了一样,净是些颠三倒四、翻来覆去的话。我现在都还相信当时他脑子是出了毛病。”
布朗娄先生又问:“遗嘱呢?”
蒙克斯没做声。
“遗嘱和信的意思大致相同,”布朗娄代他说了,“他谈到他妻子给他带来的不幸,还谈到你性情顽劣、不服管束、心肠狠毒、品行下流,小小年纪就很邪恶。在遗嘱中,他给你和你母亲每人留下年金800英镑。他大部分的财产分成相等的两份——一份给阿格尼丝·弗莱明,另一份给他们的孩子,要是这孩子能够顺利地出生并到达法定的成年期的话。若是女孩,这笔钱将无条件地被继承;如果是男孩,那就要符合一个条件:他在到达法定年龄之前不能有不光彩的、下流的行为。他之所以立下这样的遗嘱,他自己说是以此表示对孩子母亲的信任,也是为了重申自己的信念,这就是:他相信孩子一定会继承她母亲善良的心地和高尚的品质——这个信念将随着死亡的迫近而愈发的强烈。那么就是说,只有万一他的期望落空的时候,这笔钱才有可能归你;也就是说,两个儿子同为一路货色的情况下,他是会让你获得优先继承的权利的。
“我母亲,”蒙克斯提高了声音说,“把这份遗嘱烧毁了,这是随便哪个女人都会干的。信也始终没发出去,我母亲把信和其他的证据保存起来了,让他们这桩道德败坏的丑事永远都有证可查。她把那件事告诉了姑娘的父亲。姑娘的父亲遭此羞辱之后便立即带了两个女儿逃往威尔士一个偏僻的地方,改名换姓,他的朋友们也无从知道他的下落和隐居之地。不久,有人发现他已死在床上。原来,在这几周以前,那姑娘偷偷地离家出走了,她父亲就徒步寻遍了附近的小镇和村落,但没有结果。他回去的当夜便深信女儿是为了掩盖自己和父亲的耻辱自杀了,所以他就心碎而死。”
沉默了片刻,布朗娄先生才接起了话头。
“几年之后,”他说,“爱德华·黎福德,你的母亲来找过我。你才18岁就偷了母亲的珠宝和现款离开了她,逃往伦敦,在那里跟卑劣低下的流氓、恶棍鬼混了两年。你母亲患有一种痛苦的不治之症,身体愈来愈坏,她想在死去之前把儿子找回来。于是她派人四处寻访,好长时间都杳无音讯,后来总算找到了,你就跟母亲一起回到了法国。”
“她死在那里,”蒙克斯说,“拖了很久才死的。临终时,她把这些秘密都告诉了我。她完全用不着叮嘱我的,其实我早已继承了她的仇恨。她可不相信那姑娘是寻了短见,也就此没了那个孩子,她认为一定有个男孩生下来了,而且还活着。我向她发誓,只要见到他的形迹,我一定把他给找到,让他片刻不得安宁,我母亲没有料错。他终于叫我给撞上了……”布朗娄先生转过头来问蒙克斯:“那个小金匣和戒指呢?”“我跟你说过那一男一女,我就是从他们那里买下的这两样东西;那是他们从一个看护妇那里得来的,看护妇是从死人身上偷来的,”蒙克斯回答时始终耷拉着头,“东西结果怎样了,你是清楚的。”
布朗娄先生向格林维格先生略一点头,那位先生便异常敏捷地走了出去,眨眼间带回两个人,前面是邦布尔太太,后面是她那不大愿意进门的丈夫。
“莫非我眼睛花了不成?”邦布尔装出无限欢欣的样子,“那不是小奥立弗吧?哦,奥立弗呀!你不知道我曾为你多伤心哪……”邦布尔太太道:“少废话,蠢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