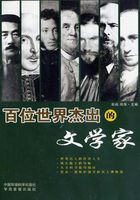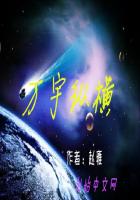“教友们,肃静啦。我叫杜遵道,是我们教主的忠实信徒。我先来说说今天聚会的根由。”他清淸嗓子,提高了声音淸晰地说道,“教友们!这些年,为什么我们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为什么我们的妻女动不动被人奸污?为什么黄河决口,淮水倒流,山崩地裂,蝗旱频生?为什么日月无光,到处是黄沙黑风?这都是北国鞑子的罪过!鞑子欺压咱们汉人,乱我中华,已经是天怒人怨。胡儿不灭,民无生理,国无宁日!”说到这里,他吟出了一首诗,“‘云雾苍茫各一天,可怜西北起烽烟。东来暴客西来盗,还有胡儿在眼前!’教友们,这是宋代邵康节写的诗。邵先生是上知八百年,下知八百年的活神仙。他所说的话,正应了眼前的光景。我们再也不能听凭鞑子的欺压凌辱。我们要听从教主的号召,高举义旗,拿起刀枪,扫暴客,荡盗贼,杀尽胡儿!带领大伙成大事的,就是我们三个人。”讲话人先指指站在椅子旁边的人,一字一句地说道:“这位是刘福通大哥,他是宋代名臣刘光世的嫡传后人。坐在上面的那一位,我们的教主——韩山童,乃是当年被鞑子掳去的宋徽宗皇帝的八世孙。为了找到真正的教主,本人费尽了心机。话要从头说起:有一天,弥勒佛尊托梦给我,命我寻访宋朝皇帝的嫡传子孙,辅佐他完成抗元复宋大业。我扔掉元朝的官儿不做,四处察访,历时三载,终于找到了弥勒佛转世的真主、大伙企盼几十载的明王。这是鞑子寿命将绝,大宋朝将兴的吉兆。我们有了韩山童教主的引导,驱除北国鞑子,恢复大宋江山,指日可待。教友们,我们的苦日子眼看到头啦。”
杜遵道曾作过元朝的枢密院橡史,因为与上司发生矛盾,愤而辞职。他不仅是一位文牍高手,而且才华横溢,口若悬河。听到他铿锵有力的讲演,宛如往油锅里注人了冷水,会场顿时沸腾起来。此起彼伏的呼喊声,打断了他的讲话。
“好哇——咱们有救了!”
“有了弥勒佛教主的引导,何愁小鞑子不夹着尾巴滚蛋!”
“不能让小鞑子逃掉!说干就干,今天咱们就动手杀狗日的!”
山呼海啸,地动山摇。春雷般的欢呼声,滚过会场,直冲霄汉。等到欢呼声低落下去,杜遵道继续说道:
“教友们,大伙的热情十分可嘉,但是杀鞑子的时辰还没有到。今天我们到这里来是要献诚心、祭义旗,拜告天地佛祖,宣告红巾军成立。后天,是癸丑日端午节,正晌午时,才是我们举义的吉利时刻。到那时,我们各路弟兄,要一齐出击,英勇奋进,直捣幽燕,一举把鞑子赶出中国!”
说到这里,杜遵道朝台下一挥手,立刻有人牵来了黑牛白马。人们用绳索将两头牲捆绑好,两条大汉,分站在牲口的前方,台上一声令下,两人弯腰挥刀,照准脖颈下方,猛刺下去。顿时,鲜血像喷泉一般涌了出来。人们用木盆将血接了,送上台去。有人将备好的高粱酒,掺上鲜血,献给三位领袖。三人饮罢血酒,随从拿来一面杏黄大旗,将四角用鲜血浸红,然后用长杆挑起,树在高台的前方。大旗上写着两行大字:
虎贲三千,直捣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
随着大旗的猎猎飘动,人们的欢呼声山呼海啸般,一浪高过一浪。
正当人们沉浸在节日般的欢快之中,白鹿庄村北的大道上,忽然腾起一股烟尘。烟尘越来越高,接着传来杂乱的马蹄声。刘福通站到高处一看,—彪元兵的骑兵飞奔而来。分明是有人告了密,元兵的骑兵才不迟不早,恰好在此时杀来。会场立刻乱成了一锅粥。人们惊慌失措,拥挤呼喊。刘福通急忙回到台上,命令人们准备战斗。可惜,已经晚了,元兵已经冲进了场院—面喊着“杀妖徒”,一面猛刺猛砍。眨眼的工夫,场院上尸体横陈,鲜血四流。韩山童被活捉,杜遵道和刘福通等人,杀开一条血路冲了出去。一场声势浩大的起义,被扼杀在摇篮之中……
正如地心之火,一旦窜出地面,便难以扑灭。白鹿庄聚义虽然失败,但刘福通、杜遵道等突围出去以后,并没有停止活动。他们在武安山深处,找到了逃到这里的韩山童的妻子杨氏和儿子韩林儿。他们尊封韩林儿为“小明王”,在颍上县重树义旗,很快发展到十几万人,一举占领淮河上游十多个县城。由于他们头裹红巾,烧香拜佛,又被称为“香军”。短短数月间,北起黄河,南越长江,到处跃动密红巾军的身影。义军四起,一派烽火燎原之势。甚至,只有几百人的小股队伍,也能纵横驱驰,如人无人之境。芝麻李等八个人,竟然夜闯徐州,天明坐衙,不几天聚众十余万……
元朝派出几十万大军,奔逐于黄淮之间进行剿灭,但统兵者沉湎酒色,士卒但务剽掠,面对嚣嚣红巾军,竟然畏葸趑趄,屡战屡败。
大元帝国的末日,已经为期不远了。
墓是统治者自己掘成的。元朝走向没落的根本原因,是残暴的统治和贪婪地掠夺。
蒙古人不仅残酷地统治和压榨掠夺,而且进行等级压迫。他们将治下的子民,划分为四个阶层:蒙古人,色目人(中亚归降的民族),汉人和南人。蒙古人是贵族,色目人次之,汉人和南人则是下等民族,被贱称为“汉子”和“蛮子”,可以任意进行欺压盘剥和杀戮。元朝各级政府的正职,汉人不得染指,汉人军官,不得过问军机秘密、阅兵籍、知兵数。科举考试也有贵贱之分,蒙古人、色目人只考两场,汉人南人不仅要考三场,而且题目难度大得多。可到了授官的时候,却反了个个儿:蒙古人、色目人官吏的荫叙和升迁,比汉人优越得多。
除了政治上的不平等,在法律上,对汉人也极尽歧视之能事。蒙古和色目贵族作奸犯科,只能由“大宗正府”处理,而汉人犯法,则由普通府衙处置。蒙古人打汉人,汉人不得还手,打死汉人,只判处从军出征或罚交烧埋银。而汉人打死蒙古人,则要从严断罪。为了镇压汉人和南人的反抗,不但建立了严格的社甲制度,而且彻底解除汉人的武装。南人在军中,尺铁寸杖不得在手。民户的马匹要人官,私藏甲杖的要处死。连各级府衙拥有的弓矢数目也严加限制:路、府、州县,分别是十副、七副和五副。汉人不准打猎,不准练习武艺,不准聚众祭祷,集市交易,甚至不准汉人学习蒙古、色目文字……
蒙古灭金以后,圈占大量土地作牧场,动辄上千顷甚至十余万顷。灭宋以后,没收的官田,则赏赐给蒙古王公贵族以及佛寺道观。以致大批自耕农变成了悃户。碰上水旱虫灾,农民只有逃亡的份儿。元朝政府又下令不准逃亡,已经逃出者,立即押解还乡。不仅如此,蒙古统治者还大肆“驱口”——掠夺人口。被“驱”的人,等同于奴隶,所生子孙,世代为奴。由于人口惨遭杀戮,大置奴隶被占有,大大限制了人口的增长。元初,国内有人口五千八百八十三万,历经半个多世纪之后,人。居然没有增加。
蒙古统治者一方面对汉人、南人极尽摧残压榨之能事,另一方面则腐化堕落,争权夺利,自相残杀。从元成宗到元顺帝,二十几年间,换了九个皇帝。仅天顺元年(1328)至元统元年(1333)的短短六年之间,就换了六个皇帝。在用人方面,不问能力大小,只看贿赂多少。买官鬻爵,大行其道。只要皇帝喜欢,一无所长的人也可以做到平章、参政甚至丞相。让这样一些寡廉鲜耻的人掌了权,自然是贪污成风,无恶不作。
朝廷和官府的勒索搜刮,更是名目繁多:下属拜见上司,要有“拜见钱”,平时索要,叫“撒花钱逢节要“节钱”,过生日要“生日钱”,办事要“常例钱”,迎送要“人情钱”,发传票拘人要“赍发钱”,打官司要“公事钱”。敛得钱多叫“得手”,买得肥缺叫“好地分”,补得美差叫“好窝窟”。甚至肃政廉访官员巡查各州县,也带上“库子”(管钱的吏役)。检钞称银,争多论少,如同市场交易。有人写诗嘲曰:
解城一金并一鼓,迎官两鼓一声镑;金鼓看来都一样,官人与践差不多。
官吏盘剥穷凶极恶,朝廷害怕激起民变,有时也派大员到地方上宣抚。无奈,宣抚者同样是贪婪受贿,官官相护。无可奈何的百姓,只能编几曲民谣,一吐胸中的积愤:
本使来时,惊天动地;奉使去时,乌天黑地。官吏们欢天喜地,百姓们啼天哭地。
奉使宣抚,问民疾苦,来若惊雷,去若败鼓。
九重丹诏颁恩至,万两黄金奉使回。
做过地方官的刘伯温,曾写过一首诗描述元朝官府淫毒贪掠,官逼民反的现状:“破廩取菽粟,夷垣劫牛羊。朝出系空嚢,暮归荷丰囊。厂男逃上山,妻女不得将。稍或违所求,便以贼见戕。负屈无处诉,哀号动穹苍。斩木为戈矛,染红做衣裳,鸣锣撼岳谷,聚众守村乡……恨不斩官头,剔骨取肉尝。”
有一阕流传甚广的《醉太平》小令,更是通畅明白:“堂堂大元,奸佞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军万千。官法乱,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愚贤,哀哉可怜!”
还有一首民谣,说得更露骨:“天遣魔军杀不平,不平人杀不平人。不平人杀不平者,杀尽不平方太平。”
“不平人”再不揭竿而起,只有死路一条了。
经过四年流浪的朱重八,熟知民间疾苦和蒙古人的恶行。在催租和采买的时候,又经常听到各地白莲教蜂起的消息。他知道,天下已经大乱。大浪淘沙,那些发难者,品德才能,天差地异,正所谓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只有韩山童,使他最感兴趣。重八在淮西一带流浪时,对于这位弥勒转世的教主,就怀着深深的敬意。而目睹韩山童传教的人,更将韩山童得到教民爱戴的细节,绘声绘色地向他做了描述。他打定主意,投奔韩山童,干一番大事业。
“娘的!时候到了,俺也该行动了。要不然,等到人家成了气候再动手,哪有碗热粥留给咱?”
朱重八想带上一批人投祿白莲教。先弄个小头目干千,焉愁尔后不发达?于是,他在和尚中暗暗串联。把在流浪途中所看到的民间疾苦,元军暴行,不厌其烦地向师兄们宣讲,动员他们跟自己一起出走,去参加红巾军,做一名驱逐鞑子的好汉。
“师兄们,如今群雄并起。尔后的天下,说不定谁是主宰。我们何不趁著这大好时机,为自己争个好出路呢?只要咱们时气好,说不定也弄个出将拜相、封王封侯昵。怎么?难道王侯将相是天生的神种?不!乱世出英雄,除了那些吃现成饭的阿斗,哪个得势成气候的人,不是真刀真枪拼杀出来的?莫非你们甘心在皇觉寺吃一辈子素斋,敲一辈子木鱼铁磬?那外面的花花世界一辈子也看不到,荣华富贵永远也没有咱们的份儿。那也算是做了一辈子人?等到百年之后,能跟西天佛祖说,此生过得有滋有味,尽了拯救众生脱离苦海的责任?”他凝视着低头沉思的师兄们,一派美好前程唾手可得的神气,“想想吧,师兄们。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再犹豫下去,俺甩手一走,你们想找个领路的人,都来不及了。”
在重八的说服下,好几个出家人动了凡心,决定跟着他悄悄出走,轰轰烈烈干一场。
重八正在得意,高彬长老派人把他叫了过去。
一见高彬绷紧的脸色,重八的心里不由“咯噔”一下。心想,莫非是在催租或者采买时出了什么娄子,惹得长老如此地不快?
怀着满腹狐疑,他来到高彬面前,深施一礼,垂手站立。小心翼翼地问道:“师父,你叫俺来,不知有何吩咐?”
高彬闭着眼睛说道:“吩咐倒没有。今天请你来,是想听听你的教诲。”“徒儿不敢。徒儿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还望师父多多指教。”
“老僧的教导,你能听得进去?”
“徒儿又不是小孩子,怎么会听不进师父的教导呢?”
“不错。你已经二十五岁,不是小孩子了。四年游方,又增加了许多
的见识。论说,应该知道什么是佛门弟子不该说的,什么是佛门弟子不该做的。”
“莫非,徒儿说了不该说的话?做了不该做的事?惹得师傅生这么大的气?”
“不是老僧生气,是你自己的作为太出格,为寺规佛戒所不容。”高彬睁开眼端详了一阵子,又重新闭上了眼睛,“我听说,这些日子,你经常跟师兄们宣讲什么鞑子邪恶,民不聊生之类忌语。可有这事?”
“有。俺确实把鞑子穷凶极恶、老百姓求生无路的惨状,跟师兄们议论过。不过,俺所说的,都是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的,一句也没有瞎说,怎么就犯了忌讳呢?”
“你认为,那些事情,只有你一个人看得明白?”
“既然都是至明至白的事,徒儿说说又有何妨呢?”
“思惠!你越说越出格了!莫非你在外面已经入了白莲教,成了邪教的信徒?”
“啊……不。俺可没人过什么白莲教!”他回答得咬钢嚼铁。
“就算你不是白莲教徒,你也忘记了自己是什么人!”高彬两眼一瞪,提高了声音,“你是个脱离凡尘、六根淸净的佛门弟子,怎么可以耳妄闻、舌妄摇、心妄思、念妄动呢?”
重八克制着不满,含糊地答道:“师父,俺知道啦。”
“光知道就行了吗?你心生邪念,四处乱说,已属越规违教,佛法不容。更不可恕的是,竟然撺掇餑心修行的人,脱离寺庙,去干那些妄开杀戒的罪恶勾当——简直不可饶恕!”
“师父,杀坏人能算是妄……”
住口!不准强词夺理,蛮横狡辩!思惠,今天我就听你一句话:你能不能翻然悔悟?你倒是说呀。怎么?知过不改?那,老僧就没有办法帮你啦!”高彬向后一靠,不再言语。
重八知道高彬的弦外之音,急忙躬身答道:“不,不。师父,徒儿能做到。”
“真的能做到?”
“当然能!”
“你可要心口如一。出家人慈悲为怀,先饶你这一遭。再不痛改前非,莫怨老衲无情,轻则削了你的差使,重则赶出佛门——你自己掂量着办吧。”重八连声应着,低头退了出去。
“既然出家人以慈悲为怀,老方丈为什么一点不痛惜老百姓,却跟鞑子穿一条连裆裤呢?是他胆子小,还是饱汉4、知饿汉饥?”一走出来,重八就在心里嘀咕,“操他娘,不知是哪个王八羔子奸细告了密?一旦弄明白啦,吃咱一顿拳头!”
不论是谁告的密,高彬的警告却不能不放在心里。饿肚子的难受滋味,!重八体会得最深。为了在行动之前,不丢掉一日三餐果腹的斋饭,他的宣传鼓动,只得先停下来。但他仍然抻长了耳朵,探听外面的消息。不久,重八就听到韩山童在祭旗时让元兵活捉了去,被活活烧死的噩耗。高楼失足,冷水浇头,他的一颗心,蓦地往下沉:
“糟啦,糟啦!韩教主一死,还有哪家红巾军是靠得住的呢?”
朱重八不想把自己的堂堂七尺之躯,交付给一个有勇无谋、无知蛮干的莽汉。别看他们今天自己封王封帅,手里有数万的兵马,没有统兵的谋略,能征惯战的将帅,保不住明天就会散伙溃败,成了光杆大王。他要谨慎选择投靠的主子。
正在这时,有人给他从濠州(今安徽凤阳)带来一封信。重八急忙跑到柴房里,拆开细读。这封写在一片旧桑皮纸上的短信,是他的街坊、童年时代的好友汤和写来的。潦草的字迹写道:
重八:我和徐达几个人,早已投靠了郭子兴元帅。郭元帅是杜遵道的部下,已经攻占了濠州城,鞑子奈何他不得。郭大帅对部下十分宽厚。当初我来投靠时,只带来十几个人,现在已经升到了千户,徐达也升了瓦夫长。看,咱们这些放牛娃,也是当官的材料!听说这几年,大哥一直没混出个好模样,至今还在破庙里受罪。如今天下大乱,能人出头。你赶快扔掉劳什子木鱼经卷,前来濠州从军。哨们一起杀鞑子,混个好前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