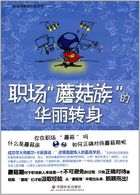一、胡适治学与为人
胡适甫从美国回来,就不断地推行他所信奉的“实验主义”。时人把“实验主义”叫作“实用主义”,因此多招误解,其实胡适自己说得非常明白:实验主义乃是一种“特殊哲学”,它包括了历史的方法与实验的方法,亦即任何一种制度或学说,必先就历史阐述其“必然性”,然后再以实验方法证实其“可行性”。明白这一层,才可以明白胡适问学从政的态度。所以除了学问之外,胡适还做官从政,做大学校长,担任驻美大使、驻联合国代表、国大代表、中央研究院院长,甚至差点还去参选总统,蒋介石也表示愿意做他的行政院长……这是近代学人中任何—个人者环曾有过的经历。
余英时特别指出,胡适之所以能成为中国文化转型时期的枢纽性人物,有两个关键因素:他有长期的精神和思想上的准备,并基于此有异常丰富的尝试。他作白话文学史、中国哲学史、小说考证以及科学方法,都是为了给中国学术开出新的机运。
在胡适的眼中,近2500年来的中国文学,最缺乏以及最不发达的就是“传记文学”。究其原因,在《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中,他这样说:“传记是中国文学里最不发达的一门。这大概有三种原因:第一是没有崇拜伟大人物的风气;第二是多忌讳;第三是文字的障碍。”
胡适不断地劝他的朋友们写自传,自己也身体力行,因为他相信,传记可以帮助人格的教育。所以在1953年1月12日的讲演中,他讲了自己读西方传记的感受:“近代新医学的创始人巴斯德(Pastur)的传记,是由他的女婿写的,也是一部最动人的传记。巴斯德是15世纪中法国的化学家……他一生最大的贡献也就在微菌的发现……这一科学家的传记,使我这个外行人一直看到夜里三四点钟,使我掉下来的眼泪润湿了书页。我感觉到传记可以帮助人格的教育。我国并不是没有圣人贤人;只是传记文学不发达,所以未能有所发扬。这是我们一个很大的损失。”因为,胡适还另外有一个思路,就是他主张通过传记来宣扬崇拜英雄的风气。胡适特意提到,近代中国历史上有几个重要人物,很可以做新体传记的资料。远一点的如洪秀全、胡林翼、曾国藩、郭嵩焘、李鸿章、俞樾;近一点的如孙文、袁世凯、严复、张之洞、张謇、盛宣怀、康有为、梁启超——这些人关系一国的生命,都被该有写生传神的大手笔来记载他们的生平,用绣花针的细密功夫来搜求考证他们的事实,用大刀阔斧的远大见识来评判他们在历史上的地位。
胡适一定知道自己是一个可以传世的人,所以他非常注意保存史料,而他的日记也因此被人们认为是写给别人看的,就像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但在我看来,写日记是一个好的习惯,他那么多的著述,我只买了《胡适文存》,却买了全套的胡适日记,我觉得这比他的一些学术成就还要重要,因为他的日记很细致地记录了平时的思考,其中含有很多细节。他平时搜集的很多数据也会时时记入日记,并且加上自己的分析。在他的日记中。不大容易看到情感的起伏,而无不是他的志业所在。例如中国新文化运动需要从哪些方面进行,需要哪些知识和行动,需要如何培养、训练,各种细节,需要的经费……在抗日期间,他甚至记下了日军军备的很多方面,例如日本军舰上火炮的口径……
从新文学的角度说,胡适有许多的倡导,比如在人名或地名的边上加一道黑杠。有一回他给章太炎写信,在章太炎名字的边上加了杠子,太炎很是生气,认为胡适怎么可以在自己的名字边上加杠子,可当他看到胡适的名字边上也有杠子时,心中才有些平和,说:原来他的名字也加了杠子。关于这一点,张爱玲还有回忆:“讲到加杠子,二三十年代的标点,起初都是人地名左侧加一行直线,很醒目,不知道后来为什么废除了,我一直惋惜。又不像别国文字可以大写。这封信上仍旧是月香。书名是左侧加一行曲线,后来通用引语号。适之先生用了引语号,后来又忘了,仍用一行曲线。在我看来都是‘五四’那时代的痕迹,不胜低回。”
胡适无疑是20世纪学术界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的学生唐德刚给他做过一个统计,说他差点就是体育中的“十项全能”,只差一项而已。这九个项目是:1.哲学思想,2.政治思想,3.历史观点,4.文学思想,5.哲学史观点,6.文学史观点,7.考据学,8.红学的艺术性,9.红学的人民性。
不管对胡适的评价高低如何,都不能不说胡适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重要人物。凡是见过他的人,都会有一些敬佩不由得不生出来。张爱玲在一次与胡适的相别时,这样写道:“我送到大门外,在台阶上站着说话。天冷,风大,隔着条街从赫贞江上吹来。适之先生望着街口露出的一角空镑的灰色河面,河上有雾,不知道怎么笑眯眯的老是望着,看怔住了。他围巾裹得严严的,脖子缩在半旧的黑大衣里,厚实的肩背,头脸相当大,整个凝成一座古铜半身像。我忽然一阵凛然,想着:原来是真像人家说的那样。
而我向来相信凡是偶像都有‘粘土脚’,否则就站不住,不可信。”这段形容,真好!张爱玲还说,当她去看胡适的时候,她的一个叫炎樱的朋友认为胡适并没有林语堂有名。于是张爱玲感慨:“我屡次发现外国人不了解现代中国的时候,往往是因为不知道五四运动的影响。因为五四运动是对内的,对外只限于输入。我觉得不但我们这一代与上一代,就连大陆上的下一代,尽管反胡适的时候许多青年已经不知道在反些什么,我想只要有心理学家荣(Jung)所谓民族回忆这样东西,像‘五四’这样的经验是忘不了的,无论湮没多久也还是在思想背景里。荣与弗洛伊德齐名。不免联想到弗洛伊德研究出来的,摩西是被以色列人杀死的。事后他们自己讳言,年代久了又倒过来仍旧信奉他。”这话倒是有远见的。
我读近代学人,都有不同的感受,读胡适的时候,心里却清明平易,这不仅是因为他的文风,而且可以从字面纸背看出他的为人。人们通常将他叫作“胡大哥”,仅此称呼就见他的平易近人,比如他对徐志摩等人的照顾,完全是大哥风度。有一次,《国文天地》的记者去访问胡适,张口就说:“大哥大”胡!您好!胡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礼貌,我又不是黑道老大“罗勿助”,怎么叫我大哥大?记者说:您不是胡博士吗?胡说:是啊!我一生得过36个博士学位。记者说:胡博士的英文DoctorHu,其音译岂不正是“大哥大胡”吗?胡说:正是!记者说:那么我称您“大哥大胡”,岂不名正而言顺。胡适才恍然道:是的,是的;失礼,失礼。原是彼此对“大哥大”这一语义的理解不同,方生如此误会。
胡适的一生,到临死前都温文尔雅、春风化雨,并不因人身份高低而态度不同。20世纪50年代,经常替他拉洋车的车夫都说,没有见过如此态度平易近人的学者。
但也有例外,鲁迅从认识胡适起,就对胡适怀有戒心。他认为在办《新青年》杂志时,陈独秀像个开着的房间,说内有武器,刀叉剑戟看得分明,胡适则像个关着门的房间,门上写着内无武器,总让人生疑——所有认识胡的人,几乎都会夸胡适,为什么鲁迅要这么说,却是奇怪。
反过头来,胡适对鲁迅却是赞誉有加。胡适在日记中写道:“周氏兄弟最可爱,他们的天才都很高。豫才兼有赏鉴力与创作力,而启明的赏鉴力虽佳,创作较少。”胡适对鲁迅早期的杂文表示过极大的赞赏之情。比如鲁迅在《随感录四十一》写过“学学大海”、“摆脱冷气”、“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寓意深刻的话,胡适说,看了这段文字,感动得“一夜不能好好的睡,时时想到这段文章”。另外,胡适看到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出版后,也不禁报以热情的夸奖,认为:“这是一部开山的创作,搜集甚勤,取构甚精,断制也甚严,可以替我们研究文学史的人节省无数精力。”
鲁迅所以那样看胡适,原因大概是因为胡适与周家兄弟在办《新青年》时有过意见分歧,但只能算是不同意见,并非至于结仇。1926年5月,鲁迅、周作人和陈源(西滢)在《晨报》发生激烈笔战,徐志摩主编该报副刊版,劝了几次无效后,停登双方文章。胡适作为各方的好友,出于好意给周家兄弟写了封劝说信,言词恳切地劝双方停止打此无意义笔仗,此信一出,周氏兄弟从此与胡适绝交,鲁迅再也不和胡适来往了。倒是温和一些的周作人在1929年主动与胡适和好。胡适在回周作人的信里写道:“生平对于君家昆弟,只有最诚意的敬爱,种种疏远和人事变迁,此意始终不减分毫。相去虽远,相期至深。此次来书情意殷厚,果符平日的愿望,欢喜之至,至于悲酸。此是真情,想能见信。”
鲁迅是不能与胡适和好的了,从20世纪30年代初,鲁迅就不时在文章中挖苦胡适。1931年,鲁迅在《知难行难》一文中写道:“中国向来的老例,做皇帝做牢靠和做倒霉的时候,总要和文人学士扳一下子相好。做牢靠的时候是‘偃武修文’,粉饰粉饰;做倒霉的时候是又以为他们真有‘治国平天下’的大道……当‘宣统皇帝’逊位逊到坐得无聊的时候,我们的胡适之博士曾经尽过这样的任务。见过以后,也奇怪,人们不知怎的先问他们怎样的称呼,博士曰:‘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上。’胡适见溥仪,是在1922年5月。溥仪宫里刚安电话,他就打到胡适家召见胡适。胡适在1922年7月所写《宣统与胡适》一文中这样写道:“阳历5月17日清室宣统皇帝打电话来邀我进宫去谈谈。
当时约定了5月30日(阴历端午前一日)去看他。30日上午,他派了一个太监来我家中接我。我们从神武门进宫,在养心殿见着清帝,我对他行了鞠躬礼,他请我坐,我就坐了……他称我‘先生’,我称他‘皇上’。我们谈的大概都是文学的事……他说他很赞成白话,他做旧诗,近来也试试作新诗。”
但是溥仪与胡适的相见,却惹起了纷纷的议论,有人说“胡适要做帝师”,胡适不得不解释说:“这位17岁的少年,处的境地很寂寞的,很可怜的!他在寂寞中,想寻找一个比较也可称得是一个少年人来谈谈,这也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事,不料中国人脑盘里的帝王思想,还没有洗刷干净,所以这样本来很有人情味口的事,到了新闻记者的笔下,便成了一条怪异的新闻了。”几年后,这件事情又被鲁迅翻起。其实更有甚者,是鲁迅在以一条不实的新闻报道,说胡适为日本侵略者献策。鲁迅在《伪自由书》中说:“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但是,从中国小百姓方面说来,这却是出卖灵魂的唯一秘诀。”
但胡适对鲁迅却不以牙还牙。1936年鲁迅去世后,苏雪林写长信给蔡元培、胡适骂鲁迅,胡适在回信中却说:“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早年的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这不是因为胡适不知道鲁迅骂过他,他只是不做回应罢了。鲁迅死前说:“—个也不宽恕。”如果有来世,他会宽恕胡适吗?
倒是周作人对胡适有许多的感念。1962年胡适在台湾去世,身处困境的周作人写了一篇回忆名为《回忆胡适之》的文章,在文章中,周作人对胡适一句好话没讲,只是细数胡适帮助他出了几本书,几篇文,得了多少钱,分毛清楚。其中他特别提到第三回出版《希腊拟曲》一事:“这是我在那时的唯一希腊译品,一总只有四万字,把稿子卖给文化基金董事会的编译委员会,得到了十元一千字的报酬,实在是我所得的最高的价了。我在序文的未了说道:‘这几篇译文虽只是戋戋小册,实在也是我的很严重的工作。我平常也曾翻译些文章,但是没有像这回费力费时光,在这中间我时时发生恐慌,深有黄胖揉年糕,出力不讨好之惧,如没有适之先生的激励,十之七八是中途搁了笔了,现今总算译完了,这是很可喜的,在我个人使这三十年来的岔路不完全白走、固然自己觉得喜欢,而原作更是值得介绍,虽然只是太少。
谛阿克列多斯有一句话道,一点点的礼物捎着大大的人情。乡曲俗语云,千里送鹅毛,物轻人意重。姑且引来作为解嘲。’关于这册译稿还有这么一个插话,交稿之前我预先同适之说明,这中间有些违碍词句,要求保留……适之笑着答应了,所以它就这样的印刷着。”到了文末,周作人特别说起:“《希腊拟曲》的稿费四百元,于我却有了极大的好处,即是这用了买得一块坟地,在西郊的板井村。只有二亩的地面,因为原来有三间瓦屋在后面,所以花了三百六十元买来,但是后来因为没有人住,所以倒塌了,新种的柏树过了三十多年,已经成林了。别葬着我们的次女若子,侄儿丰二,最后还有先母鲁老太太,也安息在那里,那地方至今还好好的存在,便是我的力气总算不是白花了,这是我所觉得深可庆幸的事情。”走笔到此,我不禁搁笔远思凝想了小半天。
胡适一生温和,信奉自由主义,强调宽容,这样的态度,在朋友间可以传为美谈,也可以让我辈后人追想不已,但他对中国的政治显然认识不清。只要我们看一段话就清楚了。他说:1919年北大辞退陈独秀,是他最痛心的事,因为陈的离开,造成了中国思想的左倾;而《新青年》的分化,则使北大自由主义变弱。他甚至天真地认为,如果陈独秀仍在北大,受胡适和陶孟和影响,就不至于十分左倾。这种话不管对错,让我们看到的却是胡适的心灵。还有,1948年底,南京派飞机到北平接走了胡适,同行的有陈寅恪。胡适到南京后又说动政府派出一架飞机去北平接他学界的那些朋友,飞机返回,机舱门打开,只有几个人走下来,胡适不由得痛哭失声——从1919年新文化运动开始到1948年,30年的时间不算长,但已是新旧世界之异了。
二、名家晚年治学
古往今来,大凡事业上卓有建树的名家,即使步入晚年,仍然谦虚且勤勉、用功。此文撷取部分名家晚年治学的趣话,以飨读者。
焚诗毁稿晚唐杰出诗人杜牧,晚年在审阅自己平生的诗作时,凡认为不满意的,统统付之一炬。本来他留存的诗作约1000余首,结果烧得只剩下200多首。幸亏其外甥还保存了200余首,杜牧诗作才有400多首得以存世。
精心修改宋代大文学家欧阳修,晚年潜心修改平生所写的文章,常为了寻找一个更贴切的词语,苦苦思索,反复斟酌。夫人见他用功过度,劝道:“何必自苦到如此程度,难道你的文章还怕那些老先生骂吗?”欧阳修笑道:“我倒不怕老先生骂,却怕后生耻笑啊!”
苦练书法南宋爱国诗人陆游,74岁始学书法。他在《学书》一诗中写道:“九月十九柿叶红,闭门学书人笑翁。世间谁许一钱值,窗底自用十年功。老蔓缠松饱霜雪,瘦蛟出海拿虚空。即今讥评何足道,后五百年言自公。”陆放翁晚年不怕被人“讥评”,以“瘦蛟出海”的雄心和“老蔓缠松”的韧劲,哪怕“自用十年功”,也要把书法练好的精神,值得后人学习。
题座右铭老革命家吴玉章,81岁时题写座右铭:“我志大才疏,心雄手拙;好学问而学问无专长,喜语文而语文不成熟;无枚皋之敏捷,有司马之淹迟。是皆虚心不足,钻研不深之过。年已八一,寡过未能,东隅已失,桑榆未晚。必须痛改前非,力图挽救,戒骄戒躁,毋怠毋荒,谨铭。”吴老这种愈老愈爱做学问的精神,是多么难能可贵!
不闲一日国画大师齐白石85岁时,一天上午连作4张条幅后,中午仍不停笔,坚持又画一张。画完题词曰:“昨日大风雨,心绪不宁,不曾作画。今朝制此充之,不教一日闲过也。”
巧署笔名大学者钱钟书晚年时,只要有年轻人向他请教,总是热情地解答和帮助。一次,有个叫吴庚舜的青年写了一篇关于《长恨歌》的论文,请钱老指导。钱老认真地字斟句酌,帮助充实修改。当论文发表时,吴庚舜请钱老署名,他不同意。经再三央求,钱老只好署了个笔名——郑辛禹。何以署这样一个笔名呢?钱老为此动了一番脑筋:《百家姓》中,“郑”在“吴”后;天干排列中,“辛”在“庚”后;而古代圣贤中,“禹”在“舜”后。由此可见,钱老在扶掖后辈治学方面,是多么谦虚而笃诚啊!
一再重复桥梁学专家茅以升八旬高龄时,仍可背诵圆周率小数点以后100位的精确数值。当人们赞佩地问他,何以有如此惊人的记忆力,茅老回答:“重复,重复,再重复!”看来,“重复是学习之母”这句话对老年人更为适用。
夕不甘死美学家王朝闻年轻时曾向自己提出“朝闻道,夕死可也”的求知要求。他70岁时,请人刻了一枚“夕不甘死”的印章,又对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闻道未详,夕不甘死;壮志未酬,夕不甘死。”
直到90多岁时,他仍勤于读书,笔耕不辍。他说:“晚年有两件大事,就是勤奋地读书和写作。”
百岁上学著名的棉花专家钱立坤,百岁时还觉得自己知识不足,于是他又报名上了老年大学。并为此赋诗:“初学棉花弱冠年,现逾百岁心留连;更新知识进‘老大’,退休不忘跑田园。”
免得流传著名画家吴冠中晚年时,有人问他:“吴老,最近忙些什么?”答曰:“一是坚持创作,二是撕画儿。”见对方不解,又解释道:“趁现在活着,赶紧把那些自己觉得不满意的作品撕掉,免得流传出去。”
希望误会著名学者、书法家启功80多岁时,为了集中精力搞点学术研究,多次贴告示于门上,谢绝客人来访。但上门的人仍络绎不绝。启功老又贴出这样一个告示:“启功遗体,告别去了。”友人建议他将“遗体告别”4字连在一起,并加上引号,以免引起误会。启功却说:“我就希望误会。”
三、读书与阅世
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说:“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然而,人并非天生就是会思想的动物,如果缺少了后天的培养与学习,再聪明的人也不会有思想。而学习,在现代文明社会里,可以简单地概括为:读书与阅世。
读书是重要而必须的。现代教育制度的确立与完善,可以说为人人享受最基本的教育提供了条件,同时也为培养和发现人才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平台。我们之所以必须接受学校教育,是因为人类已经创造和积累的文化科学知识,我们不可能都从实践中获得,只有通过接受教育这一有效途径来掌握,这是毫无疑义的。进一步说,一个人即便是接受了良好的学校教育之后,其学习的过程也并没有结束,而将是伴随其生命的整个过程。尤其是在现代信息社会里,知识的更新速度越来越快,一个人一旦停止了读书学习,也就意味着缺少了生存竞争能力,直接关系到一个人的安身立命。
读书让一个人面向了知识世界,也让人充分感受到了个人的渺小与浅薄。于是理解思考、谦虚谨慎以及精益求精,才可望被学习者当作一种品质和境界来追求。因此可以说,一个人的骄傲与自满,或者说狂妄与自大,都是因为他背离了知识世界,面向了愚昧和无知,以致最终成为“无知者无畏”。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衣食无忧却从不读书而“面目可憎”者,其实并不鲜见。
人是社会中人,应知社会中事。因此对一个读书人来说,当然面临着一个“阅世”的问题。读书人常犯的毛病不是嗜书如命,而是回避现实社会。表现为“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显然,这样的读书态度是消极的,是有害无益的。面对纷繁复杂的现实社会,一个知识分子也好,一个读书人也罢,其根本的出路就在于积极地融入、认真地体察和大胆地呐喊,以此来充分体现作为一个知识者的社会良知。也就是说,一个读书人不能只为读书而读书,而是要尽可能地运用所学到的知识,对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进行适时的人性关照与人文关怀。只有积极地参与社会实践,努力透视大众生活,了解百姓生存状态,才能阅读好“社会这本大书”。所谓“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其道理就在于此。
书本知识虽然来源于社会实践,但并不表明我们阅读了书本知识,就能了解我们所处的现实社会。恰恰相反,我们只有读好了“社会这本大书”,才能更好地理解书本知识。如果一切都是唯书为上,其后果只会是走向本本主义的死胡同。古人说“尽信书不如无书”,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德国哲学家叔本华说:“我们读书时,是别人在代替我们思想,我们只不过重复他的思想活动的过程而已,犹如儿童启蒙习字时,用笔按照教师以铅笔所写的笔划依样画葫芦一般。
况且被记录在纸上的思想,不过是像在沙上行走者的足迹而已,我们也许能看到他所走过的路径;如果我们想要知道他在路上看见些什么,则必须用我们自己的眼睛。”很显然,哲学大师所要澄明的是,读书与阅世,两者相辅相成,互为验证,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对此,清末大学者严复也有自己的深刻见解:“读书是阅古人之世,阅世是读今人之书。”
读书与阅世,或者说阅世与读书,它们仿佛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共同证明了一枚硬币的存在与币值。简言之,读书有如阅世,阅世也如读书。故而我们有必要学会“在读书中阅世,在阅世中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