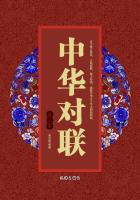被采访人:孙德全,男,47岁,生于北京,祖籍山东微山。曾在某汽车团服役十六年,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创作联络部副主任。
采访地点:太平路22号内一办公室内。
在中国作协会员的圈子里,孙德全副主任的口碑极好,他工作认真,做人谦虚,待人热情,乐于助人。最近得到他赠送的一本个人的散文、随笔集《知者乐》,更使我了解到了另一面的孙副主任,本以为他只是仕途上的人,没想到他的文笔还这么好。他曾在军旅当了十六年汽车兵,说起那段刻骨铭心的生活他总是滔滔不绝。
七0年底参军入伍时我只有十六岁,才开始去的是北京军区七分部,部队在石家庄和平医院西边,当时在汽车四团,那时和平医院算是西郊,现在已是市中心了。我们北京去的兵年龄都小,大部分被分去做饭、养猪、干杂务活,领导看我个子小,人又机灵,就被一连连长要去当通讯员,我们团有九个汽车连队,一个修理连。我跟连队去山西井径县一个叫南张村的地方协助当地驻军搞中防施工,我们连的人分散住在了好几十户人家里,那时老百姓对军队特别好,每家每户把家里最好的房子都让出来给我们住。我们连部住在村里的一个富农家里,他们的房子都是窑洞,那时村里没有电,也没有水井,人家都开着车去施工了,我担着水桶去坡下的河里去挑水,担两桶水爬坡时特别吃力,有时前边水桶里的水泼出来,好多次都差一点把自己滑倒。因是城市兵哪干过这活,有时累的都想哭。
我是在清东陵学的开车,农村兵学车的心情比较迫切,对我们城市兵来说,能躲过上山下乡来部队当兵就感到很光荣的了,所以对学车并不是特别感兴趣。在东陵的石板路上,我们排长教我开车,当时我们连队装备的是从朝鲜战场上退下来的嘎斯51卡车,载重量为2.5吨,一上车排长就让我坐在主驾驶这边,他教我起步、踩离合器、给油,加档减档,我总是手忙脚乱,顾了这儿忘了那儿,经常灭火,一半天下来出了一满身汗。后来我去了营汽训队学开车,一共就我们十多个人,都是在工作上表现比较好的。营里怕这些好兵送团汽训队训练分不回来了,所以抽了几个老司机自己训练。
我们汽车团,每年春天出发,俗称上山,配属兄弟部队执行国防施工任务,多数时候是在山区跑。十一月份下山,回营房休整。修理连要把车全卸了保养一遍。七三年我当了班长,带着五台车出去施工,因为都是旧车,车况特别的不好,每次出车都有趴窝的。为了不出事故,我总结出了班组出车经验,并编了顺口溜,到别的连队去介绍经验。顺口溜是这样编的:班组行车头车是关键,中速行驶保安全,超车时要想一想,后边还有一个班。当时出车我在最前面。速度保持在每小时40公里,副班长在最后一辆车上压阵。七四年我提了干,七五年初我带着我们排,15台车到河北丰宁执行任务,修碉堡、筑工事。据说当年苏联红军打日本时从坝上下来,走的就是那条沟。那时任务紧,没白没夜的赶工程进度,仗着年轻,苦累不在话下,睡一觉,第二天起来接着干。几十个碉堡要修在十几个山腰里,多少吨水泥、钢筋要运上去。临时修的路坡陡弯急,一台苏制的嘎斯51装半车拉二十袋水泥上去还费劲。上山时车好象是挂在墙上往上爬,有时拐几个弯车却又下来了几米高。下山更危险,挂着一档踩着刹车一点点往下蹭,一不小心就可能车翻人亡。每跑一趟都是提心吊胆,我不但为自己但心,还得为全排的人员、车辆操心。晚上天黑了下了班,所有的车辆都回来了,我才能长出一口气。一天晚上收车前下起了大雨,09号被困在了山上,司机小安跌跌撞撞从山上跑下来,说车在山上横滑的厉害,实在不敢向下开了。他一边擦着雨水和汗水一边用手比划着,前后轮都打上石头了。我想这雨越下越大,今天晚上是没办法了。一晚上我也没睡踏实,万一山体滑坡,车可能就报废了。
说到这里他打住了话语,他点上一支烟,深深的吸了两口,他神色庄重的说,那一次我真是算捡回了一条命。那年他才二十岁,带着15台车去执行那么艰巨的任务,试想现在的年轻人谁能做的到。想到他那一双已上初中的长的文文静静的龙风胎儿女,也许这就是老天对他付出的一种回报。
第二天天不太亮我就起了床,开车到山下一看,立时出了一身冷汗,那车好险,就象头向下挂在了半山腰上,随时有可能冲下来。待爬到跟前一看,车前轮离悬崖边还有不到一米的距离。小安想上车,我说你干什么,把钥匙给我。我是排长,死活也得我上。告诉所有人使劲往后推车,我跨进驾驶室,没敢向前看,我稳了稳神开始挂倒档轰油门,战士们一起高喊:走、走。可后轮打滑,我拉了手刹下车察看了一下,命令一班长带几个人上车,站在车箱尾部,其他人继续推车。我探出头对一班长说,如有危险,你们就跳车。车上的人没有回答,车上车下的人一起喊:退、退。喊声地动山摇,响彻山谷。车终于开始向后退了,我们成功了,等开车下了山,我在驾驶室里坐了许久没有出来。
我在连队一待就是十年,一年365天和战友们一起摸打滚爬,风里雨里战斗在国防施工的运输线上。那时上坝给那儿的部队送物质,路上要爬一个多小时,并不是坝有多高,而是道路难走,由于水土流失,路上深浅不平不说,经常有山洪冲下来的巨石挡道。据说坝上再往里走就是一马平川了,再向里没有一点防御能力。当年“老毛子”的坦克就是从这坝上杀下来的,于是就不修路,也算是消极防御吧。可上坝就难了,一路颠下来,屁股不好受,脑袋也会深受其害,顶的车顶咚咚响,撞的人都晕乎乎的。80年我被调到团政治处当干事,81年因工作需要调北京军械训练大队当干事。后被送到北京大学中文系上了两年学,在上学的同时参加自学考试拿到了大学文凭。87年转业到中国作家协会工作,在部队时就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散文、诗歌等文学作品,转业后由于工作太忙,写东西少了。90年提会员处处长,97年任创联部副主任兼会员处处长。90年开始我兼职义务给单位开小班车,那是一辆尼桑面包,每天下班我把西线上的同志们送回去,早晨再把他们接回来,一直到九五年,整整又开了五年车,跑了十万多公里,从来没有蹭刮过车。开这车舒服多了,冬天有防冻液。哪象我们在部队时每天晚上得把车里的水放掉,怕放不干净,每次放完水,要站到车上用嘴去吹。一般不让打马达,天天站在车前用摇把摇来发动车。
想想自己这多半生,除了小时读书,从十七岁开始我的驾龄已有30多年了,生活中的很多时光是在驾驶室里度过的,从过去部队只能装备朝鲜战场上退下来的苏制嘎斯51,到今天欣欣向荣的民族汽车工业。我们的国家一步步富强了起来,我们的军队也一步步强大了起来。盼望着将来儿子、女儿都能顺利的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或出国发展,到那时我国肯定已顺利入世,到时候买辆私家车,谁有事谁出门开着,说不定到时候每人都能拥有一辆车,象现在每人都拥有一辆自行车一样。
每当战友聚会时,望着一个个熟悉而又有一点陌生的身影,总能勾起些过去在军营时的往事。我们那一个汽车团的战友能聚在一起的还有二十多个人,想当初一个个都是十五、六岁的样子,穿上肥肥大大的军装,都快找不到人了。军营给了我们健康的体魄,磨炼了我们的意志。十六年的军旅生活,能使我们受益一生。
孙德全的肠胃不好,他说这都是在部队上给打下的印记。他人很瘦弱,但精神总是那么饱满。他的《知者乐》中许多篇章写到了他的汽车兵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