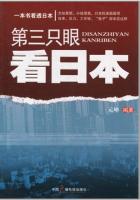文/蔡錞青
这是我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想起我的童年。
很早以前,我以为再也不能想起。
岁以前,我想不起来任何事情,包括那时候,那个领唱的低低发出声音的女孩儿,那支橘红色的自动铅笔。
有一天,它早晚回到你的记忆中,重新变成你的生活,或一个极小的部分。
让我向你描述我的旧居院落。
文祠西。几巷几号,附近的建筑。都忘了。
院子外的石板路,我说过,有雨水的时候我们都穿着水鞋,把水溅到脸上。巷口有一块大石头刻着:石敢当。好像武侠小说里的人物,到现在我都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只有院子里的景物依稀。
一条石门槛,两扇吱吱响的木板门,一棵约三米高的老番石榴树。在我爷爷去世以前,有一年它长了许多虫子,那年的果实又大又甜,院里的老人都说,这树要成精了。在我还没有学会爬树时,就失去了练习的机会。那棵老树被伐倒的声音我没有听见,现在想起来,它一定像留恋人世的老人,暗自哭泣了很久。
房子开始的时候都是瓦片屋顶,灰绿色的,小的时候我从来不知道那其实是很贴近自然的色彩,我也从来没有像电视里的小孩一样,爬到上面踩出声音来。苏童说下雨时看瓦上的青花,我没有留意过,只有耳朵听过那些花的声音,它有许多种音乐,现在我们在城市,梦里才能听到。
院子中央是一块很大的空地,种满一排一排的花,两个大水缸种着荷花,夏天我们总是折了花泡在水里喝,真好,那时候伯父还在,他把花拿在手上,总是不舍的样子。他一生都是不舍的样子,眼神柔和。他种了那么多花,我还没有来得及认得它们的名字。它们年年地开放,春花秋花,院子里总是不经意地开着花。我还不知道它们的名字。
一共有两口井。井边长了许多青苔,有时候它们变成黄色的,似乎有发霉的味道,井边的石头很滑,我总是摔倒,我对着井说话,回音是很响亮的,是有一个壳包着的声音。井水是冰凉的,因为它们来自很深很深的地方。如果你爱一个人,你可以说你们是井里两滴水,感情深,那么深,你甚至不知道你自己爱得是怎样的深。
我只是想,建筑、拆迁,我们只能记得,大约是这个地方,我们曾在那里生活,但是我们再也不能回来看望那面墙,那间屋子,那个你学会走路,傻里傻气开始成长的地方。
浮屑一样的往事,也和它们一样。
回过头来,许多美的细节,还是会留在生活里。
美,就是我们经历过、失去过,最好的报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