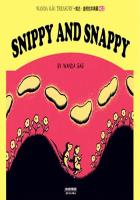动物摄影师柳宏的半路杀出让我们的小海狮改变了线路,我们偏离了北京,一路开往内蒙草原。小敏就躺在小海狮的怀里,他喜欢跟我们一起唱歌。我们的小海狮也不负众望,它一路零故障,用事实证明它绝对具有永远在路上的潜质!
那是我人生中最为快乐难忘的旅程:像是永无尽头的道路、洋溢着青春气息的城市、给我们造成错觉认为她已经康复了的小敏的笑脸、各色树木和它们在夕阳下的影辉、“好久没有讲脏话”的莫名其妙的自我意识、五线谱似的电线上的野鸽、被我们强迫笑着打招呼的运兵车、伸出拇指被拒多次的徒步旅行者、偶尔在我们车前掠过的团结友爱的羊群、即使一时沉默车厢里也始终弥散着的那种愉悦兴奋的感觉……
途中我们错过了校花的婚礼,虽然其余的那帮家伙排着队挨个和校花行了拥抱礼,但我们能想象得到校花在得知我们几个没能参加她的婚礼的那种沮丧表情(或许这仅是我们的一厢情愿而已)。我不知道那帮家伙在和她的拥抱中除了标准的动作和必要的触碰面积还有没有其他多余的可被称为揩油的动作,担若是换了我,我会在校花的脸上来个深情一吻(或许这能给后来者做个示范)。——“姑娘人人都有占有的权力”,平庸的小子当然也一样!
在路上空谈家马猴忍不住将他的灵感迸发讲给我们听,主题是《音乐、女人和草原的辩证关系》。我承认除了这段臭不可闻的议论以外,我们的谈话称得上是善良且愉快的,更重要的是,只要在路上,我们CD就会一直转下去!
现在想来,那张《灵魂橡胶》和《在别处》并不只代表爱情,就像她信上所说的,我已经被人指引着走了很长一段路。我在一个莫名其妙的年龄毫无准备地陷入一群人用吉他和眼泪激起的烟雾里,那不是跟着节奏扭几下身体或是幼稚的猜歌词游戏能解释的,毫无疑问它左右了我的生活,让我和现实之间的关联变得脆弱。当其他人给自己的人生忙着增添砝码的时候,我还得先调节那该死的天平。只要人们能稍稍调动一下常识,便可以想见“平庸的才能”和“脱离实际的生活理念”组合在一起是多么糟糕。
那天,我站在草原,一侧是喧闹欢腾的人群,一侧是苍茫无尽的黑暗。在身边朋友的说笑声中,我突然意识一种快要结束的落寞,我们的回光返照大概就是这样了。
我们见到了汪峰、许巍、见到了何勇、李延亮、栾树、丁武,北京和西安许多地下乐队也赶去了,他们很多都称得上是一流的乐队。童子乐队嗓音笨拙的主唱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们拒绝将技巧放在第一位,而是从心底发出最质朴的渴望;三鸟乐队用三把毫无约束的吉他让所有人目瞪口呆,在那种混淆的激流进行了一半的时候,人们才恍然意识到其中蕴含的节奏和律动;枪手乐队的贝司手盖过了所有人,那双手的挑拨翻飞让所有人惊谈不已……
船长为妹妹的事戒了烟酒,他在那场聚会中彻底舒展开眉间的皱痕,我们所有都不再抽烟,喝酒也只浅尝则止。柳宏抓住每一个机会给大家拍照,暗夜中扭曲的笑脸又让我们想到从前。
当那些知名乐队离开的时候,自发前来的乐手开始占据空旷的舞台,人们用汽车车灯将他们照亮,并和他们一起在帐篷外疯狂。他们唱了崔健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一块红布》、《一无所有》、《假行僧》、《最后一枪》,唱了窦唯在黑豹时的《怕你为自己流泪》、《Don’t break my heat》、《无地自容》、《希望之光》,唱了铁玉兰的《回家的路》,唱了指南针乐队的《请走人行道》……
我们的帐篷就设在帐篷群的中央,我们的小海狮和一对情侣的吉普一起酣甜入梦。草原之上的星群变得很低,我一边闻着青草的馨香一边仰面朝上。其他人围在我的身边,在马猴的主持下又开始了“草原晚间音乐聊吧”。附近的人依旧活跃在深夜里,我们几个却变得安静很多。
马猴和船长又唱起歌,柳宏的相机不时在眼前闪烁,他们将所有曲子都放慢节拍,唱了许巍的《蓝莲花》、《水妖》、《旅行》、《星空》、《我思念的城市》,唱了披头士《Yesterday》、《Let it be》、《Hello,Goodbye》,唱了郑钧的《温暖》、《灰姑娘》,唱了张楚的《孤独的人是可耻的》、《蚂蚁,蚂蚁》,唱了朴树的《旅途》、《且听风吟》……我在他们的阵阵掌声和笑声中,在酒和星空带给我的一点点晕眩中,在他们像是永无止境的歌声和温暖中,渐渐困倦、入眠,滑入永恒的夜的边缘。
几天之后,船长固执地要我们所有人都离开了北京,而一个人却固执地来到北京,一直守护到手术成功、小敏再次去看春风拂过的草原。没错,是周静。她一得知船长的事情便马上来到北京,仅用了两秒钟的时间便让船长的父母喜不自禁,然后再用了两天时间便让小敏管她叫了嫂子,再然后,船长躺在床上的那段时间里,他们的手终于牵在一起。
在北京同船长道别后,沈晓喻结束了他的蜜月之旅,继续为人民服务去了;柳宏赶去了秦岭继续钻进崇山峻岭展开对金丝猴的偷拍;马猴和夏侯杰开着小海狮一路奔回到学校,那里还有两个女孩儿和一个被烧焦的店铺等他们。
我回了家,准备为一段无所事事日子填补上一些痛苦和迷茫。我打算向家里人坦白,然后在他们的伤心和唠叨中决定是回到金融界还是继续一直在家里宅下去,直到发霉腐烂(在我身上早就带着这种霉菌)。——在和马猴他们告别的时候我撒了谎,我不打算再回学校去,我要像船长那样闷声躲在一个角落,暗自等待时间从身上流过。所谓独自承受不过是让载着痛苦和快乐的时间从自己身上碾压过去,自己既不挽着别人的手也不会发出任何声响。
没想到我妈迎接我的第一件礼物居然是给她未来儿媳的一件价格昂贵的衣服,见我两首空空孑然一身,她立刻发动群众给我寻找早先被搁置下来的一端连着急于出嫁的姑娘的线头。而我却有了再次逃离的念头。
当我收拾好东西,准备第二天离开家的那天晚上,我被老妈逼迫去相了亲。我像个货品似的被快递老妈交到她的一位同事手中,然后又像盘菜一样被这位介绍人拉到了餐桌上,并在她的监视下一直等了那个喜欢迟到的女孩儿半个小时。坐在那里的那段时间我觉得自己蠢到家了,难道我至始至终都要被生活捉弄吗?!难道我非得还要傻等半个小时,只为等到那个挑剔的女孩儿一句“这不是我的菜”的吗?!
谢天谢地,上帝为人类塑造的一套完美无暇的新陈代谢系统想必就是为了保证一些无聊的阶段必须停止,一些新的局面可以发生。介绍人去了厕所,我抓住这短暂又宝贵的三分钟内的时机立刻付了账单准备离开。在离开收银台,刚转身至餐厅走廊时,我见到了她——让我意想不到、恍若如梦、猝不及防、一时愣住的她,我的第二个女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