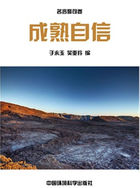她见晋献公又陷入沉默之中,照着他的软肋,又加一拳:“且昔者,曲沃之兼翼,非骨肉乎?先武公不顾其亲,故能有晋。申生之志,亦犹是也。请主公让之,以满其欲。”
晋献公摇首说道:“不可!”
骊姬道:“有甚不可?”
晋献公道:“寡人以武与威立世,破国者二,灭国者三。今当吾身而失国,不可谓武。有子而不胜,不可谓威。失武与威,人能制我,虽生不如死。卿勿忧,容寡人慢慢图之。”
骊姬道:“今赤狄臯落氏屡侵我大晋,主公何不使申生将兵伐之?若其不胜,罪之有名。”
晋献公道:“若其胜了呢?就像伐狄、伐霍、伐魏那样?”
骊姬道:“前次,申生连灭三国,非其能也。乃赵夙、毕万之力,加之狄又内讧。这一次主公设法将赵夙、毕万调回,他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
晋献公道:“这个好办。”当即降旨一道,命申生将兵讨伐赤狄,留赵夙、毕万分别驻守狄、魏。
这一招过于拙劣,明眼人一看便知。重耳坐不住了,扮作商人,由狐毛相伴,潜往曲沃。
行至旷野,雷鸣电闪,瓢泼似的大雨从天而降,行人全都加快了步伐,重耳也在跑,跑得气喘吁吁。但在他的前方有一书生模样的汉子,身背竹简,仍在不紧不慢地走着。
当重耳与他擦肩而过的时候,顺口说了一句:“你这人,未免有些太斯文了,下大雨也不乱步。”
书生立马回道:“乱步怎样,不乱步又当怎样,难道前面没有雨吗?”
重耳略略怔了一下,是啊,前面也在下雨,跑快跑慢有甚区别?
他不由自主地放慢了脚步,和那书生攀谈起来。
“贤兄,您贵姓?”重耳问。
“免贵,在下姓介,名子推。”书生不紧不慢地回道。
重耳啊了一声道:“你就是介子推!久仰久仰!”
介子推在晋国的名气虽说不如重耳,但也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
他的父亲介信,原是朝中的大夫,因翼城有人作乱,被晋献公遣往翼城,改任翼城邑长,虽是一个邑长,但因翼城曾为晋都,朝廷上下对他很是看重。莫说一个大夫的儿子,就是再小几级的官员,哪家公子没有奴仆、车马?介子推没有。他说,当官的是我父亲,又不是我自己。所以他从来不摆阔气,平时的吃喝穿戴,跟普通的百姓没有什么两样。
介子推十八岁那年,前去翼城探望父亲,那时的旅店,不像现在,没有被褥,顶多有一条稿荐。介子推带着被褥和书简上路,当然,这被褥和书简由毛驴驮着不用他背。但他得喂毛驴呀。又是走路又是喂驴,虽说十分辛苦,他却一天到晚乐哈哈的,从没想到要打扰沿途的官府衙门。
他走了七天,才到父亲的官署,父亲见儿子到来,别提有多高兴了,当即将他安排在驿馆,并要他多住几天,好好休息一下。他坚决不同意,理由是我又不是官员,怎么好住在驿馆呢?
他东寻西找,找到了马厩里的一个角落,住了进去。
介子推见重耳气度不凡,便有心和他结交,满面带笑道:“弟已把弟的贱名告之于兄,兄可不可以把兄的尊名也告之于小弟。”
狐毛抢先回道:“不瞒子推兄,我家公子,姓姬,名重耳。”
介子推闻言,倒身便拜:“不知公子驾到,失敬得很。”
重耳双手将他搀起:“不知者不为罪,但不知贤兄要往何处而去?”
介子推道:“前行三十里,乃小弟的寒舍,当然是回家了。”
重耳喜道:“你我正好同路。”
他二人一边走一边聊,聊天文、聊地理、聊当地的风土人情,什么雨不雨的,全然不放在心上。那雨倒也知趣,没下多久便停了下来。
路过介庄的时候,经介子推力邀,重耳、狐毛随他来到介子推家中。一个堂堂国都的邑长,其家和普通的农户并没有什么两样,土打的院墙,房子坐北朝南,屋顶有草有瓦,那瓦位列前、后、左、右,各八行,俗称金镶玉。
安顿好重耳、狐毛之后,介子推将一只老母鸡撵得满院子乱飞,狐毛慌忙跑了过来,帮他将鸡捉住,双手交给介子推。
谁知,到了吃晚饭的时候,介子推端进来两盘素菜,外加一盆稀粥和六个花卷馍。
狐毛有些纳闷:那鸡明明是杀了呀,杀了鸡不用来招待客人,留它何用?但又不好意思问。
饭吃到一半,介子推被母亲唤到内室,回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一只盘子,盘子里放了半只鸡。
介子推满面笑容道:“公子有口福,小弟母亲说她一个人吃不了一只全鸡,特分出来一半让小弟招待客人。”
狐毛打鼻子里哼了一声,欲要发作,被重耳拿眼神制止住了。
夜里歇宿的时候,狐毛满腹牢骚地说道:“介子推这人,看起来人模人样的,却不是个东西。”
重耳笑问道:“他怎么不是个东西?”
狐毛道:“杀了鸡不用来招待客人,却拿去孝敬他的老娘,他的老娘吃不完了,又拿来让客人吃,简直把我们当成乞丐了!”
重耳道:“有了好吃的东西,先老娘后客人,这正是一个大孝子所为,能和这样的大孝子交朋友,不正是吾等的福分吗?”
狐毛张了张嘴,欲说又止。
重耳见他仍是有些不服,循循善诱道:“先贤说,有三种人不可交,汝知道不?”
狐毛摇了摇头。
重耳曲指说道:“不孝敬父母的人不可交,连父母都不孝敬的人,还会对别人好吗?这是一不可交;“喝酒永远不醉的人不可交。喝酒一次也不会醉,说明此人的城府太深。这是二不可交;“一辈子没有上过当受过骗的人不可交。一辈子不上人当,不受人骗,说明这个人太精明。这是三不可交。照此而论,交朋友就是要交那些孝敬父母之人;交那些容易喝醉和容易上当的人。”
狐毛频频颔首道:“我明白了。”
重耳和狐毛,一连在介庄住了六天,他们不止切磋学问,也切磋武艺。将要分别的时候,重耳随口问道:“介兄所接触过的人中,有无大贤之人?”
介子推双掌猛地一拍道:“兄不问,小弟差点儿忘了。在距敝庄四十五里的地方有一个赵家集,集上住了三百多户人家,家家都有人舞枪弄棍,内中有一个叫赵衰的,字成子,不只武艺好,且为人心地宽厚,堪称贤者。”
重耳笑道:“他的心宽厚到什么程度?”
介子推道:“宽厚到连劫盗都感动了。”
他讲了这么一件事情。
这件事发生在三年之前,赵衰坐着牛车周游列国,走到一个叫二郎山的地方,山脚下,草丛里突然蹿出来十几个劫盗,手中的兵器非刀即斧,一个个面目狰狞。内中一个大胡子喝道:“把车上的财物留下来,免你一死!”
赵衰微微一笑道:“吾乃一介书生,车上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你们如果觉得对你们有用的话,尽管拿。”
说毕,跳下车来,抄着双手,站在一旁。
劫盗跳上车,乱搜一通,不说衣服鞋祙,连玉米饼子也搜了去。内中三个小盗竟当着赵衰的面吃起玉米饼子来。
赵衰的心猛地一动,这也是一伙穷人,为饥寒所迫才走上劫路这条道,我不能袖手不管。遂长叹一声,一脸诚恳地说道:“诸位仁兄、仁弟,我虽说不是豪绅,也不是富商大贾,但家里还有三百亩薄田,吃饭穿衣不用发愁,车上草垫底下尚有七匹缣,比那些旧衣物值钱,你们一并拿去吧。”
劫盗听了他的话面面相觑。良久,还是那个大胡子说道:“我等因生活所迫,才走上劫路这条道,但我们只劫为富不仁的豪绅、商贾,你是好人,劫了好人会受报应的。”
他转面向劫盗命令道:“弟兄们,还不快把这位先生的东西放回车上。”
重耳轻轻颔首道:“真是一个心底宽厚之人!若能与此人交个朋友,死不悔矣。”
介子推道:“公子如果真的想和赵衰交个朋友,小弟愿意穿针引线。”
重耳道:“那就隔河作揖——承情不过。”
介子推道:“如此说来,公子在小弟寒舍再住一天,小弟这就去赵家集一趟,把赵衰给您请来。”
重耳道:“对待贤人,登门拜访,吾还唯恐吾心不诚,岂有让贤人自来的道理?”
介子推道:“既然这样,咱明日起个大早,小弟带公子去赵家集。”
重耳道:“那就多谢了。”
翌日鸡鸣,重耳、狐毛由介子推相引,直奔赵家集。
赵衰本就好客,加之十分仰慕重耳,当即杀鸡宰羊,厚宴重耳。当然,那酒是少不了的。
也不知是重耳合该有吃虎肉的口福,还是合该再交几个朋友,正喝着,闯进一人一骑。那人身长九尺,紫膛面皮,二目亚赛铜铃,一进院子便从马背上拽下来一个麻布口袋,口袋上血迹斑斑。
赵衰笑问道:“山祈兄又给小弟送什么好吃的来了?”
山祈声如洪钟道:“虎肉。”
赵衰道:“哪来的?”
山祈道:“叔坚兄打的。”
赵衰朝厨房喊着:“狗蛋,把这些虎肉扛到厨房,先红烧一盘端来。”
狗蛋是他的男仆。
狗蛋应声而出。
待狗蛋将虎肉扛进厨房之后,赵衰忙邀山祈进屋饮酒。
重耳、狐毛、介子推全都站了起来,笑脸相迎。
赵衰指着重耳向山祈介绍道:“这位是咱国君的大公子,名唤重耳。”
山祈早已听说过重耳的大名,忙上前施礼。
介绍过狐毛和介子推之后,赵衰方指着山祈说道:“来来来,让大家见识一下,这位便是二郎山的四大王,名唤山祈。”
重耳当先啊了一声,目不转睛地盯着山祈,暗自思到:“像这样一位一身豪气的汉子,怎么能是强盗呢?”
赵衰笑释道:“强盗也是人,内中不乏豪杰之士。像这位山祈兄,乃将门之后,只因他的邑长欺压良善,劝之不听,被他失手打死,这才上了二郎山。”
重耳“啊”了一声,右手作邀客状:“请,请上座。”
山祈不肯,挨着赵衰右肩坐了下去。大家一边喝一边聊,重耳对二郎山的情况有了大概的了解:二郎山原名牧虎顶,东西走向,约二十里长,主峰高达六百余丈,山上有霸王寨、黄柏垛。三十年前亦有人在此占山为王,为王者焦二郎,故牧虎顶改称二郎山。如今占据此山的大王叫叔坚,就是曾经劫过赵衰的那个大胡子;二大王叫黑虎,力可举鼎;三大王叫特宫,是个落魄文人,拥有喽啰五百余人。
重耳突发奇想:人大都闻盗色变,但我观山祈其人,是条汉子,其他三盗呢?若真是三条汉子,日后也许有用得着处,何不去山寨走一遭!
此言一出,狐毛极力反对。当然也有不反对的,那便是赵衰和介子堆。
狐毛扭不过重耳,只得跟他上了二郎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