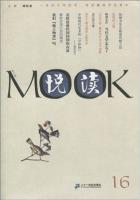在武昌胭脂路昙华林,当年华师中文系图书馆,我读到一本列夫?托尔斯泰晚年日记。那奇怪的日记格式与世人不同,过去没有,现在我也没有发现,恐怕将来……托翁当天写下第二天的日期,接着写下“如果我还活着,就要写作”,到了第二天,接着写上“我果然活着”……他继续赶紧写作。托翁晚年与死亡赛跑,很多事抢着做,如和农奴一起劳作等,但写作仍是他第一位的工作。
“奇怪的日记格式”的发表,对我的小发现是一种肯定,一种鼓励,更是一种鞭策。从此,被列宁称为“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的托尔斯泰,他的活着就要写作的精神成了我的镜子。大学毕业后,我先是在荆州地直一所学校教书,后到江陵县文化馆工作。其间,正逢文革十年,学校和文化馆都有图书馆,尘封的文学名著无人问津,我偷食了不少,包括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粉碎四人帮后,我从政一直没忘读书,没全投笔。
1993年底,我调省直,先后工作在省委、文化厅、湖北日报社,隔三差五也写点小文章,以言论、散文、随笔为主,目前已出六本书。
奇怪的日记格式,已深烙心底,流诸笔端写文字。作家有大有小,活着就要写作的精神却应该是永远的。
(周年丰,1960年入中文系。曾任中共湖北省委副秘书长,省文化厅厅长,湖北日报社长兼党组书记)
难忘昙华林
【丁忱】
相逢是首欢乐的歌,回忆是条遥远的河。人生有许多欢聚,许多回忆;有的心酸,有的甜蜜。
人老思骨肉,人老爱忆旧。早已过古稀之年的我,大约与众多同辈人有着这样的共同情怀吧。
人生是段旅行,生命是段过程。二十岁前后的那段大好青春时期留在了昙华林。五十年前的昙华林,四年的大学生活恍如昨日,好多好多情景宛然如在眼前。
1959年的一个仲夏之夜,高考前一天,半夜三点,我在路灯下备考看书完毕回家。那时家贫,家里没有电灯、电扇,路灯下要凉快一些,回到家就悄然入睡了。怀揣着当作家、记者的梦想,因而那样刻苦、努力。虽然“及第”了,却被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录取了,于是在昙华林学习、生活了四年。当时华师的中文系、历史系设在昙华林。
那四年,一头一尾较好,中间却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十八、二十岁左右的年龄,正是身体发育的黄金之期,每餐是一瓢三合粉的“菜羹”(当然不会还有菜),常年吃不饱。吃完后,饭钵一般不需洗,在木桶里接点开水喝下。开水在钵子里晃荡几次,这样,钵子也就算是洗了,肚子也就可以灌饱了。加之隔壁有个“久安制药厂”,风一吹过来,难闻的硫磺味使人头昏(要是现在,早就会向环保部门投诉了),所以,四年中有三年头都是昏的。不过,我比许多同学幸运,没有像他们那样因营养不良而得肝炎。那是怎样的“困难时期”啊!难怪不少同窗早已“含笑九泉”了!
虽如此,大多数同学仍然是蓬勃向上的。那时,有对“苏修”“九评”的鼓舞,增强了大家共产主义的信仰;有“雷锋精神”的激励,培养了大家革命乐观主义的情操;当然更有母校的教育,树立了大家积极进取、蓬勃向上的世界观、人生观。所以,在课余不准看书、只能“劳逸结合”的“校规”管束下,很多人依然专心读书、写作,最终打下了良好的根基,成就了自己的一生,有的一生也不乏辉煌。人,是要有点精神的。
“石韫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大学使人成熟,使人充实。常言道:腹有诗书气自华。大学使人成为淮南的桔,而不是淮北的枳。人与人的差别,有时大于人与动物的差别,根本原因即在于教育与素养的有无。也因此,我对昙华林、对母校,是永远深深感念的。
四年中,我见过一次“昙花一现”。一个夏日的夜晚,听说隔壁“湖北中医学院里”的昙花要开,我们几个同学好奇而欣喜地结伴前往,半夜时分去的。医学院的花工师傅已将几盆昙花放置在大门进去不远处,花开得艳丽极了,好看极了,真不知怎么形容,实在难以言状。花叶如玉,像锦缎,又似翡翠。有诗道:“玉骨冰肌入夜香,羞同俗卉逐荣光。辉煌生命何言短,一现奇芳韵久长。”这首七绝诗也许可以赞咏“一现”的昙花吧。
这“一现”可以“现”多久呢?花工师傅告诉说:“要开三、四个小时。”昙花实际是“夜美人”,她只在夜晚开放。在夜色中,她漂亮地来,黎明时微笑着去。
昙华林正是因有昙花而得名的。华、花古今字,《诗经》里“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说的便是妖冶的桃树,盛开着红艳艳的桃花。“灼灼其华”就是“灼灼其花”。因而昙华林也就是“昙花林”。
离开昙华林半个世纪后,我与同年级的窗友们欢聚,“千里来寻故地”,可是,已“旧貌换新颜”了,那通向校园的青石板路没有了,那五月黎明飘香的槐花树也没有了,还有那校内古色古香的“文华楼”也不复存在了,哪里还听得到一小时一次的清韵悠长的钟声呢?哪里还找得到那熟悉的草坡、洗衣的古井呢?一切都“现代化”了。啊,曾留下我的书声、我的梦想的地方,再也找不到你、见不到你了!世间哪有什么永恒不变的呢?
我爱你,昙华林!是你让我成长、成熟、乃至以后成功的圣地。我心目中的昙华林,就是母校华师,就是华师中文系。
我爱母校,爱那些可亲、可敬、可爱的师友。人的一生,只要你志存高远,努力向上,至少有一次像昙花“一现”那样的辉煌。
拳拳之心、眷眷之意。说不尽对昙华林的思念。难忘昙华林!虽未实现梦想当作家、记者,而在教师岗位却也实现了自身的价值。人生得失难由己,自有梅香耐广寒——这是我的由衷之言、切身感受啊。
昙华林一辈子都在我的心中,在我的梦中。
(丁忱,1959年入中文系。武汉大学教授,日本爱知文教大学名誉教授)
漫忆昙华林岁月
【凌忠祺】
2012,金秋时节。教师节深夜。北去的动车上……黑黑的夜,静静的车厢,车轮滚动着,发出不间断的声响,列车风驰电掣向北而去。此时,躺在卧铺上的我却产生了错觉:列车好像穿越岁月时空,正载着我奔向一九五九——一九六零的昙华林……上午出发去北京前,袁巍学友来访,约我为昙华林写点东西,以纪念华师大校庆110周年。一提起昙华林,她就从我记忆的某一个深层的角落里象昙花一样冉冉升起。一整天直到深夜,大脑屏幕上全是昙华林。一九五九——一九六零的昙华林啊,我从桂子山走进多彩的大学生活,又从你走向幸福的教师生涯。虽然在你的怀抱里仅仅只有一年时光,但你和桂子山一样,留下了我生命中一段美丽而又奇特的印迹。要说写一篇文章,我一个字也不敢落笔,因为我无法将这一年的经历集中于一个鲜明的主题。如果是扯闲篇,漫天撒网,我却又可以讲好多关于你——昙华林的故事……毛主席“来了”
那是一个艳阳高照的日子,我们正在开团员生活会。突然听见有人大声呼喊:“毛主席来了!毛主席来了!”一时间,整个文华楼里“咚咚咚咚”,全是向楼下奔跑的脚步声。我和同学们一起冲出宿舍开始狂奔,下楼拐弯上坡,奔跑奔跑奔跑。身前身后左左右右全是人,除了脚步声,再也没有任何声响。跑啊跑啊,跑到中文系行政楼旁,就见许多人正往回走。“糟了,来晚了!”我正懊恼沮丧时,听见有人大声说:“谁在那里瞎咋呼?根本没有的事!”原来是以讹传讹呀。
正想着,听见有人叫我:“凌忠祺,你跑得好快呀!”我回头看是我们班体育委员:“按你今天的速度,劳卫制八百米达标没问题。”“真的?那我今天就算达标了?”听他这么一说,我赶紧高兴地叮了一句。他立即严肃起来:“不行!这不是正式测验。”“奇怪,你怎么能跑得这么快?”另一位同学问。“一点也不奇怪,她刚才的肾上腺素的分泌恐怕是已经达到极限了。伟大的动力产生巨大的爆发力嘛。”另一位同学发表他的高见。
是啊,从少年时代起,我就渴望有一天能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一九五三年得知斯大林去世的当晚,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和毛主席坐在一起,对面坐着的就是斯大林同志。醒来的感觉是又幸福又遗憾。遗憾梦境太短了,和毛主席在一起只坐了那么一小会儿。今天有机会见到毛主席,奔跑的动力自然是从未有过的大啰!
迈入“共产主义时代”
1958年某日——记忆里也是一个晴朗的日子,下午,南门水泥地坪上。同学们都坐在小板凳上,整整齐齐安安静静。一位学生干部正在前面激昂慷慨地演说。现在还能记住的是这么几句话:“从今天开始,我们就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了!中国,从此迈入共产主义时代。”“各班都要成立共产公社。”(好像是这个名称)“每个同学除生活学习的必需品,多余的东西都捐给共产公社。”
听见今天进入共产主义时代,会场有小小骚动,但没有欢呼声掌声。从一九五八年至一九五九年,我们听到的大跃进放卫星的信息很多,已经习以为常,不再欢欣鼓舞是很自然的。而这一次没有热烈反响恐怕就不是“习以为常”能概括的了。我想,当时许多同学的内心反应是和我一样的。一开始我蒙了,紧接着就质疑:“这也太突然了吧?共产主义社会是需要物质的极大的丰富的,那样才能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现在我们连吃饭穿衣都要凭票证有限量。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和我们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不是相差太远了?”又想:“也许这说的不是物质上而是精神上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吧?”
回到宿舍,清理东西。衣服?就这么几件,不可能捐。饭票?刚刚够用,也不可能捐。掂量来掂量去,最后只好忍痛割爱,将我的一把崭新的秦琴和几本心爱的小说送到我们班共产公社所在地,也就是我们班最大的那间男生宿舍去了。一看,两排桌子上摆的全是书和乐器球拍等等。心想:这是建共产公社还是建文体俱乐部?
这以后,我没再去过我们班的共产公社,记忆里共产公社也没有组织过什么活动。一九六零年夏天我毕业了,离开了昙华林,也不知道我心爱的秦琴被何人“各取所需”了。
大别山采风
1960年的初秋时节,我背上简单的行囊和同学们一起去红安县采风。往届的同学四年级上学期去中学实习,我们这一届改实习为采风,去老苏区接受革命传统教育。
我们小组去的地方是红安七里坪,这里是董必武的家乡。参观了董老故居开过了座谈会,第二天便按公社的安排采访军烈属。吃过早饭就下乡,中午在采访对象家吃饭,天快黑时赶回公社招待所吃晚饭,晚上整理采访资料。
我第一天采访的对象是一位参加过“黄麻起义”的老人刘爷爷。他家只有祖孙三人,孩子们大约五六岁。老人一谈起当年的革命斗争就变得神采奕奕。我这个土生土长的武汉伢,第一次下乡又是到了向往已久的革命根据地,亲耳聆听革命老前辈讲革命斗争史,兴奋激动是很自然的。但吃中饭时,这份兴奋激动便搀和进了别样滋味。刘爷爷端上一盆黑乎乎的东西,告诉我这是菜粥。将青菜野菜剁碎再加一点点米煮成的。刘爷爷给我盛了一大碗,我喝了一口,味道很怪,难以下咽。再看看因为瘦骨伶仃而眼睛特别大的两个娃娃和额上的皱纹如刀刻斧凿的刘爷爷大口大口似乎吃得很香很香的样子,我的眼泪便不由自主地涌了出来。是难过的泪也是愧疚的泪。想想我们这些大学生,连女生一月也有二十七斤粮食定量供应,天天白面馒头白米饭,还嫌菜里油太少。我饭量小,每月还可以省下两斤粮票支援男生。我没有挨过饿。这次来到红安七里坪,在招待所早晚也吃稀的,但毕竟还是白米粥。做梦也想不到老苏区的人竟然是在用野菜充饥了!当我将一毛钱一斤粮票放到桌子上时,刘爷爷赶忙说:“不行不行,有规定的,只能收二两粮票。”我把粮票硬塞到刘爷爷手里,老人收下粮票就像收下了一块金元宝。一只手攥紧了粮票,一只手抹着泪眼。
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在七里坪的这一段时间,的确一到半夜肚子就唱咕咕歌。有时,我们也相约去公社供销社买葛根粑粑充饥。现代人推崇葛根的营养价值,将葛根磨成又细又白的粉再精包装,就成了上等的礼品。我们吃的葛根粑粑那是又苦又涩又硬的。
生活确实很清苦,但我们没有怨言。我们相信困难是老天爷是苏修制造的。我们更相信,有毛主席党中央,大饥荒很快就会过去,社会主义祖国的前景很快就又是一片光明。我们在油灯下奋笔疾书,每一个人都完成了一篇自认为不错的习作。我的习作是短篇小说《革命的火种》。
别开生面的化装舞会
一九六零年,恰逢“人间四月天”,昙华林草长莺飞。中文系举办了一次别开生面的舞会——化装舞会。不是每一位参与者都要化装,而是要求每一个年级要有一个或两个有主题的化装群体。我们年级选择了“国际青年联欢节”的主题。参加化装的同学,高个儿的扮苏联人欧洲人和蒙古族新疆少数民族;小个儿的扮缅甸柬埔寨等国人和朝鲜族西南少数民族;还有几个人扮非洲黑人。真是五光十色绚丽多彩。我因为忙着帮同学们搭配服饰,自己反而就什么民族也没扮演。只穿了一件白色的长袖衬衣一条碎花短裙,白色短袜黑色布鞋。结果是成了中国女大学生的代表。其它年级也都有精彩的化装。
我们是最后进入会场的。六人一排手拉手,在《青年友谊圆舞曲》的前奏中步入会场。一看见我们四十八人组成的炫人眼目的队伍,会场便响起热烈的掌声。大家和我们一起高唱“蓝色的天空像大海一样,广阔的田野上尘土飞扬,穿森林过海洋来自各方,千万个年轻人欢聚一堂……”我们边唱边以轻盈的舞步快速变换队形。当我们最后变成一个单环时,四周的同学就自发地拉起手将我们包围,他们的外面又很快形成一个更大的圆。三个圆圈以三拍子的交换步跳起一种最简单又最热烈的集体舞。伴奏的速度愈来愈快,我们的舞步也愈来愈快。嘭嚓嚓嘭嚓嚓,所有的人都在忘情地舞蹈着欢笑着。
开始跳交谊舞了。慢四中四中三快三,一曲一曲又一曲。一小时后,同学们特别喜欢的苏联歌曲将舞会推向高潮。流畅轻盈的快三步舞曲一对对舞伴的飞快旋转让舞场变成了波涛起伏的海洋。来者不拒,谁请我我都跳,真想跳一个通宵。要知道,这是我们五六级同学在母校在美丽的昙华林参加的最后一次舞会了。
终场舞曲响起,那是让人荡气回肠的苏格兰民歌《友谊地久天长》。约我跳最后一曲的是王洪玉,他和我四年来一直是院系舞蹈队队员。我们一边舞着一边回忆着在桂子山在昙华林在中南民族学院大礼堂在草埠湖农场的一次又一次激情飞扬的表演。当提到舞剧《明天》夺得中南地区大学生文艺汇演冠军一事时,我的心在一瞬间颤动了:日月如梭,岁月飞逝,而那逝去的又是何等的珍贵啊!
激情颂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