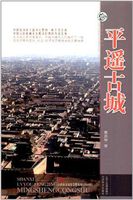月桂走到当街时,那几个晒太阳的老没牙,脸全都葵花盘似的转过来,没个遮拦地看她。月桂知道自己的模样惹眼,刚刚又打扮了一番,他们不这样看,反倒有些怪了。可她心里正烦着,停都没停,便匆匆朝村口走去。
没几步,又碰到几个站街的女人,目光都酸溜溜的,带了些审查的意思,好像在说,这狐狸精,挺了两个大奶子,又要去会老相好了吧?若在以往,月桂会觉得这刻薄是她们对她的一种嫉妒,但现在,她心里却没了底,一点都不觉得自己有什么比别人好了。
这其实都是因为那个人,因为他的冷落。
这会儿,月桂就是要去问问他,怎么忽然换了个人,都一个月没露面了。出了村口,她听得自己的手机响了起来,她以为是那个人打来的,赶紧按键接听。刚刚在家里,她打电话约他在老地方见,他支吾了半天,老大不情愿地应下了。这会儿,他把电话打过来,是不是又要变卦?她喂了一声,听到的却是男人天成的声音,不由怔住了,这家伙常常半月二十天没个消息,让人怀疑他是不是死在工地上了。有时她实在憋不住了,把电话打过去问个平安,他说不了两句就让挂,说还是省着点吧。这会儿她急着要去见那个人,他却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冒了出来。
你咋想起给我打电话了?月桂问。
也没啥,这两天我老做噩梦,眼皮突突突地跳,总担心家里会出事,你和娃们都好吧?男人吭吭哧哧地说。
你到底怎么了?老也不来个电话,来了就说些不吉利的屁话。你说我和娃们能有啥事?
没事就好,我也就是随便问问,那挂吧。
挂了电话,月桂又觉得这么做有点过火,远天远地的,男人再怎么有错,也不该对他太冷淡呀。忽然想,天成是不是猜到了什么,故意拿话套她呢?不可能,他那么粗心,能猜到她想什么吗?他真要这么细心,体贴,她也不会跟那个人好上了。管他呢,猜到就猜到了,想离就离,想散就散吧,反正怎么着也是个守活寡。就又想到了那个人,这会儿他到底起身了没有?会不会来见她?这个可恨的家伙,他究竟有什么好的,竟然惹得她日思夜想,老像丢了魂呢。近一段时间,她老这么问自己,把这个男人在心里颠过来倒过去地看,从头看到脚,又从脚看到头,好像连他身上有几根骨头都想看个清楚。想着,眼前又跳出那个人的样子来,他不抽烟也不喝酒,牙很白,笑起来泛着玉一样的光泽。有时候她会在心里感叹,真是个玉一样的男人啊,可眼下这块玉却不再温润了,石头一般硌着她的心。
以前,她和村子里别的人一样,把他看得很神秘,和他好了一段时间后就不这么看了。每当有人提起他,说他在镇大院如何如何的勤恳,如何如何的待人热情,又如何如何得到头儿们的赏识时,她就在心里偷偷笑,笑这些人没看到他内里的东西。他虽是个小秘书,却会像魔术师一样变戏法,手里扯着一块红布,三下两下就把你的眼蒙住了,让你不知道他究竟站在你的对面,还是背后。这个男人太有城府了,让人很难看透。
想着,月桂又给他拨了个电话,问你起身了吗。那个人支支吾吾地,还没,给点小事绊住了。月桂就变了脸色,有事,你总是有事,你到底来不来?那个人说,我真的有事,要不改天吧,改天我们再约个时间。月桂狠着声说,你听好了,今天要见不到你,我就找到你家里去,把我们的事跟你老婆挑明,我说到做到,你信不信?
你疯了月桂,你想毁了我吗?
我是疯了,你怕毁了,那就赶快来!
好好好,我这就去。
月桂听得出那个人言语里的勉强,她知道他不高兴,可这会儿她什么都顾不上了,今天要见不到他,说不准她真会疯了呢。但就算真的疯了,她也不会找上他的门,她早不是小姑娘了,不会死缠硬磨拆了他的家。她有男人有孩子,男人没出息却也没过错,更何况还有北大清华两个孩子。两个孩子都挺机灵,她爱他们,不想让他们失去妈妈,失去家。所以,她早就断了嫁给那个人的念头,只是想暗暗守着他。她那么说,也就是想吓唬他一下,没想到他真的吓坏了,没准尿了一裤子呢。这,这是她当初看上的男人吗?
月桂心里喧嚣着,步子也加快了,虽然她知道那个人不会来得比自己早。
她朝秀才山脚下的那座老瓜棚走去。
老瓜棚是公公搭起的,她没嫁过来时就有了,多少年风吹雨淋,破得都不成个样子了。老人是种瓜的好把式,种了一辈子西瓜,八年前一蹬腿走了后,这一片地再没种过西瓜,瓜棚跟着就荒了。老人本来希望这点手艺能传下去,但天成根本不愿承继,他认为西瓜就是西瓜,怎么种也是西瓜,硬是跟着人进城做工去了。月桂并不希望男人进城做工,动点脑子把西瓜种好也不是赚不了钱,可好说歹说都没用,只能由着他去了。或许是为了报复天成,她把和那个人的约会地点选在了瓜棚。那个人却总想着他们的第一次,想把她拉到狼窝山脚下去,抱到车上,说那样才刺激。她不肯去,说这不好,一点都不好。那个人问怎么不好了。她说没个房顶不踏实。其实她是觉得那样太放纵了,她不敢想象自己一双腿探出车门的样子。
拐了一个弯,就看到老瓜棚了。
秋天才刚露头,瓜棚四周的玉米绿油油的,都快把人掩住了。月桂走到棚前,迟疑了一下进去了。炕上铺的麦秸还在,灶前那一堆玉米秆也还在,这是公公过去守夜时烧炕用的,没用完,一直没人动。灶台上方有个小洞,洞里还放着盒火柴,也没人动。好久没在这里亲热了,但她好像还能嗅到什么味道,瓜棚的味道,时间的味道,还有属于他的微咸的虾皮味。她使劲挥了挥手,好像要赶走什么似的。但怎么也赶不走,她摇了摇头出来了。她立在瓜棚前,看着夹在两片玉米地之间的路,好像她是来看瓜的,或者是照看这一片玉米的。但是假如有人路过这里,一眼就会看出她是来等人的,可这又怎么了?现在她什么都顾不上了,就算给人看到又怎样呢。
她不明白自己今天怎么就控制不住了,全身的每一根骨头好像都成了干柴棒,一根火柴就点得着。
这时候,她的手机又响了。
是那个人打来的。
月桂,还是改天再见吧,我真的有事。电话里的他赔着笑说。
你怎么没一点男人样了,改天,改天是哪天?你不来我就把这瓜棚烧了,把自己也烧死,死给你看!月桂几乎吼起来。
你别乱来啊,我这就去。那个人说。
挂了电话,月桂心里酸酸的,想哭,又哭不出来。
脚下是一片细软绵白的沙子,当初为了把西瓜种好,公公赶着驴车从几里外的沙沟一趟趟地拉沙,一直拉了半个月。据说铺了沙,旱坡地就蓄水,雨水想蒸发也蒸发不了。月桂盯着这片沙子,慢慢蹲下来,伸出一根指头在上面写那个人的名字,写一个抹掉,再写一个,又抹掉。写得没劲了,又开始画,画那个推三托四的男人,潦潦草草几笔,就是一个他,觉得不像,抹掉了再画,再画再画再画。一开始,她画的那个人还是两条腿,后来呢,两条腿中间就多出了一条,中间的这条老画不好,像腿,又不像,但她认为这就是腿。画出后,她心里又有些吃惊,怎么就多出一条腿呢?每个人不是只有两条腿吗,怎么她画的他就多出了一条?她希望他有三条腿吗?三条腿又暗示着什么?是希望他更稳定,更可靠吗?她实在想不清楚。
记得第一次见到那个人,是在两年前,他陪人进村搞什么普查。进了她家,他没说几句话却一直盯着她看,看得她有些不好意思,也不敢去看他。
临走时,他趁着别人不注意给她留了个手机号,说也许以后用得着。村子太空了,她的心也太空了,有一天她真的给他拨了个电话,她说你不忙的话,带我四处走走吧。他开着车轰隆隆来了。他说我知道你会唤我的,我一直等着这一刻。他拉着她在这一片火山之间行走,一路上滔滔不绝,没一点生分,似乎他们老早就相识。后来,他刹住车,一把将她揽进了怀里,好像她原本就该属于他。他不停地在她耳边低语,他说,知道吗,第一次看见你,我就想得不行了。说着,他开始把她往车后座上抱,她知道他要干啥,挣扎着,但最终没抵住他,把自己打开了。她汹涌在他的波涛里,喊叫,扭动,甚至把这边的车门都顶开了。那以后,他就在她心里发了芽,生了根,繁茂起来了。
有一次在瓜棚里会过后,她说你究竟喜欢我什么。他指着她的胸说,就这两座雪山吧,做梦都想爬。她打了他一下,你想得太具体,我可是想着你的一切。她知道,他们的爱从一开始就不公平,现在,他连这点可怜的爱都不想给她了。他在她的灶里添了那么多柴,让她燃烧起来,现在,又开始一根一根往外抽柴了。
那边有车声传过来,轰隆隆的。
一听这声音,月桂就知道是那个人来了。
她站起身,看到了夹在两片玉米地中间的那辆破桑塔纳车。她曾经问过那个人,为啥不换辆车,他说就我这个级别,只配开这种车了。就是能换辆稍好点的,最好也别换,做人要低调嘛。车离着越近,她心里越不安,不知道他过来后会发生什么。她甚至想躲开他,躲开了也许什么都不会发生了。但她却没躲,看着那个人开过来,在离她十几步远的地方停下,又把车头掉过去,熄了火,一推车门钻了出来。她注意到他没去把车藏到那边的林子里,以往,他再急也要先做好这件事,说让人看到就不好了。看他这样子,好像是说几句话就要走。
月桂心一沉,不再看那个人,把身子朝这边扭过来,一低头,又看到了自己画的那个人,三条腿的他。她本来想用脚把这画擦去,至少擦去中间那条腿,但脑子里忽然划过了个念头,假如他答应以后好好待她,那就让这画留着,假如不是这样,就擦掉它。那个人走过来了,两只手从背后环住了她的胸,嘴也凑了过来,你急着叫我来,想了吧?
别碰我,你别碰我。月桂努力从他怀里挣出来。
我又不是狼,有这么可怕?那个人笑笑,又摇摇头。
你从来就没个正经,一见面就动手动脚的。
不能吗?你可是我的女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