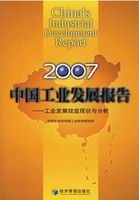每页文件上面都标示着"X"记号的地方,就是要我签名的地方。但要是真的签了,那表示什么?我无法相信萨莉得了精神病,我打从心底抗拒接受这项事实。萨莉会接受什么治疗,我清楚得很: 瓶瓶罐罐的精神安定剂、脑部化疗,药吃下去会有什么后果,我当然也知道,人人都心知肚明。我不敢想象萨莉变得那般迟钝愚笨的样子,像隔着窗户看世界,好厚好厚的窗户,犹如出租车或烟酒专卖店用的防弹玻璃,上面还布满刮痕。
"医生,给我一分钟。"
"要多久都没问题。"
我还是希望可以想出办法带萨莉回家,于是回到诊疗室找帕特商量。护士正在替萨莉抽血,针头移开时有一滴血不巧滴到萨莉衣服上,留下鲜红色的椭圆血迹。"看你做的好事!擦掉!帮我擦掉!"她把衣角凑到护士眼前,证明对方犯下滔天大罪,表情一副要杀人的样子,仿佛这滴血像老鼠屎,坏了她所有的努力,玷污了她的理想、她的纯洁。她全身都在剧烈颤抖。我恍然大悟,原来萨莉的所作所为,无非是要战胜惶恐;但她胜得惊心动魄,且这份胜利是如此脆弱,以至于这一滴血的出现,让她对这场胜仗起了疑窦。她感觉自己快要完蛋了,这滴血是玫瑰花萼里的害虫,妨碍花朵盛开。萨莉绝不容许这种事发生。
"帮我擦掉!"她呐喊着,仿佛这滴血会赔上她的性命。
"自己擦吧,大小姐。"护士说着,面不改色,顺手把刚刚抽的一管血放进口袋,走出病房外。
墙壁的金属架上有一筒卫生纸,帕特撕下一张,沾点水擦拭血污,擦着擦着晕开成一片绯红。
萨莉继续放声尖叫。
我叫她闭嘴。
帕特抬起头,满脸疲惫,充满困惑,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
有那么千分之一秒的时间,萨莉用陌生的眼神盯着我,突然,尖叫声毫无预警地转为哀婉,变成歌剧里的悲剧唱腔。"我父啊,可怜的父亲啊,快找回你心中的天才吧,只要跟着我,来我这吧,我就在这里,就在你眼前。"她用夸张的动作,以手背轻抚着我的脸颊,然后她痛哭了起来。
我接受事实,填妥同意书,谢谢医生体恤我。她说小事一桩,快去挂号柜台交医疗保险卡。
医疗保险卡。经过一整天混乱下来,我根本无心顾及医疗保险卡这种小事,帕特最近刚离职没教跳舞,我们的医疗保险也已经过期了,当时认为眼前不会有什么重大变故,所以连月来都在物色新的保险公司,谁晓得灾难早在一旁伺机等候。公寓的书架堆了一叠保险说明书,积满了灰尘。
"没保险?什么都没有?"柜台的人员问。
我转向医生求援:"不管医疗费多少,我到时一定付给你,我说话算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