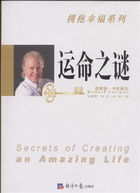§§§第一节 山西地区崇商的社会文化
山西民俗以商为重,重商习俗特别强烈。平阳府、泽州、潞安府、汾州所辖各州县,特别是浦州、曲沃、高平、沁水、长治、汾州、介休、洪洞、临县等晋南地区,这种重商观念在明代后期蔚然成风。蒲州外出经商居民,明代已达十分之九,“商之利倍农”。不少地区“民逐于末作,逐利如鹜,而又无富之实,有富之名”。争相从商求利致富,以富为荣,以贫为耻,甚至还出现了不少有名无实的富翁。很显然,重商崇富已成一方风尚。许多地方历史文献记载了平阳府、蒲州、汾州、泽州、太原府所辖各县“多商贾”、“重贸迁”、“罔事本业”、“去本就末”的习俗。
自明代中期起,政府某种程度上放宽了“重农抑商”政策,商人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社会舆论也有所转变,自古多商人的山西,变化尤为显著。特别是嘉靖、隆庆后,山西不少地主越来越热衷于工商业,弃地而从商;一些知识分子也违背“圣贤”教导,弃仕而从商。由于省内从商的很多,重商风气也随之浓郁起来,于是人们又形成了这样一个观念,即:荣光莫过于经商。所以,晋中有“生子可作商,不羡七品空堂皇”,“好好写字打算盘,将来住个茶票庄”的谚语,这就是最好的证明。纵使经商者要栉风沐雨,奔波四方,跋涉万里,常年背井离乡,但当地不少女子并不以“商人重利轻别离”为然,甘愿以身相许而受多年分离之苦。祁县、太谷、平遥等赖商为生的比例,在许多村庄里近成年男性之半。忻县、定襄、汾阳、孝义、临汾、侯马、永济等县经商的人数也很多。因此,山西当时有“以商为本”的说法。清代重商习俗更甚于明代。传统的中国人中,名利相较利重于名,因此长辈将上等人才送去经商,而将“中材以下,送去读书应试”,这种重利轻名观念,可以说已与耕读传家、重农贱商的观念大相径庭。曲沃“重迁徙,服商贾”。高平县四郊出现“东务农,西服贾”的地域职业分化。夏县“居民争趋商贸,每年新谷登场,只留一家口粮,余粮全部变卖,以充资本,外出贸易”。运城位于解州、安邑之间,地处池盐产地,五方杂处,富商大贾游客山人骈肩接踵,居民争趋盐利,外出经商。安邑富翁中,运城人超过一半,运城商民“或以科第奋进,或以货郎起家,是亦晋省一都会也,于是商民相习成风,贫富相耀成俗,乘坚策肥争奢斗靡”。
晋商之所以能称雄商界达数百年,这与山西地区普遍存在的重商贱儒、求富逐利的社会风气是分不开的。这种重商风气与中国传统的重农抑商的士农工商观念格格不入,甚至还为最高统治者所关注与探讨。雍正二年(1724年)九月。大臣刘于义奏称:“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至中材之下,方使之读书应试。”雍正皇帝深表赞同,朱批道:“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犹肯力农,再次者入营伍,最下者才令读书。朕所悉知。”在清朝,山西许多府县应试科举的人数呈明显下降趋势,以至于参加人数不足上榜额数,令地方官府大为头疼。皇帝重臣也在国事决策和奏谕中郑重其事地加以讨论,可见山西重商轻儒的社会风尚在忤逆中国传统观念的轨道上走得多远。但他们不会明白,山西人之所以迷恋于商贾末业,起初是被三晋地区恶劣的生存环境逼出来的。
山西地方贫瘠,土不养人,从晋商的几个主要故乡看,均存在这一生死攸关的问题。蒲州位于河曲,明代已呈现“土陋而民伙,田不能以丁授,缘而取给于商计,其挟转资牵车牛走四方者,则十室九空”。泽州“其地在万山之中,险狭而硗薄,民力田勤苦,岁获不及他郡之丰,故土俗自古称纯俭,其势然也”。总之,“山西土瘠天寒,生物鲜少”,仅仅依靠耕种土地无法获得温饱,这是晋民远走他乡谋生求利的原因。但是,晋南一带气候土质均优越于晋中、晋北,为什么外出经商的也会这么多呢?因为晋南自然条件也无法与华北平原相比,加之人口密度高于晋北,“盖其土之所有不能给半,岁之食不能得,不得不贸迁有无,取给他乡”。
当生存的起码条件都不能达到时,脚下贫瘠的黄土地,还有什么可以让人留恋呢?是恪守古训,困穷故土,还是背井离乡,闯荡天下?许多山西人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后者,远涉塞外进行易货交易,下江南购进棉布,出关外销售铁货。风餐露宿,日夜兼程,商业资本一点点地积累起来,一个地域大商帮就在他们匆匆的步履与辘辘的车轮声中不知不觉地诞生了。可以想见,在这些最早背井离乡、出外贸迁的山西人背着鼓鼓的包裹回到家乡,不作声张地建起了鹤立鸡群的北方大院时,会在村子里引起多大的轰动。他们的发财经历会成为同村人长期津津乐道的话题,他们还会成为不安现状的年轻人模仿的典范。是的,当通仕与务农都没有什么前途与指望时,列为末业却能带来财富的商贾就具有莫大的吸引力了。就这样,在求富逐利的强大动力驱使下,几千年重农贱商的传统观念不堪一击地败下阵来。封建社会里最受尊崇的“士”,山西人却看得一文不值,“最下者方令读书”,招致许多读书子弟也弃儒从商,趋之若鹜。这种民风,令不少寒儒迂士为之痛心疾首:“近来吾乡风气大坏,视读书甚轻,视为商甚重,才华秀美之子弟,率皆出门为商,而读书者寥寥无几,甚且有既游庠序,竟弃儒而就商者。亦谓读书之士,多受饥寒,曷若为商之多得银钱,俾家道之丰裕也。当此之时,为商者十八九,读节者十一二。余见读书之士,往往羡慕商人,以为吾等读书,皆穷困无聊,不能得志以行其道……”
在这种民风影响下,才华出众的年轻人纷纷踏入商途,为日益壮大的山西商帮源源不断地补充着新鲜的血液,他们观念新颖,勇于开拓,目光远大,视野开阔,继承了前辈商人的成熟与精明的经营策略,摒弃了其迟缓与保守的经营方式,抓住机遇,不断拓展商业活动空间与经营品种,把山西商人的事业一步步推向新的辉煌。和其他地域商帮相比,晋商在商业资本规模、经营活动区域、经营品种等方面都远远超过了他们。像介休侯氏金融帝国、祁县乔氏“在中堂”商业金融集团等家族企业,不仅在国内商界独占鳌头,即使与当时的欧美大公司相比,也毫不逊色。难怪当时人感叹,山西是“县县皆商,人人皆贾”,贫瘠的黄土地却蕴积了厚实的商业精神,走出了一个令世人惊叹的庞大的地域性商人集团。
虽然山西地方风俗向往经商,他们对经商持积极态度,绝不以经商谋利为耻,甚至引以为荣。他们读书做官不成,往往欣然弃儒从商,经商致富的成就甚至可以和应试为官相提并论。不过生活在封建社会的晋商,也不可能全然不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他们并非完全不关心仕途问题,晋商中考中进士或举人者也有人在。据《两淮盐法志》载,明代陕晋商人及其子弟进士及第者共有三十七人,其中原陕西籍者二十九人,山西籍者八人。可见晋商对进入官场以求显贵也非毫不动心,但其程度尚不及陕西商人。对他们来说,求得官位是事业成功的荣耀,当然也会为他们的商业活动带来多多少少的方便与利益,但为官思想却比其他商帮淡化许多。晋商中为官者比徽商要少得多,而且几乎没有人做到总商的位置,他们对做官不积极,与官府关系也不密切,如范永斗对送到头上的官都坚辞不就,后来做洋铜生意赔了本,拖欠下大量官银,终于被官府抄家,难逃破败的下场,也许与晋商的这一特色不无关系。正由于晋商重视专一经商,传统轻商观念淡薄,他们的开拓精神也较强。从地域上看,他们不仅远涉日本,还往北发展,一直把生意做到莫斯科,而且为适应社会经济发展,还创立了票号,开中国封建时代经营汇兑业务之先河,大大促进了商业贸易活动的发展。
在重商观念流行山西之际,作为地方思想文化代表的士大夫阶层,亦受到很大影响。一是诗书之家眼见在商潮中暴发的富商大贾,气象辉煌,不免产生艳羡心理,不得不降低身份,进入他们的交际团。另一种影响是读书不成,又不屑稼穑,去而经商。明成化平阳府商人席某,“幼时学举子业,不成,又不喜农耕,曰,丈夫苟不能立功名于世,抑岂为汗粒之偶,不能树基业于家哉”。经商发家成为建立家族基业的终南捷径,因此读书人趋之若鹜。
由此可见,明清山西重商观念的深入人心,不仅造就了一大批中国巨商首富,而且对缙绅地位发生了动摇作用。重商观念无疑是对传统重农轻商观念的背离,它有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是一种进步思潮。
§§§第二节 徽商的企业文化
南宋时期,徽州是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的桑梓之邦。朱熹原籍婺源,外祖父祝确,歙县人,为当地富户,人称“祝半州”,意思是他家的财产可当徽州之半。朱熹小时候受到外祖父的教育与培养,后来便常回故乡传播理学,在徽州影响极大。元、明时期,徽州人大多“喜读朱子之书,取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对朱熹几乎是顶礼膜拜。尤其是理学所宣扬的伦理文化,渗透到徽州人的心灵深处,朱熹手订的《文公家礼》,是徽州人所崇奉的信条。此后,徽州的文化,便打上了“朱子”的印记。徽州的各姓家谱,在有关“家规”、“家训”中,无不都提到朱子《家礼》,认为《家礼》所规定的“冠、婚、丧、祭诸大典,炳如日星”,要“遵而行之”。诚如光绪《婺源县志》中所说的:“自朱子得河洛之心传,以居敬穷理启迪后人,由是学士争自濯磨以冀闻迢,风之所渐,田野小民亦皆知耻畏义。”
明清时期形成的“徽州文化”,它因袭了六朝以来的传统文化,而“朱子之学”更是渗透其中。“新安理学”直接肇自朱子,所谓“文公为徽学宗传”,那是合乎事实的。同时,一些社会制度文化也是与旧时的制度文化一脉相承。此外,由于徽州商帮的崛起,以商帮为“酵母”而出现了商人文化、园林文化、建筑文化、绘画艺术文化、戏剧文化、篆刻文化、饮食文化等等,这给徽州传统文化又增添了新的内容,表现了时代的特征。但上述新形成的文化,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以往包括朱子思想在内的传统文化的影响。
徽州商帮作为一方地域的商人群体,之所以能在历史上对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贡献,有不少人“五年而中(贾),十年而上(贾)”,很快致富发家,有一些在商界同行业中成为“祭酒”即首领人物,这都是与这个商人群体的文化素质和思想素质较高密切相关的。
宋元以来,徽州便是一个“文献之邦”,书院兴起,文风特盛。所谓“虽十家村落,亦有讽诵之声”,并非夸饰之词。徽州商人生长于这种社会环境中,他们大多数人自幼即入学就读,其目的多是为了追逐于科举仕进之途。其后,或因中试不第,或因家道中落,或因子承父业等等原因便转而从商。因此,在从商之前,有不少人便饱读了经史百家之书,粗通翰墨。有些人在经商过程中,还是“经史子集环列几前,至老未尝释卷”。可见,徽商是一支有文化的商帮,有的既是商人,又是文人。这支商帮的一个重要特征,便是“贾而好儒”、“商而兼士”。早在明代,就有人称徽商为“儒贾”。所谓“儒贾”,大致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徽商多是“业儒”出身,是有文化的商人;二是指徽商以“儒道”经商,即以“儒学饰贾事”。“儒贾”二字,反映了徽商的文化素质和经商的思想素质,也是徽商不同于其他商帮之处。
文化素质和思想素质是有密切联系的,甚至可以说,文化素质是思想素质的基础。文化素质较高,其思想素质也必然是很高的。“多才善贾”,自古皆然。不仅经商需要这两方面素质,即使百工技艺也是一样。尤其是在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社会分工不断发展,商业联络网日益扩大,商品与货币的运动错综交织,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行将接轨,商业竞争也日趋激烈。在这种形势下,商人的文化素质和思想素质较高,就有助于分析市场行情,预测供求关系的变化,从而在取予进退之间不失时机地作出判断,以能在商潮逐浪中扬帆前进。这在徽州盐商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徽州盐商是这支商帮中最富有的商人。他们当中“藏镪百万”者比比皆是,有的竟至“以千万计者”。因此,盐业乃是徽商经营行业中的“龙头”行业。但是,从事盐业经营,必须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和分析能力,这是因为:
其一,盐业从汉代以来都是国家经营的行业,自唐宋以迄明清,国家财政收入,几乎是“半出盐赋”。因此,国家设有专门机构管理盐业,掌管盐课。而盐政衙门的官员都有一定的文化知识,盐运司的最高长官盐运使,在明清时期大多是进士出身,有的乃是饱学之士。其时,“行盐之法”主要是“官督商办”,“商”与“官”交往甚密。盐商特别是总商、大贾,经常出入于盐政衙门,就必须有一定的文化知识,才与盐官有共同语言,共同的兴趣,甚至成为与盐官唱和往来的诗文之友。从这个角度来看,文化知识便是盐商通往盐政的桥梁,是“官督”与“商办”之间一条隐形纽带。
其二,正是由于盐业官营,所以,国家对盐的生产、贩运、销售、课税,都有较完备的政策规定,这就是盐法。而且随着时代的不同,形势的变化,盐法亦常因革损益。而经营食盐的盐商,就必须熟悉盐法。不仅要熟悉“本朝”的,而且还要熟悉历代的。只有具有较高文化知识的商人,才能读懂盐法,依法行盐。有时盐官要和盐商讨论历朝盐法的利弊得失,盐商还要提出合乎事实的见解来。
徽商因是“儒贾”,所以,他们经营商业也是恪遵“儒道”。以“儒道”经商,其特点就是:非义之财不取,非义之利不求。徽州商人虽然也希望能“快快发财”,但由于他们从小就受儒家学说的熏陶,所以,除少数被人斥之为“徽狗”的以外,绝大多数人在经商过程中,是比较讲究以义为利、以诚待人、以信接物的,所谓“本大道为权衡,绝无市气,协同人于信义,不失儒风”。有的人则明确地表示:“职虽为利,非义不取也。”商人而有“儒风”,反映在商业道德上首先是甘当“廉贾”,不谋暴利,不缺斤短两,不售假货,不坑害顾客。其实,这“儒道”的本身,就是商品价值的一部分,是由文化知识和商业道德融合在一起的无形价值。徽商中的不少“上贾”、“中贾”,就是凭这无形价值指导经营活动而发家致富的。把“儒道”引用到商业经营中,不仅只是当年的徽州商人,即在今天我国周边的一些国家,也以“儒道”发展经济,以“儒道”兴国,而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第三节 民营企业的文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