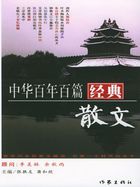那天晚上,我和妻子去听于丹讲课,因等公交车结果迟到了几分钟,进大厅时,于丹已开讲了。我从落座那刻起,她那清亮带磁性的嗓音就牢牢地抓住我的心。她的口才真好,不是一般的好,是相当的好。她能不停地讲,不重复地讲,生动,有趣,煽情,就是下面传纸条上来也没停下来,一场报告一个半小时一气呵成。她讲得有条理、有故事、有哲理、有警句;有亲和力、有吸引力、有感染力。她记忆力惊人,没有讲稿,能记得那么多例句,记得那么多名言,孔子的、庄子的;儒家的、道家的,苏东坡的、王阳明的。没有多年来的扎实积累,仅靠天赋是做不到的。她喜欢用的词汇是“圣人”、“君子”、“当下”、“担当”、“笃信”、“有理由”。也许是当老师的习惯,她不习惯那种作报告式的坐着讲,站着讲更有激情、更有风采。她从古代讲到当代、从名人讲到百姓、从箴言讲到哲思,用事例来说明道理、用典故来论证观点、用感悟来呼唤心灵。随手拈来,恰到好处。精彩的演讲结尾总是最精彩,她用了“岁末流光将尽之时,有理由憧憬江西来年更好,憧憬每一个人的生命气象辽阔博大,自由欢乐……”很文气的词句,掌声骤响,长久不息地。她不知道,省委书记作为一名普通听众坐在大厅中央,最后结束时才在后台和她见面,说一声:很精彩,谢谢!
于丹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是中国古代文学硕士、影视学博士。是央视百家讲坛解读《论语》让她一炮走红,以后陆续出书,进入中国图书排行榜前列并翻译成30多语种文字世界各地发行;她到各地巡讲,包括给各级领导干部,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形象大使走向东西方。我认为,于丹走红有她的理由,首先当前精通古典文学的专家不多,在读点经典、用经典拯救国民道德、提升文化素养的大趋势下,她的成名是顺势而上再自然不过了。还有,她的确是个人才,罕见口才加渊博知识,再加机遇,一不留神就冒出来了,就这么简单。红得过快富得也快的人,总是遭人妒忌。网上有人说,于丹是用山寨版通俗手法来解说《论语》,是亵渎了经典。并有10名博士要联名起诉于丹。且不说博士起诉于丹的动机是否借名人来炒热自己,也不说当今的博士特别是新世纪以后评上的肚子里有多少货(我曾当过几个类别的省高级职称评定委员会的评委,知道有些正高职称的人是名不副实的),仅对一个传播中华传统文化、拉近时代与古典的距离、促进东西方文化对话的人苛求,并要法办,这只有在当下中国才会出现的怪事。博士们应该清楚:“过分的苛责,不如宽容的力量更恒久。”“君子的力量永远是行动的力量,而不是语言的力量。”“要本着平等和理性的态度去尊重每一个人。”这些不是作者的观点,而是于丹读经典的感言。在理想缺失、道德滑坡的今天,于丹用中国传统文化对渴求圣典的人们心田及时雨露和滋润,给大众提供“心灵鸡汤”和人文之光,我们有什么理由去吹毛求疵、求全责备?!我不是于丹的粉丝,但我同意于丹的观点:“一个人永远不要去羡慕他人。”“宽容一点,给自己留下一片海阔天空。”“只有自己的心清楚了,才能去善待他人。”
通俗化,不等于庸俗化、简单化,通俗易懂是褒义。大俗就是大雅,以圣贤道理为原料、用小故事煨出来的汤,虽然看似很浅,但对老百姓而言,更入心入胃。送于丹的一句话给那10位博士:“道不远人,让我们在圣贤的光芒下学习成长。”
再说口才。口才好的人容易出名,这是名人之所以有名的一个条件。我认为,中国官场口才好的人不多,因为中国选官基本上是官选,不要经过面对公开场合的脱口演讲和激烈辩论。而口才好的人都跑到电视媒体、学校讲坛、曲艺舞台上去了,因为这是职业的基本条件,也与长期磨炼有关。我还发现,口才好的,女的比男的多。像杨澜、倪萍、于丹、鲁豫、许戈辉……数不胜数,而男的我想到的除白岩松、冯巩外,我还一时真想不到谁。余秋雨、马未都也讲得好,可那是他们渊博的知识起了作用。我记得我上大学时,有一位教鲁迅课的女老师,一次在大礼堂给全校教职员工作学习鲁迅辅导,滔滔不绝,精彩极了,在那动乱年代能做到轰动效应,真不容易。口才这东西,我觉得四分天生,三分知识,三分实践,还有就是临场发挥,靠激情去超越自我。如你是女性,就更要加分,这是女的性别优势,不承认是不行的。于丹是什么条件都占有了,她的成功是当之无愧的,为她祝福!
“于丹现象”是串信号,它显示中华传统文化在今日现代化建设中依然有着强大的魅力,中国古典名着饱含着的朴素的真理,能穿越时空将今人的心灵唤醒,推动现代人格的完善、社会的和谐。
2012年3月15日
读李存葆
江西省散文学会要开一个全国性的散文创作研讨会,准备请中国作协的领导、并在全国散文界有影响的作家来指导,李存葆是最合适的人选之一。我到北京去邀请他,在赣参加研讨会后,又陪他到井冈山走了一趟。在井冈山北山革命陵园,看到年轻的解放军战士向这位肩挂少将军衔的威严汉子行军礼,我由此想到,对他在中国文坛作出的突出贡献,也应该给他敬个礼。
李存葆的出名是他的那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1979年8月,他到广西前线参战部队深入生活。自卫还击战中涌现出的英雄人物,他们可歌可泣的事迹感染着他、震撼着他。1982年4月,他去北京参加军事题材文学创作座谈会,听了军委有关领导的讲话和大家的发言,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因为英雄人物在李存葆的脑子里存活已久,情节也成竹在胸,他便一气呵成创作了中篇力作《高山下的花环》,引起强烈轰动。广大读者和专家普遍认为,这篇作品的成功很重要的一点在于作品真实体现并大胆地揭示了部队生活中的矛盾冲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在军事题材文学创作上有着突破性的贡献,该作品获得了第二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记得当年我把登载《高山下的花环》的报纸珍藏,时不时地拿出来学习。
李存葆的作品是有他独到之处,他将关心的民族命运、人类未来的全部情思、痛苦与欢乐,以及哲学思考熔铸进创作之中,让人感受到的是作家的大气与深刻的忧患意识。李存葆的脉搏是与时代紧紧连在一起的,他无疑就是创新型的作家,他用一颗敏锐赤诚的心,创作了一篇篇意蕴深邃耳目一新的作品,这一切均源于作家对生活的独特感受,源于他高度的责任感和神圣的使命感。黄河断流,作家为之动情,心情再也平静不下来了,他站在新的起点上,以超越历史、时代和未来的视角去冷静阅读黄河,创作了《大河遗梦》,用一个哲人深深地叹息、急切地呼唤、深沉地思考着黄河文化的今世和未来。他的散文创作从题材上看,都是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思考,在他的系列文化散文中,除了解说历史事情和人物有着崭新的视角和精辟的见解外,意在以史为鉴作出历史的反思,对道德尊严和人类理想发出强烈的呐喊。其大气磅礴和激越昂扬,开拓了当代散文的新境界。
李存葆虽为着名作家却十分谦虚,没有大作家的派头。在车上,他谈笑风生,思路敏捷,出口成章,时而背诵名家名句,时而引经据典,讲文坛古今中外的故事。散文海外版的主编甘以雯说,你记下他围绕文学不经意讲的话,就是一篇很好的创作谈。而他却称自己因穷从小没读到什么书,只有初中文化。李存葆丰富的人生阅历孕育了他深沉睿智的气质,他坦荡和正直、豪爽与热情,所以,他的作品气势雄伟,跌宕起伏,洒脱豪放。
他是勤奋的,时常有佳作出现在全国核心文学刊物上,出现在年度散文排行榜首篇。人民性、时代性、民族性和艺术性是李存葆散文的基本特征,而且也包含了文学的根本精神。我同意专家的观点,李存葆总是从当代生活出发,然后对中国的某种有悠久历史的文化传统进行梳理,最后再表达自己的见解。和余秋雨的文化散文相比,李存葆更重视现实指向性,余秋雨则更重视对一种曾经辉煌的文化现象进行梳理。《飘逝的绝唱》《祖槐》《东方之神》和《苏东坡突围》《抱愧山西》《一个王朝的背景》的最大区别就在这里。李存葆散文的现实感之所以比余秋雨更加鲜明,原因仍在于他对时代精神的执着追求。一个人只有站在时代的最高峰,其声才能震撼云霄,其作品才能千古流芳!
从上世纪80年代的小说《高山下的花环》《山中,那十九座坟茔》到90年代初的报告文学《大王魂》《沂蒙九章》,再到如今的散文《国虫》《呼伦贝尔记忆》,李存葆的作品体裁广泛,题材丰富,总是一文既出,必有轰动效应。他的散文都是一些大散文,是登高望远、纵横古今、忧国忧民之作,多写大主题、大题材、大感情,是散文中的洪钟大吕之音。有人比喻,如果说,贾平凹的散文就是谈心,是聊天;而李存葆的散文就是演讲,是朗诵;余秋雨的散文,介于两者之间,是温文尔雅的讲课。我认为,他们是中国散文界各具特色的“三剑客”。
在谈到创作时,李存葆认为,“真”是文学必备的品格,真情实感是一切艺术赖以生存的根基。散文应该更贴近中国人的生活,也应该更关注人类面临的生存危机与种种困境。散文里应该有情感的浓度、哲学的深度。近年来,各种类型的散文增添了散文的丰富性,但也出现了一些小情小调的软性文字。李存葆认为,这些散文不应该是“主流散文”,他提倡的是充满文化含量的“大散文”。李存葆说:“好的文章应该让历史检验。也许我罄毕生心力也难留下一篇为后人称道的文章,但我仍会像苦行僧那样去跋涉、去探求,因为探求的过程是美丽的。”
探求者永远年轻。祝愿李存葆!
2012年8月15日
读施叔青
应江西大学邀请,美籍台湾女作家施叔青女士于1986年6月来江西作《台湾文学概述》的学术报告。邀请台湾女作家来赣讲学,这在改革开放以来我省还是第一次。
施叔青女士来江西当时只有41岁,台湾鹿港人。17岁成名,着有《约伯的末裔》《一夜游》《牛铃声响》十多个长篇、短篇小说集。她兴趣广泛,曾入美国求学获戏剧硕士。她是一位对祖国大陆文坛十分熟悉、在文学上有独到见地的作家,这是当时在江西大学举行的座谈会上,我对施叔青女士产生的第一印象;她又是一位步履匆匆而笔耕不辍的作家,这是我在采访她的过程中逐渐加深的印象。
我们在拥挤的电车里、热闹的街头上交谈着。她步子迈得很大,对眼前的一切很有兴趣,显然,她急切地想多体验和感受一些新的生活。她多次来大陆观光讲学,她的足迹遍及沿海边疆、城市乡村。她用一种欣慰的心情,去感叹所看到的变化。她觉得大陆生活色彩变得斑斓,文坛变得兴盛,在这里有挖掘不尽的创作素材。她写了《驱魔》等小说,先后发表在《收获》《上海文学》等刊物上,从而也赢得了大陆广大文学爱好者的青睐。她一次次来去匆匆,在大陆结识了许多文坛上的朋友,看了许多作家的作品。在读谌容的《人到中年》时,她激动得热泪盈眶,不得不放下书来,让心绪平静一下,一种与民族共忧喜的感觉油然而生。她为中国文坛有这么多的好作品、好作家感到高兴,也看到了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