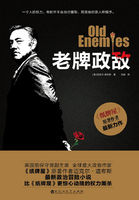在他身上很难找到通常文人的那种狂傲之气,他更多的是倾听来自外界的批评,有时甚至在外界给予很高评价时,他的自我评价却不高,甚至表现出一种自卑的心态。在《贾平凹小说选集》序言中,他说:“我是愈来愈觉得我的先天的不足和后天的不足”,“创作12年里,我是极贱看我的作品的。我是山里人,到西安这个古都里,仍是山里人德性,不大注意修容,故我的作品,一任的‘扑腾’品,也就全不看重……”在“商州”系列小说已经获得较大反响的情况下,他自己却说“我的哲学意识太差,生活底气不足,技巧更是生涩”;在《废都》后记里,他写到了自己搔秃了头发、淘虚了身子却仍没写出美文来的苦恼,面对他人恭维时“脸烧如炭”的尴尬,并且将成名与成功区别开来。但是,在另一些地方,贾平凹表现得又极为自尊,他曾多次谈到不被人理解的烦恼,责备外界没有注意他的苦心经营之处,并抱怨自己的某一种倡议没有得到回应。他自己可以写下标题《我是农民》的书,但对他人谈论他的乡下人身份和农民意识却颇为敏感。在《(土门)后记》中,贾平凹写道:“……我进城二十多年了还常常被一些城里人讥笑。他们不承认我是城里人,就像他们总认为毛泽东是农民一样,似乎城市是他们的,是他们祖先的,但查一查他们的历史,他们只是父亲辈,最多是爷爷辈才从乡下到城的。”大有彼此彼此、半斤八两的含义。可以说,一种建立在自卑基础上的自尊和一种要达成自尊而不得引起的自卑,是这样完整地交缠在这一作家身上,因而有时成就了这一作家的创作,有时则烧灼着这一作家的灵魂,毁灭着这一作家的创作。自尊与自卑,是出现于这一作家身上的又一大矛盾。
自卑在没有发展成为自卑情结时,并不是一个完全消极的、否定的词。A·阿德勒曾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自卑感,因为我们都发现我们自己所处的地位是我们希望加以改进的。如果我们一直保持着我们的勇气,我们便能以直接、实际而完美的惟一方法——改进环境——来使我们脱离掉这种感觉。”阿德勒甚至说:“自卑感本身并不是变态的。它们是人类地位之所以增进的原因。例如,科学的兴起就是因为人类感到他们的无知,和他们对预测未来的需要:它是人类在改进他们的整个情境,在对宇宙做更进一步的探知,在试图更妥善地控制自然时,努力奋斗的成果。事实上,依我看来,我们人类的全部文化都是以自卑感为基础的。”
贾平凹身上的自卑感,既表现为少年时期由出身、体质等原因在同龄人面前的弱势地位引出的无助感,也表现为创作初期蹒跚学步、屡投屡不中的挫败感,还表现为成名以后在人类文化的巨匠巨作面前的渺小感。贾平凹曾说:“我出生在一个22口人的大家庭里,自幼便没得到什么宠爱,长大体质差,在家干活不行,遭大人唾骂;在校上体育,争不到篮球。所以,便孤独了,喜欢躲开人,到一个幽静的地方坐地。愈是躲人,愈不被人重视;愈不被人重视,愈是躲人;恶性循环,如此而已。”这其实就是一种自卑感的表现。这种少年经历应当说给贾平凹心上烙下了深刻的印痕:“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初中后,便又开始了更孤独、更枯燥的生活……班里的干部子弟且皆高傲,在衣着上、吃食上以及大大小小的文体之类的事情上,用一种鄙夷的目光视我。农家的孩子愿意和我同行,但爬高上低魔王一样疯狂使我反感,且他们因我孱弱,打篮球从不给我传球,拔河从不让我入伙……”这种反复的不无重复性质的述说说明了少年时期的被忽略与人类与生俱来的不平等给这一作家的心灵留下了近似于精神创伤式的记忆。但这种自卑感所带来的积极的一面,是促使贾平凹从少年时期起便养成了一种忍辱负重、以柔克刚、以退为进、纳于言敏于行的人生态度:“懦弱阻碍了我,懦弱又帮助了我。从小我恨那些能言善辩的人,我不和他们来往。遇到一起,他愈是夸夸其谈,我愈是沉默不语;他愈是表现,我愈是隐蔽;以此抗争,但神差鬼使般,我却总是最后胜利了。”如果说,沉默与隐蔽所代表的是一种自卑与自尊相交织的复杂情感,那么,这“最后的胜利”所培养起的则是贾平凹不无固执的自强自信。正是凭借少年时期艰难的乡村生活培养起来的坚忍不拔、吃苦耐劳的品性和这种源于自卑的自强自信,使他能在创作的早期面对一百余封退稿信仍能坚持创作下去,使他面对因《鬼城》引起的批评而没有从此一蹶不振。在1983年,贾平凹曾将自己的创作之路比喻为拽着碌碡上台阶:“我的出路只有上台阶,只有沿着台阶往上走,夸父不到大海就渴死了,他死得悲壮。我或许在半路上也要倒下,但是即使倒下,我仍是一个上台阶的鬼。”后来在回顾自己的创作时,又说:“有人讲我的散文要比小说好,我生气了,就不写散文专门攻写小说。我有一种怪脾气:你说我啥不行,我就要弄啥,你说我弄啥行我就不弄了。”无论是拽着碌碡上台阶的创作态度,还是“你说我啥不行,我就要弄啥”的怪脾气,都不难从中看到由作者少年时期培养起的忍辱负重、自尊自强心理的影子,看到一种发现自己所处的地位而希望加以改进的对自卑的超越。
如果可以将自卑感视为人类地位之所以增进的原因,也就可以将文学创作视为贾平凹对自卑感的超越。但是,一旦经历了最初阶段的自卑感的超越,更高层次的自卑感又出现了,因为更大的人生意义和价值问题依然未能得到解决。体现在贾平凹身上,就是一旦成名,却没有成功的感觉,甚至于在《西厢记》《红楼梦》等人类遗产面前,产生了大的恐慌和困惑。他自述自己陷入了一种尴尬:“我看不起我以前的作品,也失却了对世上很多作品的敬畏,虽然清清楚楚这样的文章究竟还是人用笔写出来的,但为什么天下有了这样的文章而我却不能呢?”一种想要超越自我、创作出一部巨著来的巨大冲动出现在贾平凹身上。在《废都》后记中,作者谈到了创作《废都》之前自己家庭的变故和生活中的波折所带来的巨大苦闷,同时也谈到了《废都》的创作带给自己的巨大的安慰和太大的惩罚,并称《废都》是一部带给自己无法向人说清的苦难,同时在生命的苦难中又惟一能安妥自己破碎的灵魂的书。《废都》出版以后,引起了外界沸沸扬扬的评价,可以说,这既在作者意料之中,也在作者意料之外,然而所有有关《废都》的截然相反的评价都是与作者无关的,它是一部作者不得不写的书。现在看来,《废都》
既是一部世情小说,也是一部作者的精神自传体小说。说它是一部世情小说,是指它相当真实地记录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的生活世象,通过对西京四大名人的叙写反映了转型期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形态;说它是作者的精神自传体小说,是指作品主人公庄之蝶的精神状态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创作主体一段时期的心路历程,作品所包含的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里包含了作者的自叙传(尽管这种批判是以文化沉沦的方式表现出来)。我们不仅可以从作品中的那条牛身上看到贾平凹一以贯之的对城市文明的抵触和隔膜,而且可以找到庄之蝶的言行心态与作者本人言行心态间的互证。庄之蝶所说的“毛主席都不说普通话,我也是不说的”,贾平凹在《说话》里有过类似的表达;庄之蝶签在崇拜者毛衫上“把杆杖插在土里,希望长出红花”的诗,便是作者收在诗集《空白》中的诗。
而只要看一下庄之蝶对唐宛儿所说的一段话,就可以明白庄之蝶的心态与作者本人一段时间的心态有多么的相似:
“宛儿……十多年前,我初到这个城里,一看到那座金碧辉煌的钟楼,我就发了誓要在这里活出个名堂来。苦苦巴巴奋斗得出人头地了,谁知道现在却活得这么不轻松!我常常想,这么大个西京城,于我又有什么关系呢?这里的什么真正是属于我的?只有庄之蝶这三个字吧。可名字是我的,用的最多的却是别人!出门在外,是有人在崇拜我,在恭维我,我真不明白我到底做了些什么让人这样?是不是人们弄错了?
难道就是因为我写的那些文章吗?那算是些什么玩意儿?
我清楚我是成了名并没有成功的,我要写我满意的文章,但我一时又写不出来,所以我感到羞愧,羞愧了别人还以为我在谦虚。我谦虚什么呀?这种痛苦在折磨我,可这种痛苦又能对谁说,说了又有谁能理解呢?”
这完全可以看成贾平凹内心的独白,只不过是借一个拟想的听众倾吐了出来。贾平凹在《(废都)就是(废都)》中说:“我不明白我怎么就混入了名人之列,我一再说成名不等于成功,名使我得到了许多的好处,名又常常把我抛入尴尬之地。”这种表述应当说是真诚的。在贾平凹那里,他所说的“尴尬”不仅仅指一般的名人之累,它还表现为作者的自我评价与他人的评价不一致所带来的烦恼,以及成名后活得并不轻松快活而生的苦闷。《废都》出版以后,有人将它与《浮躁》进行比较,肯定《浮躁》而贬低《废都》。但事实上,这两个作品间有相当紧密的联系。
某种程度上说,金狗就是一个刚刚从乡村走向城市的庄之蝶。金狗第一次踏上州城的土地,就因打抱不平同穿西装的城市青年干了一仗,面对城里人“土包子”一类的斥骂,金狗刚拥有的记者身份让他不无自豪地说出了“乡下人不只是光会吆车拉沙子吧”的话,这个人物身上,其实就寄托了贾平凹本人那种初到城里就要活出个名堂来的心迹。然而后来的金狗虽然在制止召开河运队现场会、营救雷大空两件事上成了功,但对这种成功却并不像小水、福运和韩文举那样高兴,而总觉得其中包含着巨大的“耻辱”,原因是利用了田家和巩家的矛盾,违心地以记者身份去恫吓、威胁公安局长,这有违一个农民的儿子、一个正派人的本分。这种成功后并不快活的心迹,与成名后的庄之蝶也是相合的。
甚至于庄之蝶与几个女人之间的关系,也可以在金狗与小水、英英、石华间的关系中找到雏形,几个女性以飞蛾扑火的热情倾心于同一男性,成为两个作品共同的重要的写作线索。只不过《浮躁》对男女情爱关系的描绘更为“纯洁”、“干净”罢了。《废都》中种种社会的怪现状、特别是遍地是“假”的生活世象在《浮躁》中已通过雷大空的皮包公司、田家与巩家的矛盾得到了反映,只不过在80年代,无论是作家还是评论家,都习惯于将它们看成改革时期难以避免的现象罢了,而金狗周旋于权力矛盾之间的做法,也在80年代的整体文化氛围中被赋予了反抗权力腐败的光环;而在90年代的整体文化氛围中,当权力腐败成为一种令人痛心疾首的“正常化”的社会现象时,拥有名人头衔的庄之蝶的权力周旋,则成了人文精神失落和知识分子堕落的一个象征。
不过,总体上说,《浮躁》和《废都》有种种相通之处,但撇开其中过于笨拙陈腐的性描写不谈,我以为在反映生活的广阔度、心理描写的深度、语言文字的纯熟度等方面,《废都》显然超过了《浮躁》。《废都》的主人公诚然是以伪恶者的形象出现的,作者创作这一作品时确实也失去了以往作品中的那种乐观的理想主义的色彩,主要人物关系的设置也不无模仿《金瓶梅》一类作品的痕迹,但它对20世纪90年代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生态和心态的描绘和把握,却达到了同一时期作家作品没有能够达到的深度和广度。《废都》写的是一个时代和一个时代文化名人的失败,“鬼魅狰狞,上帝无言”所传达出的,是作者面对自己的内心之鬼和外界的种种鬼相而生的巨大的愤怒,以及人文知识分子被边缘化后的无足轻重感和荒凉感。钟唯贤这样的知识分子只有在火葬场里凭借高级职称证书才得到优待,“作协的”在世人那里只是“作鞋的”,这使作者的内心产生了巨大的悲哀。但《废都》的意义远不止于对某个人和某一阶层人的生态和心态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