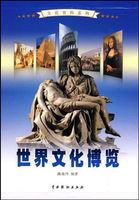明清以来,上海深受经济富庶、人文荟萃的江南文化的滋养,开埠前一路追随当时的文化中心城市苏州、扬州,并遵循自己的文化轨迹,逐步走向商业化的城市发展道路。开埠之后,特别是租界的设立,使上海呈现出五方杂处、万商云集、百货交汇的繁荣景象,城市氛围愈益浮华奢靡。市民阶层的兴起,消费空间的重构,与休闲观念的流行,促成了“洋场”文化与都市生活景观的建构。各种来自不同时空的文化样式,如西方现代商业文化、中国传统士大夫文化、市民娱乐文化等等,皆在都市休闲娱乐这一特定时空和都市景观中获得彼此的交融与杂糅。戏园更成为豪富巨绅、达官贵人穷奢极欲挥金如土的娱乐天地。因缘际会,加之京班南下,地方戏进城,遂使上海成为近代中国戏曲活动的中心,与京城南北对峙,遥相呼应。从私家厅堂花园抑或就地开演的简易戏棚,到营业性茶园,再到规模宏大的西式剧场,回溯上海戏曲娱乐空间的这一扩张、竞争和兴替的过程,我们可以发现:从现代性反思的角度来看,在新旧演出场所更替的表象之下,这也是一种借助空间形式而将戏曲活动中的观演双方不断纳入一个与演出统一协调的整体的过程,亦即强调统一、协调、集中原则的逐渐化约和规整的理性化过程。实现这一过程的原因和动力是多方面的,而本章所要侧重分析的,则是运作其间的商业与市场的驱动机制。西方经济、文化、科技(特别是技术)文明的浸染与影响,往往借助商业资本运作的必然导向,而首先体现于社会物质层面的空间建构(如剧场结构和设施);即便是同在文化建构中,往往也都是取媚于商业资本的魔力,即和市场因素密不可分的消费文化、娱乐文化、流行文化等领域首开风气,而以戏曲为典型的都市大众文化的建构正是在与上述文化诸向度之间的错综联系中迂回行进。
从简易戏场、戏棚,到茶楼、茶园,再到新式剧场,随着戏曲娱乐空间的结构及功能的演变,戏曲演出的整体氛围也从随意、混乱而日益协调和规整起来。与此同时,娱乐活动也从日常生活中提取出来,由自娱自乐自足的日常随意性的消遣,一变而为享乐性的消费活动。在此过程中,娱乐变成公众的、群体的行为,经由同一化、规模化而成为都市消费市场和市民文化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原本作为娱乐要素之一的戏曲演出,也从整体娱乐活动中解析出来,并得以整体性的凸显。于是,茶园就从九流三教杂陈共处的一方社交娱乐空间,慢慢演变为单纯进行娱乐消费的独立空间,艺术欣赏的独立空间,由此促成了都市空间的功能分化。而从自由自在消遣的“白相人”到一门心思看戏的“观众”,此一变化也表明了消费活动所塑造出的消费主体的确立,当然,同时也是艺术欣赏的主体的确立。从更深的层面来看,随着都市娱乐消费空间的化约和规整,及其对日常生活和公共空间所构成的挤压,戏曲作为一种起始于民间日常生活的草根文化,其内在的元气和活力恐怕也正在与都市中相对更为自然的生活状态及其空间一起萎谢。
崛起于20世纪初叶的海派戏曲的风格特点,要而言之,那就是开放性、时代性、商业性、通俗性、娱乐性和西方“现代戏剧艺术”意义上的艺术完整性。很显然,此间综合融会了上海这座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习俗、民众心理及社会舆论等方面的诸多因素。而海派戏曲活动所集中体现的大众文化冲击力,无论从都市文化建构的何种向度来看(诸如市民文化、通俗文化、流行文化、娱乐文化、商业文化等等),都可能对长期居于正统地位的种种文化向度(诸如传统文化、精英文化、雅文化等等)构成挑战,乃至具有颠覆性的意义。而世界局势的瞬息变幻,租界统治的错综复杂,文化市场竞争的紧张激烈,市民观众趣味的求新求异,戏曲艺术主体的内在制约,等等,都从各自不同的方向对海派戏曲的生存构成了极大的驱动力。事实表明,海派戏曲风格的为人或褒或贬之处,恰恰因其同根同源而彼此夹缠不清。其根源,简单说来,即是伴随资本主义经济机制而来的都市大众文化、商业文化、娱乐文化等等的兴起,特别是其间所蕴涵的民主思想、新的文化和艺术观念以及与之相应的新的表现形式的渐入人心:各种力量此消彼长,而又共同作用,其结果便造就出了令人莫衷一是的“海派”。有鉴于此,许多研究者往往为了确保政治正确,也为了论述方便起见,索性在海派戏曲的整体风格中划分“良性”与“恶性”。所谓“恶性海派”,指的是戏曲为迎合资本主义的商业运作而出现的种种庸俗作风,即后来在新中国戏改运动中屡遭贬斥和批判的“落后的小市民趣味”,如连台本戏的粗制滥造,机关布景的竞奇斗艳,插科打诨的噱头主义,等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以政府为主导力量而推行的新中国戏曲改革运动中,“海派”几乎沦为“恶性海派”的简称,因其直接与商业、与市场相联系而被视为充满腐朽堕落之“毒素”的资本主义渊薮。以政治宣传和文化整合为目的,新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表现出了对大众文化的商业性质和娱乐功能的贬斥,这直接导致了政府戏改部门对完善戏曲活动的市场机制的忽视,由此引发了对海派戏曲的商业色彩和市民趣味的舆论批判和行政压制。这种批判和压制的结果,一方面当然是在很大程度上清理和更新了上海戏曲舞台的面貌,使之更加符合“人民”和“人民的城市”的主体形象;而另一方面,也大大降低了戏曲作为大众娱乐文化的活力和吸引力,而越来越沦为履行政治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功能的工具。直到市场机制重新在中国崛起的20世纪80至90年代,“海派”一说才渐渐恢复元气,并得以在戏曲界乃至整个文化领域抖擞其精神。
其间,就大众文化体制改革而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上海文艺院团改革历经“内部承包经营责任制改革”、“所有制和经营方式双轨制改革”、“院团全员聘任制改革”、“院团分类管理和领导管理体制改革”、文广影视合并、院团委托新闻传媒和社会单位管理等一系列阶段。这些改革,初步建立了文艺院团责、权、利相统一的责任制关系,使院团成为文艺创作生产的经营实体;初步建立了国家确保重点、政府宏观调控的管理体制,做到了政事分离、政企分开、管办分离;初步建立了文艺院团由新闻媒体和社会单位委托管理的新格局,强强联合发挥了市场资源、品牌宣传、人才整合、资金融通等方面优势。但是一切尚在过程中,距离文艺体制改革的目标,即建立符合精神文明建设要求、遵循文艺发展内在规律、发挥市场机制积极作用的充满活力的大众文化体制,其间还相差甚远。
综上所述,可见海派戏曲作为都市大众文化的特质及其与市民文化消费选择密切互动的关系,可见以海派戏曲为表征的近代上海戏曲市场的形成及其对市民文化生活和戏曲自身发展的影响,亦可见戏曲文化市场构成的社会、经济及物质、文化要素,皆与都市化过程紧密相连。转思建国以来的戏曲活动流变,则是在计划经济体制背景的社会、政治、文化诸因素影响下,戏曲文化由变异到回归其大众文化本质、回归市场机制的过程。总之,通过对上述历史语境的观照和梳理,笔者试图呈现,海派戏曲的发展与市民的日常生活和文化娱乐生活的互动关系,以及海派戏曲对近代以来的上海都市大众文化建构的作用和意义。
一、大众文化的“共同体”:海派戏曲的都市化语境
上海的租界作为一种相当特殊的“殖民地”形式,是如何嵌入本地原有的政治、经济、文化脉络中,继而采用何种策略规划、改造和重建了原有的社会脉络?同时,原有社会又是采用怎样的方式来回应、排拒和抵抗这种殖民改造?具体而言,租界对土地的直接诉求,凸现了殖民主义侵略性的特质——对空间的掠夺、占有和改造。因此,租界和原有社会之间的冲突和重组都较为集中地体现在空间面向的争夺上。资本主义的特征就体现在“空间的生产”上,它不断地创造空间的中心,同时也生产出依附于此中心的边缘。
如果将“空间的生产”回置于具体的大众文化建构的历史语境之中,我们不难发现,对近代上海而言,工业化、都市化、世俗化、民主化等进程,和上海由租界带来的特殊的殖民化(或曰“西化”)几乎处于同一个近代化(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之中,正可谓理一相殊,殊途同归。
(一)“租界”的特殊性与近代上海的都市化进程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根据《中英江宁条约》(即《南京条约》),上海于1843年11月17日正式对外开放为商埠。1845年11月上海道台与英国领事订立《上海土地章程》,英、美、法等国次第在城北建立租界。在让外国人享有土地专有权的同时,章程还赋予外商在界内进行全面建设的权利和英国领事署对界内绝大部分事务进行公共管理的权利。此三者结合在一起,决定了上海租界的“国中之国”的基本面貌,而同时又属“化外之地”,于是租界作为一种“异质”,逐渐嵌入了上海固有的社会结构脉络中。《上海土地章程》可以说是中英两国官员利益博弈和相互妥协的结果,英国殖民主义者借此取得了在租界范围内的租地、建房、居住、经商和一部分市政管理权,上海地方政府也部分地达到了对英国殖民主义者进行限制的目的,比如划定范围、华洋分居、租地限制、治安管理等。显然,此举原求华洋划界、各自为政,但战乱中大批华人逃入租界,五方杂处,万商云集,城市景象繁荣异常。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日本及其他各国根据片面“最惠国待遇”取得开厂特权,遂使原本以经商为主的外资高速扩张到工业领域,而上海作为中国外贸中心的同时又成为新兴的工业城市。1899年上海租界大规模扩张,屡屡越界筑路,至此大致奠定其范围。到了1914年7月,法租界的面积从两千一百四十九亩剧增到一万五千一百五十亩,加上公共租界前大扩张达到的三万三千五百零三亩,上海租界的总面积已达到四万八千六百五十二亩(不包括越界筑路的区域)。这个总面积如果与1846年英租界初建划定界线时的八百三十亩相比较,整整扩大了五十七倍。在上海口岸地位愈显重要,土地愈益紧张,地价不断飞涨的情况下,殖民空间的迅速扩张无疑赋予了租界一种发展的特权,它意味着租界拥有了更大范围的具有“生产性”的土地资源,更大规模的资本回旋的领域,吸引和容纳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繁荣自己的可能性。租界的特殊性,如安全感、自由度、西方文明,在客观上促成了广泛而杂糅的中西文化交流,从而造就了上海城市风格的繁复和变异,美其名曰海纳百川,日新月异,乃至一跃成为国际性的商业大都会。
租界之于上海的巨大影响,突出地体现为以经济、文化资本为手段的殖民扩张对城市空间的生产与重构。随着租界的发展,上海旧城之北出现了不同于老城厢格局的新型城区“北市”,通过整顿交通、拓展道路、管理环境、维护治安等途径把原有的空间加以改造,促使城市“光明化”、“技术化”和“公共化”,而这一切都是为了使之适应工业组织规则的管制体系,成为殖民地的“工业化”中心。上海的城市面貌极大改观,许多先进的城市设施迅速入驻上海,例如:1865年中国第一家煤气厂在此投产供气,1882年中国最早的电力厂也在此正式供电,1883年自来水厂开始向居民供水,同时代表西方物质文明的电讯设施也相继出现,逐渐完善了作为近代城市的基本设施。在经济方面,上海打破广州的外贸垄断地位,以连接广阔内地和国外市场的中介点地位发展起数量巨大的对内和对外贸易。在工业和交通方面,随着洋务活动的开展,1865年近代中国规模最大的军械和造船企业“江南制造总局”诞生,1872年中国最早的近代航运企业“轮船招商局”也在此成立试办,1890年上海机器织布局正式投产,成为中国最早的机器棉纺织企业。这些规模巨大的新式机器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取代了原先那种旧式作坊的简单协作生产关系和旧式经营方式,标志着中国近代城市工业化的开端。经济的近代化也带动了城市科技和教育的近代化,同时上海的近代政治民主思想也得以广泛传播。而租界的发展,特别是租界作为西式城区的市政管理制度和较高的管理水平,大大刺激和推动了华界士绅的地方自治,当然也强烈地刺激着本地政府官员的民族自尊心,不能不急起直追,借鉴西法改良市政,从而在整体上提高了近代上海的都市化水平。毋庸置疑,近代上海的都市化进程,起步之早,程度之高,堪称中国第一。
上海近代文化,便在此富于殖民色彩的都市化背景中形成并日渐成熟,进而以新型报刊、书籍为传播手段推向全国,其势取代北京而成为全国文化中心。而这个中心本身又是相当丰富而复杂的,既是雅文化中心,也是通俗文化、市民文化中心,同时也是新旧文化并存的中心,和中西方文化交汇的中心,由此呈现出一种多方面、多层次、彼此交错而又整体互动的立体建构。简言之,上海的地理位置、历史文化、西方文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机制、新型的市民意识等等,错综交织在一起,使之在文化的走向上突显出这样几股推动力:从历史的纵向看,是近代社会取代传统社会,是城市、工业文化取代乡村、农业文化;从世界的横向看,是中西方不同文化、文明的冲突和交融;从中国社会的内部结构来看,则是传统士大夫文化与市民文化的冲突和交融,是雅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双向对流。处在这样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中,特别是在富有殖民色彩的资本主义文化机制的影响和制约之下,种种力量的交汇使得上海成为“化外之地”,而又“五方杂处”,充满异域感和杂糅性,这不免就赋予城市中人无拘无限的想象力和层出不穷的可能性。换言之,租界存在的特殊性,看似来自外在的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强力作用,而实已内化为这座城市特有的变化基因,由此便成就了近代上海都市化发展的巨大可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