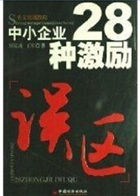消费市场的大转折已经并继续在改变着人们的消费内容和消费形式。由于跟上转折是需要成本的,因此不同阶层的人们在这场转折中往往就会有不同的表现。这些表现上的差异以及相互之间所发生的影响,就是本章所要研究的重点。
(第一节)各阶层之间的差异
由于社会地位、收入能力及文化、品味的不同,各阶层在这场大转折中所持有的态度和选择也就可能不同。下面就分别从以下五个方面对其差异进行比较。
一、需求层次上的差异
各阶层对于大转折的态度和反应取决于各自所处的需求层次。
从马斯洛和劳动力再生产的需求层次出发,各阶层之间的差异何在呢?
1.从消费结构上看差异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3年城镇居民家庭的消费数据,各收入户组之间在前述消费大头上的开支比重都是不同的,从中可以看出各收入组在主导性需求上的差异。为便于比较,先交代一下相关项目的全国平均数据:恩格尔系数(即食品支出的比重)为37.12%,其他的主要消费项目按比值的大小排序依次为:教育文化娱乐(其中教育占了55%)、交通通信(其中通信占了56.8%)、居住(其中住房占了36.7%)、衣着(其中服装占了71.4%)和医疗保健。接下来就来看看各收入户组的数据:
(1)先来看收入最低的三组。10%的最低收入户组的恩格尔系数为47.72%,消费大头按开支大小排序依次为:食品、教育文化娱乐、居住、衣着、医疗保健和交通通信;10%的低收入户组的恩格尔系数为44.93%,消费大头依次为食品、教育文化娱乐、居住、衣着、交通通信和医疗保健;20%的中等偏下户组恩格尔系数为42.26%,消费大头则依次为食品、教育文化娱乐、居住、衣着、交通通信和医疗保健。这三组的前四项排名完全一致,除了在教育这一项上与全国平均名次一样,都排在第2位以外,居住却比全国平均排名提前了1位,而交通通信却降低了2—3位。这说明这三个低收入组目前的主要需求尚属于争取基本的生存和发展条件的性质。虽然居住的开支已列在第3位,但从其住房上的人均开支分别仅为56.79元、77.48元和98.85元来看,其对于较差的住房条件并不能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善。这一方面说明基本的生存条件尚有待改善,另一方面也说明这些阶层是以压抑基本居住条件来力保教育方面的开支的。至于在其他阶层已成为消费大头的交通通信(即满足归属和发展要求的手段)上,就更只能沾点边而已了。
(2)再来看20%的中等收入户组和20%的中等偏上户组。其恩格尔系数分别为39.23%和36.61%。前一组的消费大头依次为食品、教育文化娱乐、衣着、交通通信、居住和医疗保健,而后一组的排序仅仅在衣着和交通通信之间换了一下位置,其余的皆与前一组相同。这两组的需求有更明显的追求归属和发展的性质。放在第2位的教育的意义已无需多说,至于居住的排序比全国后推了1位,成了第5位,而衣着的排序却提前了1—2位,则表明这两个阶层在基本的居住条件已经解决的前提下已将注意力转移到穿得更好上面,具有“更好地满足工作和交际需要”的性质。值得注意的是后一收入户组在衣着和交通通信上的换位,说明随着收入的再提高一步,对衣着的重视就可能会让位于交通通信。
(3)最后来看10%的高收入户组和10%的最高收入户组。其恩格尔系数分别为34.67%和29.85%。前一组的消费大头依次为食品、教育文化娱乐、交通通信、居住、衣着和医疗保健,后一组中仅是将末位的医疗保健换成家庭设备,其余的都与前一组相同。这两组尤其是后一组的消费结构除了显示出强有力的发展倾向以外,还表现出加大了对于享受的力度。以最高收入户组为例,其消费值为全国平均数3倍以上项目的依次为住房、交通通信和家用设备中的耐用消费品。值得注意的是住房上的开支,其水平几乎为全国平均数的4倍,在本身消费排序中的位置是第4名,比中等、中等偏上组的排列又提前了1位。这种情况所反映的可能是其中一部分人已购买了第二、第三套房子,或者是级别更高的房子。购房的动机既可以是投资,也可以是享受的,这与前述低收入组排在第3位的居住开支显然不是在一个层次上的,而是有着天壤之别的。此外,该组将其他所有组都放在第7位的耐用消费品却排上了第6位,且开支为全国平均数的3倍以上,原因何在呢?从“按收入等级分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2003年耐用消费品拥有量”中可见,最高收入组最突出的项目为家用汽车,是全国平均数的4.8倍,甚至也是高收入户组的3.3倍。这一差异说明,家用汽车在现阶段主要还是为最高收入阶层所拥有,而且不仅仅是他们用以提高效率或享受的工具,同时也是他们用以拉开与其他阶层的差距,并以此来凸显身份的手段。
2.从烦恼的内容上看差异
邓伟志等人曾在前述“上海社会结构与阶层分析”(下简称邓文)一文中就当时(2000)上海各阶层的烦恼问题作了研究,其中的有关数据也可以帮助我们来分清各阶层在需求层次上的差异。主要的烦恼正是人们亟待要解决的问题,因而正好从反面印证了人们的主要需求。根据邓文的调查结果,各阶层回答的主要烦恼分别是:下下层主要集中在“收入低”(占36.4%)、“住房拥挤”(37.2%)和“文化程度不高”(36.4%)上;中下层则集中在“环境脏乱”(24.0%)和“有烦恼但无处倾诉”(23.6%)上;中层主要是“单位人际关系紧张”(27.0%)和“社会治安不好”(17.2%)上;中上层的主要烦恼是“单位人际关系紧张”(40.5%)和“文化程度不高”(32.9%);上上层则没有什么明显的烦恼。
从下下层的回答来看,属于典型的正为生存而战的烦恼。尽管多数阶层都会抱怨收入低,但那主要是反映了人心永远不会满足的那种情况。然而对于下下层人们来说,“收入低”则意味着难以达到社会公认的起码生活水平。至于“住房拥挤”的含义就更明确了,毕竟对于不少人来说,几代人同挤一室的那种窘迫状况还是可以记忆犹新的。“文化程度不高”反映了人们对于目前地位的痛定思痛。为什么只能从事这类社会地位低和收入微薄的职业?归根到底在于自己的文化水平太低!下下层的这些回答太具感性化效应了,一方面令人感觉沉闷,另一方面则活脱脱地勾画出该阶层人们亟待解决生存条件的需要。
从中下层的回答来看,人们的主导性需求主要体现在安全和归属的层次上。“环境脏乱”,直接反映的是对于现在居住地段的不满,间接地所透露的却是对于共处一地的人们素质的不满。因为居住地的质量往往与该地居民的地位和教养有关。由于居住地的环境质量往往与住宅的质量和价格是正相关的,因此有钱人的住宅往往会集中在既安全又干净的地段,而收入较低、买不起好房者则往往只能生活在比较脏乱的地段上。一旦生存不成问题而收入富余后,环境脏乱所导致的烦恼就会成为一些人们的主要问题,而改换环境,并归入到自己所羡慕的那种地段和群体中去就成为了他们的主导性需求。
至于“有烦恼但无处倾诉”也是一种典型的对于归属和友爱的诉求。
它可能提示了两个层次的倾诉要求:一个是在日常生活工作中所遭遇的困难和不公没人来管,所表达的主要是针对上级领导部门的不满;另一个是关于个人感兴趣的话题找不到合适的人来交流,所反映出来的遗憾主要是针对所属团体中的其他成员的。无论是这两者中的哪一种缺憾,归根结底总是与自己的人微言轻有关的。因此,改换所处的团体、进入到地位更高、交流更对“胃口”的团体中去,就会成为这些人们的首要需求或选择。
从中层的回答来看,则既具有对于安全和归属的要求,又具有希望受到尊重的愿望。对“社会治安不好”的埋怨与前述对“环境脏乱”的烦恼一样,反映了对于生活所在地区的不满和希望换个更好的环境的需要,因此同时具有安全和归属的性质。而对于“单位人际关系紧张”的抱怨却可能反映了两种内在需要:一种可能仅仅是希望能换一个人际关系较为和谐的单位,故而属于对于更好归属的追求;另一种则可能是针对人际关系阻碍了自己晋升或成功的机会而发的,因而是从反面印证了渴望得到他人认可和尊重的需求。
从中上层的回答来看,也是既有寻求更好归属的愿望,又有着更为强烈的对于晋升的渴望和担忧。其中注重“单位人际关系紧张”的涵义已如上所述,不再重复,而对于“文化程度不高”的烦恼却因与下下层的烦恼相重而值得认真分析。虽然从表面上看这两个阶层的选择相同,但鉴于两者的地位相差较大,因而实际上对于文化程度的要求是根本不同的。在下下层身上,“文化程度不高”指的是没有文化或只有很低的文化程度,因而难以进入到那些较为稳定和可靠的工作岗位中去,所反映的是对于摆脱生存困境的强烈需求。但在中上层身上,“文化程度不高”往往是对于名牌大学本科毕业生及硕士、博士的不断涌入而产生的担忧。由于同事们的平均学历在迅速提高,原本具有的大专或本科学历就相形见绌了。此时别说是普通员工,即便是总经理或处局级的干部也会产生某种不安,并由此而引发了读书充电拿学位的高潮。这种对于“文化程度不高”的烦恼实质上是出于“升迁可能受阻”或“怕被人看轻”的考虑,因而实质上属于对于尊重和地位的追求,与下下层的担忧显然不是在一个层次上的。
从上上层的回答来看颇为耐人寻味。人非圣贤,岂能没有烦恼,更何况是以一个阶层整体而言的。之所以是“没有什么明显的烦恼”,既可能是因为在调查问卷中没有找到合适的选项,也可能是因为原有的主导性需求刚刚得到满足,尚处于暂时的心满意足阶段,因而自己确实也不清楚究竟有什么烦恼。
以上数据的意义与前面对于消费结构的分析有一定的吻合,只是有关烦恼的调查是以2000年的上海情况为对象的,而且当时各阶层的恩格尔系数也比2003年的全国城镇相应阶层的水平要高,因此邓文中各阶层的需求层次似乎都比2003年的数据所反映的要低一些。不过这也有一个好处,那就是通过两者的比较,可以更清楚地看出需求差异的变化趋势来。
二、转型能力上的差异
面对主导性消费的转变,各阶层之间由于条件或能力的不同,所产生的感受和反应也就不同。下面就以在城乡居民的消费支出中分别占了第2位和第3位的教育消费以及分别占了第4位和第2位的住房消费为例,来比较一下各阶层的表现。
1.教育消费上的能力比较
先来看城镇中的情况。2005年2月25日的《国际先驱导报》刊登了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徐安琪关于子女扶养成本的调查研究数据(见表31)。据称,调查取样是从上海市徐汇区的36个居委会中各个阶层的家庭中得来的,59.3%的被调查者年收入在12000元—60000元。
根据表31,可分别计算出一个学生从小学至初中(即九年制义务教育期间)和从小学至大学(共16年)的年均支出,前者为13533元,后者为17856元。由于上海的人均收入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因此这些数据对于全国来说可能并不直接适用。但根据笔者对于上海情况的了解,表中有关小学至大学的数据并无明显的过分之处,在上海应有一定的代表性。那么对于这种教育成本,上海城市各阶层的承受能力会如何呢?表32列出了2003年上海市区居民家庭生活的相关数据。
该年上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4867元,以每个家庭平均3口人计算,只有达到了这种人均收入水平的家庭才可以勉强地做到以1/3的家庭收入来支付上述教育成本,低于这一平均线的家庭就会感到困难了。从表32中可见各收入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
最低收入户组为5598元,低收入户组为7785元,中等偏下户组为9816元,中等收入户组为12602元,由于这四组各占调查总户数的10%、10%、20%和20%,因此可以说60%的家庭是难以承担前述教育成本的,因为这四组家庭的食物支出占全部消费性支出的比重均超过4成,而且尚未怎么改善的住房的支出却已成了第3位的开支。
因此这些家庭虽然已将教育消费排在了第2位,但却难以跟得上社会的平均水平,因而在不同程度上会呈现出落伍、被动和疲惫之态。
再来看农村的情况。在全国农户的生活费支出中,教育方面的开支占据第3位。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3年的全国农村人均生活费支出是1943.3元,其中食品开支占了45.59%,居住开支占了15.87%。然后就是文教娱乐了,其开支占了12.13%,现金为235.68元。2005年3月3日的《21世纪经济报道》刊登了对于全国政协常委、苏州市分管教育的副市长、教育在线的创办人朱永新的采访记录。其中提到目前农村小学生每年每人需要500元,初中生则需要700元。根据这一数据,我们可以大致计算出农村学生从小学至初中平均每年每人所需的教育费用是666元,若以农民个人承担了其中的50%来计算,那么每个农民家庭在九年制义务教育期间必须平均每年为每个在校的孩子支付333元的教育费用。农户中能够承担这一开支的又有多少呢?在2003年按收入分组的农户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中,文教娱乐方面的开支水平分别是:低收入户组109.94元,中低收入户组161.37元,中等收入户组218.34元,中高收入户组276.81元,高收入户组465.45元。可见从整体上看,只有高收入组才能较为轻松地负担孩子九年制义务教育所需要的333元,即使考虑到2003年与今天的不同而降低这一标准,那也顶多是再加入一个中高收入户组,而其余各组依然难以整体达标。其间若发生了相当比例的辍学现象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2.购房能力上的比较
再以城镇居民的购房为例。这是自2001年起缓慢升温的消费大头,在2003年的城镇居民消费支出中仅占据了第4位,但在2004年却出现了价格飙升的局面。在这突如其来的狂潮中,各阶层的表现又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