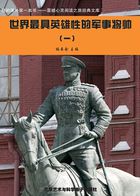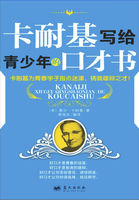《李宗仁归来》一书起因
1965年7月,李宗仁先生偕夫人郭德洁女士毅然从海外归来,是当时一件震动海内外的大事。在这之前,追随李宗仁先生几十年的程思远先生,曾数次秘密回国,穿梭于周恩来与李宗仁之间。此时,终于促成了这件大事。
程思远先生和夫人石泓女士也一起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记得当时不论是上层爱国民主人士,还是政协统战系统的干部职工,无不为李宗仁归来这一中央统战工作成功的大举措而欢欣鼓舞,以至都在议论李宗仁先生在下一次全国人大、政协大会时可能增补为全国政协副主席或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等。然而,谁也未曾料到,一年后即爆发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直至李宗仁先生在1969年4月“文革”顶峰时期郁郁病逝,也始终未能安排上一个职务。
笔者目睹李宗仁先生夫妇和程思远先生夫妇的丰采,是在他们从海外归来之初,却未有直接交谈的机会。但是,对于李宗仁先生等从海外归来前的神秘策划和历史情况,笔者却所闻甚多,其来源:一是政协统战口的口头传达和书面材料;一是我们熟悉的原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也是李、程的昔日同事和朋友)在会场内外的议论和陈述。这一切,正是我在十多年后撰写长篇报告文学《李宗仁归来》最早的素材积累和创作起因。
1972年秋天,我从湖北沙洋“五七”干校返京并回到政协直属学习组小组秘书的工作岗位,程思远先生已经是这个学习组一名几乎从不缺席的学习成员,尔后又成了学习组的召集人之一。那时候,学习是与思想改造和政治运动相结合的,每周要学习两三个半天。自然,我同程思远先生,很快就熟悉起来。在长年累月的学习会上,程思远自然要谈起往事,解放前的,在海外的,包括李宗仁先生归来的起因和过程,这就更加引起我的浓厚兴趣,以至在会外也找他询问,他也乐于满足我的要求,甚至把他精心保存的海外华文报刊的剪报材料带给我看。这是我酝酿撰写《李宗仁归来》的第二阶段。
时至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由于政治大环境的逐渐宽松,我的准备工作也进了一步,即登门找程思远先生长谈,对李宗仁先生归来的前前后后,有了系统的素材。正是这时,我的一位作家朋友王士美从长春来京,我同他谈起想做成这件事,写篇长文。他兴趣极大,认为应该写成一本书,表示愿意合作,鼓励我加紧收集资料。他的支持和鼓励,使我增强了信心,工作也进一步加紧,曾一度每周都要去一趟程先生的家,请他如讲故事一般地叙述。
一瓢凉水浇不灭:作品在东北出版
就在这时,一位负责同志找我谈话,他单刀直入地问我:“听说你准备写一本关于李宗仁归来的书,有这事吗?”我听了一愣,竟一时答不上话。沉思了一会,自然是如实汇报。这位负责同志耐心地听完我的叙述,即严肃地说:
“一个机关干部,有写作爱好,在业余时间进行,不谓不可。但作为一名统战部门的干部,写李宗仁归来这样重大题材的作品,这尺度和分寸你个人能把握得了吗?再说,李宗仁从海外毅然归来的背景和过程,其细节并未见之于国内报刊,你的书写些什么,怎么写,都是问题。你不可感情用事,把事情想得太简单,将来弄出毛病后悔不迭。这些年来,写文章,写书,出问题的教训还少吗?我找你谈谈,是打个招呼,爱护你,不是别的意思。你若坚持要写,写成了也得经过主管部门审查,才能决定是否可以发表和出版。这一点,也不得不提前打招呼。”
这一瓢凉水,浇得我几个晚上睡不着觉,左思右想,总解不开这个疙瘩;事情再大,已经过去十多年了,还能这么严重?再说,写李宗仁归来,是歌颂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成功和李宗仁先生的爱国爱乡之情,会有什么大错?
我别无他法,只得给王士美写信,商量这个难关怎么过。正巧,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不久便召开了。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大大鼓舞了我们的信心,解不开的疙瘩也敢于先扔在脑后。我们的工作也加快进行。王士美在长春又招来他的作家朋友顾笑言,在1979年夏天到北戴河直接与程思远先生见面,并进行一场马拉松式的连续采访。在我的先期工作和王、顾二位采访的基础上,《李宗仁归来》10万字的书稿很快写出来了。由于这之前有那位负责同志打的招呼,我自然老老实实地在北京打听,有哪位主管部门的负责同志愿意审看一下我们的稿子,把把政治关,结果令我十分失望。这些有身份的负责同志,虽然了解内情,但无一人愿意审看我们的稿件,都纷纷推托“了解有限,不好把握”。如此看来,要在北京寻找审稿的负责同志,是不可能了。
使我意外的是,王、顾二位远在东北大地,根本不想等待遥遥无期而且很有可能把书稿“处决”的有关部门的审批,而直接送交一张省辖市级的四开报纸和主管此报的市级部门审看,因为他们确信,作品在政治方向上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是一致的。
在北京方面,只要我做一件事,即得到程思远先生的允诺并拍板。在这之前,程先生已经审看完作品的初稿。
当我郑重其事地找到程先生,如实向他汇报一些有关情况,并提出听取他最后裁定的意见时,程先生毫不犹豫地说:“作品所写的事实没有问题,用的是文学的笔法,写得生动,引人入胜,我认真考虑过了,在当前的形势下,作品的发表和出版,有利于宣传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这个法宝的力量,有利于宣传毛主席和周总理在李宗仁归来这件大事上决策、筹划、安排的英明正确。我相信广大海内外的读者,也一定会欢迎这部作品的。”
事情就这么敲定了。作品在小小的《长春日报》上连载,第一章刚登完,全国陆续有几十家报刊全文连载或选载,唯独北京的报刊没有一家响应。作品未及在报刊上登完,吉林人民出版社即抢着在1980年2月成书出版,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内,即几次印刷,印数高达106万册。
作品涉嫌“泄密”受追查
但是,事情并没有完。正当我不断接到一些热心的读者来信鼓励,有的建议尽快把《李宗仁归来》搬上舞台、银幕,有的甚至寄来数万字的电影脚本时,那位负责同志又找我谈话了。使我意外的,是这位负责同志的口气比较缓和,甚至让你感觉他也是奉命办公事,不得不找我谈谈。他对我说:“你的作品发表了,出版了,我也看了,写得不错,吸引人,有这么高的发行量,不简单。但作品是三个人署名的,怎么回事?”我如实以答,是三个人合作的,并说明作品完成的最后阶段,他们两位花了大量时间。接着他又询问这两位作者的身份,我都如实回答。听完我的情况简报,他又对我说:“这件事已生米煮成熟饭。我个人看法,作品歌颂的大方向能站得住,但事情也并非这么简单。你们发表出版这本书,题材重要,特别是涉及国家安全部门的一些工作关系和手段,你们没有经过审查,已经出了差错,泄露了机密。现在,主管部门的负责同志已经表示了意见,我现在正式转告你,你们必须就这本书的形成、发表、出版写出一份详细材料,由我们审看转交,听候主管部门提出下一步处理的意见。”我听了不免一怔,但当即对这位负责同志提出问题:“涉及安全部门的事,我们在写稿前是认真研究过的,除了李宗仁归来在卡拉奇机场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随巴方救护车进机场迎接李宗仁夫妇这一个情节保留外,其他所有情节都一字未写,不知我们的作品泄密泄在哪些方面?”负责同志听我一反问,却笑了,说:“人家主管部门严厉批评的,就是你说的李宗仁在卡拉奇机场转机的情节。这不但事关安全工作,而且事关两个国家的关系,问题还不严重吗?你还是好好想想,先写一份详细材料吧。
要记住,该检讨的检讨,不要辩解。材料不仅给我们看,而且要转交有关主管部门。”
于是我又是几夜不能安眠。虽然事情的经过都在脑子里装着,要写出来费不了个把小时,但是对卡拉奇机场的情节该如何下笔呢?得费点脑子。最后,我在材料上写了三层意思:第一,在写作时认真研究过凡涉及国家安全工作的内容(调查、访问中的确涉及不少这方面的情节甚至细节),决定一个字也不写;第二,唯卡拉奇机场转机的情节,一是作品情节安排非写不可,二是这一情节与1971年基辛格秘密来华一样,在国外已是公开的秘密,特别是海外的报刊,在当时就已作过详细报道,因此我们认为已不是什么机密;第三,现在看来,我们考虑不周,警惕性不高,如造成后果,我们是有责任的。材料送上去不久,那位负责同志又找我谈话,他转述说:“你们写的材料,主管部门负责同志看了,批了几条意见,由我转达给你们:第一,卡拉奇机场的情节是泄密行为,海外的报刊怎么登那是他们的事,在我们国内的报刊上是你们第一次公开这个秘密,因此必须检讨,引以为戒,以后如发生后果,再追查处理。
第二,你们的作品发行就到此为止,以后不得再出版同一内容的电影、电视、话剧等等,也不准翻译成外文出版。
第三,所有单位必须对三位作者进行教育,避免今后再犯这类的错误,给国家利益造成损失。”
这最后的批评不谓不严厉,我们(至少我本人)只有点头称是的份儿,其实际后果,一是有两家电视台和几家话剧团改编作品的计划告吹,上海的一家话剧团已演了几场后停演了,中央和上海电视台还没有搞成电视剧便作罢——五年后又有一家东北的电视台改编并拍成电视连续剧播出,那是后事。二是后来在有关部门评选全国性的报告文学作品奖时曾有许多读者推荐我们的作品,不少评委也颇看中,但一听主管部门的首长早有过重要指示,便只好割爱。我们更应感谢的,是我们的友好邻邦巴基斯坦方面并没有就卡拉奇机场的情节提出什么异议,否则我们三位早就应该被“追查处理”了。
在历史责任感的驱使下……
一部受到海内外读者广泛欢迎的作品,却在内部受到这样那样的查问和批评,这是我当初所料想不到的。本来,我是应该接受教训从此洗手不干。
然而,出于一种自认为对历史负责的责任感,我认为不能这么做。知难而进,还是知难而退,常常是决定一件事情成败的关键。机关那位负责同志不知道,就在我参与撰写《李宗仁归来》时,我这位不听话的部下早已同时收集了有关梁漱溟先生的大量材料,已经开始在给梁漱溟写“传”了。梁漱溟这个人,却不可与李宗仁先生(含程思远先生)同日而语。那是因为李、程二先生毕竟是起义归来的人士,他们今天的历史性的举动可以把历史上的种种问题一笔勾销;而梁漱溟,这位解放后曾经独一无二地直接与毛泽东面对面地干仗,并从此落得“反动分子”而始终不得“翻身”的人,一旦加上其历史上的种种“反动罪责”,其敏感程度可以说是很少有人可以与之相比的。
事实正是这样。就在查问《李宗仁归来》泄密一事结束不久,即1980年11月间,我应约在《北京晚报》发表了一篇访问梁漱溟先生的一千多字的文章,一星期后即招来雷电般劈头盖顶的批评,该报党委为此文专门写了书面检查。那篇在1980年11月9日《北京晚报》一版发表的访问梁漱溟先生的文章《一位刚直不阿的老人》主要内容如下:
在全国五届政协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八十八岁的梁漱溟先生被增选为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同时又经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通过,被任命为宪法修改委员会的委员之一。这件事,国内外关心梁漱溟先生情况的人,都颇为瞩目。
梁漱溟先生在解放前从事了几十年的文化教育工作和社会政治活动。
但二十余年来,在国家公开的政治生活中,他近乎销声匿迹。笔者早就得知,梁先生并非生活在世外桃源,对国事不闻不问。凡在允许梁先生参加的场合,遇到重要的问题,他始终刚直不阿讲真话,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在粉碎“四人帮”不久,几位熟知梁漱溟先生的前辈又告诉我,历史在证明梁先生不仅是一位多年来坚持讲真话的人,而且并非都是“反动话”,其中有不少话经得起实践的检验。他们都建议我去梁先生家作一次专门采访,还指明着重写写讲真话的问题。前不久,在梁先生担任全国政协常委之后,我终于去了。在梁先生的新居里,向他说明来意之后,他笑了笑。这位老人,看上去身子骨瘦小,但耳不背,眼力好,精神尤佳。他慢而有力地对我说:
“我一生经历的事,说来话长。是非曲直,当由后人评论。但我在做人的道理上,平生所敬重并力行的是八个字,叫“独立思考,表里如一”。我做得怎样,也应当由旁人去评论,而决无自我标榜之理。”
梁先生一面说,一面从沙发上缓缓站起来,由客厅走进卧室,不一会取出一迭旧稿纸递给我,接着说:“我所经历的事,凡能保存的尽力留在手头。你可先翻翻这些材料,然后再谈。”
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工整秀丽、苍劲有力的笔体,看着看着,就把我吸引住了。二十余年,往事如云,笔者只能摘录几段。
“如何评价孔子,看孔子在历史上的影响,是好是坏,是大是小,站在今天的高度来评量,应当一分为二。绝对的肯定或绝对的否定,都是错的。我现在认识到的孔子,有功、过两个方面,在没有新的认识之前,我只能表里如一……”
梁漱溟还说过这样的话:林彪公开说的话都是假话,用假话骗取信任,是说假话的第一能手。林彪是个鬼,他够不上一个人,这就是我对他最严厉的批判。而刘少奇、彭德怀等诸位都有为国家、民族前途设想的公开主张,是说真话的。
据梁漱溟先生介绍,讲这些话的时间是1974年。其时正值江青一伙上演“批林批孔”的闹剧,把偌大的中国搞得天昏地暗。慑于这帮政治流氓的淫威,多少人被迫讲违心之言,创造了中国历史上讲假话的破天荒纪录。在那种时候,梁先生因为讲了这些真话而理所当然地受到整整一年的大小会批判。
笔者不敢说梁先生的这些话句句都对,但拿它来印证梁先生一开头讲的“独立思考,表里如一”八个字却是绰绰有余的。
我把话题引到当前:“梁先生,您老现在的心境如何?”
“三十而立,这又是孔夫子的话。”梁先生爽朗地笑出声来:“新中国三十岁出头,经验有了,教训也有了。现在走上了正轨,集体领导与民主法制逐步加强,这是最稳妥的路子。朝这个方向走下去,实现四化是有希望的。”
“您老现在忙些什么?”我接着问。
“我身体尚好,但近几年也感觉头脑昏沉,记忆力差。”梁先生放低了嗓音说:“但还是每周参加政协组织的学习和一些会议。平时在家看书学习,精神好就写写东西,有时还要接待和处理内外的来访来信。”
唔,我还差点忘了,来时有人告诉我美国出了有关梁先生的专着,立即问他:“梁先生,是美国出版了有关您老的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