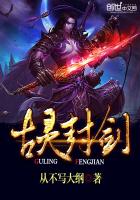我终究还是逃不过这场劫。
我告诉自己说,将来某一天,我会真正长大的,我会忘记的,可那一天迟迟不肯到来。
我叫蒲絮,我有一个大我三岁的哥哥,我们是同父异母的兄妹。我觉得有必要来讲讲我的家庭。哥哥的妈妈是爸爸的原配,用通俗的话来说,我是狐狸精的女儿,私生女。
从小就背负没有爸爸的的苦痛,渐渐地已经不会去问我的爸爸在哪里这样的问题,呵呵,那给我的是突如其来的母亲的谩骂殴打和眼泪。好吧,我是个没有爸爸的孩子,风言冷语让我忘记了疼痛,呵呵,没事的,就这样卑贱地活着。
放学回家的路上,穿过一个黑巷子,我已经习惯了,一群背着书包的高年级的男生女生围住我,我顺从的在墙角蹲下来,闭上了眼睛。污秽的脏话和着拳脚密密袭来,疼痛,但是没有眼泪,我就是他们的出气筒,一个十岁的孩子学会了逆来顺受。
住手!你们在干什么?!一个声音从人群外面传来,人倏忽间逃散,我躺在地上,看见一双白球鞋朝我走近。他蹲下来,对我说:小妹妹,你没事吧。我从地上爬起来,擦掉泥土和血迹,背上书包匆忙逃跑,我抬头看了他一眼,只一眼,余生不忘。
这时候我随母姓,叫柳絮。
三年后,有个西装革履的男人找到我家,后来母亲就嫁给了他,他执意要我随他姓,我便更名为蒲絮。
我们住到了一起,过上了我从没想过的生活。
当晚,我们在一起吃饭,爸爸拉着我的手说:小絮,你看,这是你哥哥。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一个清瘦的男生默默的夹菜扒饭,爸爸大声说:蒲岭,你没长耳朵吗?!男生这时才极不情愿的抬头看我一眼,然后说:知道了。
他一抬头就吓到我了,三年过去,我竟然又看见他,而且我们竟然成为一家人!他忘了我,可我又怎么会忘记他,那个叫我小妹妹的人,那个第一次让我感到被爱的人。
吃罢饭他就出去了,我悄悄跟在后面看见他上了上了楼顶。我退回来,抓起两瓣西瓜就往楼上跑。他靠在角落里一动不动,抬眼望天,天上全是忽闪忽闪的繁星。他突然就注意到我:你跟着我干吗?
我举起西瓜给他看:哥哥,吃西瓜!
他粗暴的推开我:不吃!不要叫我哥哥,你不是我妹妹,我只有一个妈妈,我妈妈只有一个孩子!我不会接受你和你妈的,滚!
那几年他们的欺负也没让我掉一滴眼泪,可是他愤怒的眼神却让我湿了眼。我咬住嘴唇不让眼泪落下,放下西瓜仓皇逃离。
第二天早上我起得很早,他房间里面整整齐齐的,看来一夜未归,我跑上楼顶的天台,发现他蜷缩在那里,睡着了,眉头拧成一团,西瓜没有吃被他碾成了渣。
他是这样坏脾气的人,可当我收了盘子准备离开时,他居然在轻声啜泣,我握住他的手,他轻声呼唤:妈妈······
他的妈妈已经去世两年,少年依然不肯接受现实。
我伸手擦掉他的眼泪,又轻轻将他紧缩的眉头舒展开。我怔怔的看着这么好看的脸,一种莫名的悲伤铺天盖地席卷而来。
在他醒来之前,我已经离开天台,我迅速洗漱好,躲进卧室听外面的动静。许久之后,终于听到洗漱的声响,过了一会,我听见门吱呀一声响了,我拉开门追出去:哥哥,你去哪里?
他回头看我,皱了一下眉头:晨练。
我兴冲冲地说:哥哥等我,我也去!
他的眉头又拧作一团,不说话,我就当默许了吧。
他跑得很快,我在后面跟着,气喘吁吁,如此笨拙。
我实在跑不动了,我大喊:哥哥你等等我,我跑不动了!
他还是不回头,步子却明显放慢了,等我赶过去,以为可以和他并肩的时候,他又加快了速度。
我知道我们之间始终保持着距离,不是三五米,而是只有我们两人能看见的天涯海角。
一个暑假的不冷不热的接触,他的态度已经明显好了很多,他总是沉默,可是晨练时已经熟练的掌握和我总保持五米的技巧,五米,五步,我始终追不上。
你有没有听说过一种名为五步的毒蛇?
每次我在后面看着他清瘦的背影和我们之间看起来即长又短的距离时,我总是会绝望的想起这种蛇。听说这种蛇毒性很烈,被咬的人在走五步的时间内毒发身亡。很恐怖的样子。
也听说过一个笑话,儿子问爸爸如果不走五步会不会活下来,我也想知道如果只走四步会不会死。
也许我和他之间隔有雷池,不可逾越,但是我想知道等我长大了,我是不是就可以跑得更快了,不乞求与他并肩,真的,向前跨四步就好了,我只想与他更近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