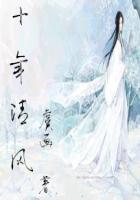我知道,我是在想念Cloudy。一只狼,从嗷嗷待哺,到成长为《狼图腾》电影里的明星,中间的坎坷、痛苦和欢乐,我都亲身经历,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都和Cloudy共同度过。就像在一起相处了几年的老朋友,不,更像是亲人,我和Cloudy早已结下了一生都无法解开的缘分。
我想念Cloudy。安德鲁发过来的照片已经不能满足我的想念。我想见到Cloudy,再次轻抚它的颈背,感受它对我的亲昵和信任,感受它充满自由狼性却对我无比温柔的眼神。
我拨了安德鲁的电话,他竟然没接!
这个家伙,肯定是在狼舍里驯狼吧,说不定正在和Cloudy嬉闹呢。可安德鲁有那么多狼,也许他最喜欢的不是Cloudy,Cloudy会不会失宠?会不会在异国他乡受欺负?哪只狼敢欺负Cloudy,我知道了决不会放过它!
我再次拨安德鲁的电话,响了很多声仍然没有回应。
我的心一下绷紧了。难道是出了什么事情?安德鲁为什么不接电话?Cloudy出事了?!我拿着电话的手微微颤抖着,手心里开始出汗。
电话终于应答了,听筒里传来安德鲁低沉的声音。
“怎么才接电话?”我真是急了。
“哦,我刚才带着一只狼去做手术,刚刚回来。”安德鲁依旧不紧不慢。
“做手术?哪只狼?不是Cloudy吧?!”我嘴上说着不是Cloudy,可脑海里想的全是受伤的Cloudy躺在手术台上痛苦的样子。
“不是,Cloudy可好着呢,是新来的一只狼。”
“啊,你怎么不早说?!”我一下子释然了,虽然也为那只做手术的狼担心,但Cloudy安然无恙,我一下子放松下来,“手术还成功吗?”
“没问题,小手术。”安德鲁真是个不会聊天的人,问什么答什么,一点儿也没有老朋友的热乎劲。
“嗯,那就好。我……没什么事,问问Cloudy的情况。”
“它很好。”
“嗯,电影后期这边也很顺利,你忙你的工作吧。”
“好。”安德鲁的话越来越少。
“那就先这样吧,有事打电话。”我也不知该说些什么了。
“好的……哎,Max……”
就在我即将挂断电话的一刻,安德鲁终于主动要表达了。
“什么?”
“Max,你是不是想来看看Cloudy?”
安德鲁的声音不大,语速也不快,可这句话如同一股暖流灌注了我的全身,他怎么能知道我心里的想法?!我还有点儿不好意思说呢。
“啊……是啊,我挺想Cloudy的,没什么,你多发发照片过来吧。”我真为自己的虚伪感到难过,明明是很想去加拿大看望Cloudy的,又不愿完全展示自己的情感。
这也许就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东方人含蓄,而西方人更直接。
“Max,你来加拿大吧,Cloudy想你,我们也很想你。尽快安排吧。”安德鲁真够直接坦率。
是安德鲁帮我下定了去看望Cloudy的决心,这个电话打得真是值了!
我的行动没有丝毫犹豫,订机票,收拾行囊,即刻启程!
加拿大的气候比北京冷,下飞机时,这里已经开始下起了小雪。
我换上特意准备的厚衣服穿上,寻找来接我的人。通常的情况是应该看到一块高高举起的牌子,上面写着“Max Wang”的字样,可找了半天也没见这熟悉的字眼。直到这架航班的旅客几乎全部散去,接机的人群也都找到自己的客人热络地聊着天离开,我彻底绝望了。
我气呼呼地拨通安德鲁的电话,不等他说什么便开口质问。
“安德鲁,我已经到了,在机场。”
“好的,我想你也该到了。你直接到巴士站,看看图示就可以找到来我这儿的车。”安德鲁轻描淡写地说着,从语气中好像可以感觉到他还在忙着别的事。
“你不打算来接我吗?你在干吗?”我直接将怒气喷出。
“哦,不用接,你坐巴士非常方便的。”
“你到底在做什么?”
“我嘛,在清洗狼舍,为了迎接你!”安德鲁这才显露出一些兴奋。
天哪,这个毕生与狼共舞的世界顶级驯狼师,竟然不亲自到机场来迎接一位远方的客人,还说什么清洗狼舍迎接我?早干吗去了?!
我挂断电话,拖着行李直奔巴士站,顺利地选择了我该坐的那趟车,怒气这才慢慢消解。看着安静地排队等候上车的人们,我似乎理解了安德鲁的“失礼”,他把全部精力都用到养狼驯狼上了,对这些“人之常情”全然不放在心上。我也是一个成年人,既然可以独立到达目的地,又何必浪费人力物力来接我呢?正是因为安德鲁的这种专注和敬业精神,才使他那么地与众不同,才使那么多部与动物有关的电影拍摄成功,才使我们的巨著《狼图腾》在难以实现的情况下完整地呈现在镜头中。
这时,安德鲁的电话追过来。
“Max,非常抱歉没能去接你,我真的忙着呢。”
“没关系,我已经登车了,回头见。”我释然地回应。这个安德鲁,看起来不谙俗礼,但事情还是做得缜密。千万别低估了他的情商,和狼一起生活了多年的他,必定也拥有狼的智慧和“狡猾”。
巴士行驶在略显空寂的路上,小雪打在车窗上,很快化为雪水流下。我看着窗外的景色,灰蒙蒙的天,空旷的原野,伸向远方仿佛没有尽头的公路,内心竟隐隐升起一丝身在异乡的哀愁。这才是刚刚飞到加拿大啊,不知道Cloudy在这里会不会也在想家,想念它从小长大的北京的狼基地,想念在广阔的内蒙古草原上在摄影机前一条条地完成规定动作。我的脑海中,还是将近一年前那幅机场送别,我在铁笼外不知所措,Cloudy在铁笼里急切地想要冲出来的情景。
随着点点滴滴的回忆,巴士开了不知多久,时间悄然消逝。
安德鲁这次表现得还算不错,当巴士车门打开,我一眼看到他依旧沧桑但笑得纯真灿烂的脸。
“Max,欢迎你!”安德鲁张开双臂。
“下次去中国,我也不会到机场接你!”我和他拥抱,嘴上还是嗔怪。
“没关系,我对中国很熟悉了,我自己认识路。”
我和安德鲁都笑了,的确,《狼图腾》这部电影前前后后耗费了近五年时间,有多少人能再用五年的时间全心全力打造一部电影!
当我随着他走近狼基地时,心中还是感到震撼。如果不知道内情,远远望去那就是一片优雅的别墅,怎能是饲养狼的所在?国内我们辛苦建立的狼基地和这里比起来,简直是太简陋了。
“Max,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没关系,拍电影时的基地是在特殊条件下的特殊需要,而我这里是专门为了狼感受生活的。”安德鲁几乎看穿了我的内心。
我注意到他用了“感受”一词,不是“享受”。是的,安德鲁的理念是以天性和自然为本,虽是饲养,但绝不让狼太过安逸和太过拘束,尽全力将人和狼的距离缩短,又尽可能地保留狼的野性。他的狼在这儿生活,将点点滴滴地“感受”世界,绝非享受。
“Cloudy呢?它感受的生活怎么样?”我笑问。
“这个嘛,我说了不算,要等你来评判。”
安德鲁的女朋友早就和团队里的“女同志们”等在门口迎接我,个个笑容灿烂,精神十足,还没等我开口,便一窝蜂地拥上来。女孩子们像是商量好的,给我来了个轮番熊抱,每一个熊抱都几乎让我喘不过气,箱子也倒在地上,背包更是歪在一旁。在这样的窘态中,我的眼睛一下子湿润了,时光仿佛回到拍摄电影的过程中,那时候,我们全剧组同甘苦共患难,有过多少次挺过艰难庆祝胜利的拥抱啊。
“我爱你们!”我忍住泪水,大声表达对她们爱。
我最想见到的,还是Cloudy。
在安德鲁的陪同下,我激动地走向狼舍,双手不由得轻轻发抖。我沉默着,安德鲁也沉默着。
离狼舍还有些距离,我就敏感地觉察到异动的气息,一阵杂乱的脚步声伴随着粗重的呼吸声灌入耳朵,我知道,狼们知道有人来了,更确切地说,其中的几只应该知道是我来了!动物有很多超乎人类想象的能力,不管是视觉、嗅觉、听觉都格外灵敏。尤其是狼,更拥有一种超强的感知力,即使是几十年前相识相知的人,它们也能在有障碍有阻隔的情况下,清晰地辨识出来。
何况我和这些狼分别不满一年。
当我的目光透过铁网,看到狼群时,满溢的幸福感几乎要从胸口涌出。
Parker、Silver等若干只从中国远渡重洋而来的狼们,正聚集在铁网后,有的用热切的眼神,有的用轻快的叫声,有的干脆用前爪趴在网上,以种种美好的姿态欢迎我。在明确了我的到来后,狼群更加躁动,它们干脆跑动起来,扬起片片雪水,那场面,真该拍摄记录下来。
“孩子们!”我不假思索地喊着,这句话绝没有任何装腔作势的意思,完全是脱口而出,接着加快脚步走上前。
我轻轻地把手搭在铁网上,胆子大些的Parker干脆把嘴伸过来轻触我的手指。
“Parker,坏家伙!”我抚摩着Parker的鼻尖,看着比一年前更加壮实的它,早已忘却了它曾经夺走Cloudy王座的愤怒。
“Parker已经不是狼王了。”安德鲁淡淡地说。
“这是狼群的规则,其实也是自然界所有动物的规则,胜者为王。来加拿大不久,另一只狼就开始了和Parker的争霸战。”
“Parker伤得重吗?”
“没关系,这是狼王必须要承受的。”安德鲁笑着说。
“怎么没见你的狼?”我很好奇,这里都是从中国带来的狼。
“我还没把它们和北美狼融合在一起,”安德鲁指指另一边的狼舍,“我觉得还不到时候,现在放在一起肯定会引发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
“哦,会有死亡吗?”
“会。”安德鲁点点头。
不知为什么,我始终没问出那句我最想问的话。Cloudy在哪儿?Cloudy并不在面前的这群狼中,它在哪儿?它最应该第一个出现在我面前的啊!
我不敢问,怕听到残酷的回答。
“看,Cloudy!”安德鲁似乎洞悉了我的心,指着铁网侧面一处不显眼的角落。
我顺着方向看去,只见那一簇紧贴地面生长的草团旁,站立着一只大狼,正侧着头用沉静、深邃的目光望着我。
Cloudy!
虽然隔着数步的距离,虽然它比分别时身形更大体格更壮,虽然它只是远远地冷静地注视我,并没有表现出像其他狼那样的热情,我仍然可以确定地判断出那只狼就是我朝思暮想的Cloudy!
“Cloudy!”我的声调提高好几分贝,叫了一声,这肯定是我来加拿大后发出的分贝最大的声音!
Cloudy依旧站在原地看着我,只是身体微微转过来,可脚下一步都没动。
我呢,也似乎被什么东西粘住了双脚,腿僵僵地戳在原地。
“怎么样?Cloudy在我的关照下,生活得不错吧?长大了很多。”安德鲁有些得意。
可我根本不理会安德鲁的语意,心里完全被另一种情绪控制了,诧异和伤感在胸口翻涌着。为什么?为什么Cloudy不冲过来和我相见,为什么它看我的眼神那么陌生?为什么就算我激动地喊了它的名字,它仍然无动于衷?难道那不是Cloudy,只是一只长得和Cloudy一模一样的狼?
“嘿,它在等你过去!”安德鲁打断了我的思绪。
是呀,也许是相隔时间太久,Cloudy的确不太记得我了,人还有健忘的时候呢,何况狼?既然想念,我又何必计较这细小的感受。
我打起精神,展开笑容,伸出双臂快步走向Cloudy,同时呼喊着它的名字。
Cloudy还是冷静得像一尊雕像,对我的热情没有任何回应,当我走到它面前,隔着铁网伸出手示好,盼望它能像从前一样,探过头用长长的嘴亲吻我的手指,然而,让我寒彻身心的一幕发生了!
Cloudy竟然侧过头去,迈着不紧不慢的步子,走远了,如同我只是一股空气!
现在轮到我是雕像了!我呆呆地僵在那儿,笑容凝结在脸上,望着Cloudy的背影,嘴唇动了动却没能发出任何声音。Cloudy拒绝了我!
安德鲁走过来轻轻拍拍我的肩膀,“Max,别着急,你来得太突然了。”
我缓过神,身体被强烈的寒意侵蚀,轻轻地发抖,在本已寒冷的加拿大,Cloudy让我更冷,更寒。
“呃……还好吧……”我尴尬地咧咧嘴,说出一句自己都不明白什么意思的话。
“别忘了,Cloudy可是咱们最有个性的明星狼,当然要有些明星的风范嘛。”安德鲁继续安慰我。
“是……还真以为自己是大明星呢,这个家伙!”我也尽力为自己的尴尬开脱,可目光一直没离开Cloudy。它走到狼舍旁,安静地趴下来,也看着我,一脸若有所思的目光和神情。
到底是怎么啦?!Cloudy,你真的不认识我了?我千里迢迢就是为你而来啊!
在安德鲁和诸位姑娘为我准备的欢迎宴会上,大家说说笑笑,回忆往事,很是尽兴。可我心里的问号越画越大,在Cloudy的身上,一定发生了什么特殊的事情,否则,它是不可能对我视同陌生人的。我可以接受任何一只狼的麻木和冷淡,但Cloudy不行!
会有什么特殊的事发生呢?觥筹交错中,我冷静地打量着安德鲁、姑娘们和每一个工作人员,一种奇特的想象在我的脑海中慢慢荡漾起来—难道就像某些耸人听闻的小道消息所说,这些外国人在用Cloudy做某种动物实验?Cloudy是纯种的蒙古狼,具有一定的科研价值,尤其是它的智商和情商都超过同辈,更值得研究。我一边喝着酒,一边陪着所有人谈笑,一边思索着这个荒唐至极却又有模有样的假设,逐渐,每个人在我眼中都变成了嫌疑人,每个人都成了侵害Cloudy的坏蛋,安德鲁温和的笑容变成了伪善。
愤怒和悲伤在胸口积聚,我再也忍不住了!
我拉着安德鲁走出房间,来到稍稍安静的地方。安德鲁很不解,嘲笑我喝醉了,直到我用咄咄逼人的目光盯着他,他才也严肃起来。
“Max,怎么了?不舒服吗?”安德鲁关切地打量着我。
“告诉我,你们到底对Cloudy做了什么?!”我直奔主题。
安德鲁望着我,完全迷惑了。
“Max,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你们做了什么,难道自己不清楚吗?!别装糊涂!”
事后想想,我当时真的冲动而愚蠢,竟然把胡思乱想武断地当作事实,还把怒火无端地倾泻在安德鲁身上,要知道,安德鲁可是最爱狼,最尊重狼的人啊。
“Max,我真的不明白你的意思!”安德鲁显然也有点儿火了。
“Cloudy为什么不认识我了?!”我大声地喊道。
此话一出,安德鲁明显地怔了怔,接着便低下了头,这个举动更是让我误解为他做了亏心事。
“安德鲁,我太信任你了,我把Cloudy交给你,可……可是你……”说着说着,我不由得哽咽了。
“Max,我明白你很难过,稍晚些时候,我会好好和你谈一谈。”
安德鲁轻轻留下一句后便转身走了,只留下独自站立在寒冷中的我。郁闷,不解,怀疑,悲伤,随着星星点点的雨夹雪打在身上、脸上,像刀割一般。
欢乐的宴会结束,一切归于寂静。
我呆呆地坐在房间中,等待安德鲁。
门开了,安德鲁走进来,并没有坐,而是靠在窗边,望着不远处的狼舍。
“Max,有很多事,你的确不知道,我也曾经反复思考,到底要不要告诉你。”
我没作声,期待安德鲁继续说。
“Cloudy刚刚从中国来到加拿大时,生过一场重病,险些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