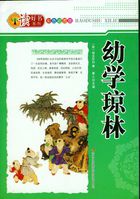我蹲在地上,摸索着狼掏洞时挖出来的土。
“走,基地里能活动的人都跟我走,找狼去!”
找狼,说起来容易,那可不是在马路上丢了个纸箱或者毛绒玩具,环境清晰目标大,实在找不着没准儿还会有个好心的路人给你送回来。现在这可是茫茫草原,天高地阔,绿草丛生,别说丢了两只活蹦乱跳、有自主意识的狼,就算真的在草原上停一辆卡车,你也得费上一番工夫才能把它找出来。最近就有过这样的事,剧组的一辆车就停在拍摄现场不远处的草甸上,可好几个工作人员转来转去就是没发现,我当时还埋怨他们眼神太差,其实那应该是一种正常现象,姑且把它叫“草盲”吧,和雪盲的意思相近。
我们一行人急匆匆地赶赴拍摄现场,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想,狼白天在这里拍了一天,这里应该是它们比较熟悉的地方,也许会在这儿呢。我闷闷地一言不发,其他人也一言不发,东张西望地搜寻着,这纯属自我欺骗,给紧张的情绪找个发泄口。
到了拍摄地点,我放慢了脚步,真希望两只狼像迷失的孩子一样正等着妈妈寻找它们,可我心中又充满恐惧,害怕见到空空荡荡被铁丝网围起来的空地。一瞬间,我的头脑一片空白。
“没有!不在这儿!”
不知是哪个讨厌的家伙喊了一句,把我从幻想中彻底拉回到现实,的确,眼前就是空空荡荡,没有狼,没有人,也没有任何垃圾,仿佛白天根本没在这儿拍摄了很多场戏一样,只有冷冰冰的铁丝网埋在地面,一直向远处延伸,圈起一片巨大的草地。
“什么没有?!你们找了吗?都去找啊!”我无法承认这个结果,只好把怒气发在随行人的身上。
大家得到命令,纷纷钻进铁丝网,沿不同方向散开搜寻。
我环顾四周,天苍苍野茫茫,傍晚的草原掠过阵阵凉风,穿透了我的身体。
“快点儿,快出来吧,别跟我玩儿了!”我也钻进铁丝网,一边找一边轻声地自言自语。
天很快黑了下来,虽然有月光照亮,但视线已模糊不清,找狼肯定是没戏了,别再把人丢了就好。我召回一起来的工作人员,大家一个个灰头土脸神情沮丧,看来是没什么发现。
“回基地,明天一早继续找。记住,这件事我不发话谁也不许把消息传出去!安德鲁和阿诺导演也不能知道!”说完,我转身头也不回地大步离开,工作人员们垂头丧气地跟在后面。
基地里难得清静。大多数人都去休假了,剩下的都是找了半天狼,啥都没找着,又累又怕的倒霉人。除了狼舍里偶尔有几声狼叫,只剩下了寂静。我疲惫地躺在床上休息,心中倍感凄凉。
狼丢了,两只,后果很严重。
如果两只狼跑进了牧区,恐怕牧民的牲畜要遭殃了,虽然这些狼是人工喂养长大,但骨子里的天性是不会磨灭的,饿了一样会对牛啊羊啊发起本能的攻击,万一阴差阳错地攻击了人,后果不堪设想。
如果这两只狼死了,会对拍摄产生重大影响,临时去找新狼,安德鲁还得从头训练,时间不允许;用狗代替,阿诺导演也不会同意;就这么少两只狼愣拍下去,效果肯定不好。
更重要的是,全剧组好不容易培养起来的人和狼的良好关系将会受到打击,大家再也不会像从前一样把这些狼当成可爱的伙伴,大家会觉得这些狼是野兽,必须要敬而远之。那时,后面的拍摄状况可想而知,会有越来越多难以解决的问题。
我独自坐在休息室,尽量让自己平静下来。其实,静下来又能思考些什么呢?现在能做的,只有等待和祈祷。腾格里啊,现在是拍摄的关键时刻,请你看在我们全剧组几百人和这么多狼的情分上,保佑那两只莫名失踪的狼吧!最好,明天一早这两个“离家出走”的坏蛋,突然出现在狼舍里自己回来“报到”了。
工作人员匆匆跑来汇报,我急切地期盼着他能带来好消息。我们早已跟牧区联系过,只要有人发现两只狼的踪迹,不管是死是活,马上通知基地。工作人员看着我焦虑期盼的表情,想说又不敢开口。
“快说,什么情况?!”我抓着工作人员的胳膊。
“牧区来电话说……他们没发现狼,还说,如果狼真的侵犯牲畜和人,他们只能采取必要的行动。”
采取必要的行动?我的心一下凉了半截。当人们面对扑向自己的狼时,最必要的行动就是拿起武器,毫不留情地将狼解决掉。完了,我的两只狼啊,虽然不是最重要的两只,可毕竟是我亲自选定,亲自接回,亲眼看着它们长大的,想到它们很可能变成两具尸体,我的眼睛一下湿润了,泪水差点涌出来。我赶紧对工作人员挥挥手,转过身去。
工作人员默默地走了,我下了命令,所有人今晚都早早休息,明天天一亮便出发,继续找狼!
很奇怪,我竟然睡着了,也许人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反倒想用睡眠来逃避难以解决的问题吧。闹钟把我从睡梦中惊醒,当我推开门时,工作人员们都站在院子里,整装待发,我略感欣慰,要是之前大家都如此“严阵以待”,狼恐怕也丢不了。
凌晨的草原充满寒意,我们借着天边微微的白光匆匆行走,没人说到底去哪儿找,但大家还是不约而同地奔向拍摄地,被铁丝网包围的那一大片草甸,似乎只有那儿能带给我们一丝希望。
“带上狗吧!”一个人说。
我仔细地想了想,这似乎是个好主意,电影电视剧里的情节不都是让狗去寻找和追击吗?可我们的狗行吗?它们没经过类似警犬的搜寻训练,能听从指挥吗?再说,朝夕相处和拍摄过程中,这几条狗早已把自己当演员了,动不动就闹点儿小情绪,伺候不周的话还要罢工呢。我决定还是不带狗去,免得带来更多麻烦。
赶到目的地时,天已大亮,我快速给每个人分配了搜索区域,大家散开行动。我也给自己留下最大的一片区域,一步步地用脚丈量着这片草地,职业习惯让我永远无法把最重要的事情交给别人,只有亲自上阵才放心。
也许是昨晚我的祈祷感动了腾格里,也许是真相早就在那儿等待着,总之,搜寻开始不久,便有了进展。
“大家散开仔细找,争取能找到脚印!或者狼粪!”
工作人员们依照我的命令,有的蹲在地上,有的几乎是趴在地上,观察狼的脚印。如今正是草皮丰厚的时候,狼轻盈的步子踩在上面,什么也留不下,我很清楚大家认真寻找的样子更多的只是自我安慰,可谁都不愿说穿,宁愿自我安慰下去。
我也和大家一样,单膝跪地,瞪大了眼睛,一寸都不愿放过地搜寻着蛛丝马迹,经常被一块土坷垃或一小团枯草吸引,兴奋地研究半天,再失望地连连叹气。腾格里啊,你给了我们希望,却又关上了通向希望的门!
时间就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了。我满头大汗地坐在草地上稍作休息,放眼一望,工作人员们也在寻找中不知不觉地越走越远,铺散在很大一片区域,此时的他们,也一个个地或躺或坐在草地上,满脸通红大汗淋漓,有的还捂着胸口呼哧呼哧喘气。
太阳就在头顶,整整一上午,一口水都没喝,就这么找啊找,太辛苦了,我看得都有些心疼。其实,寻找脚印是个很笨的方法,可除了用这种笨办法还能怎样?两只狼从洞里逃出来,可以去往任何方向啊,它们才不会给我们留点什么记号方便联络呢。
“好了,我们回去!”我扯着脖子用尽最后一点力气喊道。
工作人员们都听到了,但几乎没人有力气回应,大家满身灰土狼狈不堪地向我聚拢,走起路来腿脚发软。丢了狼就够呛了,别再把人累坏,那可是更大的损失。
“还找吗?”一个工作人员怯怯地问。
“别问了。回去好好休息,能找到总会找到,我们已经努力了。”我安慰大家。
回去的路上,我低着头认真思索着。事到如今,迅速把狼找回来几乎是不可能了,该怎么向阿诺导演和安德鲁解释这件事呢?最好的办法可能就是直说了。我故意放慢脚步,落在队伍后面,拿出手机,先找到安德鲁的电话号码,这家伙也许正在什么地方享用中国美食吧?听到狼丢了的消息,他会是什么反应呢?我犹豫着,手指稍稍用力,马上就要拨通安德鲁的电话。
“看,那边有只野兔!”一个年轻的女工作人员喊起来,毕竟是年轻,还有精力和情趣关注自然呢。
大家的目光不自觉地望过去,只见不远处一个隆起的小山丘上,真的有只野兔在前后左右地乱蹦乱跳。
“哎呀,后面还有只狗在追呢!”另一个小姑娘也喊起来。
我慢慢放下手机,也驻足观看“狗”追野兔的事情,定睛细瞧,一股电流迅速传遍我的身体。什么叫狗追野兔?!那分明是一只狼!
“不是狗,是狼!”其他人也看清楚了,纷纷叫喊。
“又一只狼!”
山丘后,果然又蹿出一只狼,加入扑赶野兔的队伍。
“两只狼,是我们的狼!我们的狼!”大家的情绪沸腾了。
由于距离较远,两只狼追野兔的情景像是动画片或皮影戏,它们的动作似乎并没有那么矫捷凶猛,而是像野兔一样一跳一跳的,煞是可爱。
“都别喊了!小声点儿!”
我命令大家安静,观察了一下地形,领着两个饲养员从侧面慢慢包抄过去,其他人原地待命,唯恐惊动了两只狼。
我们压低身体,慢慢地靠近,视线越来越清晰,没错,就是这两只狼!好啊,当了逃兵,害得我们一通好找,你们却在这儿快活!
两个饲养员就要过去抓狼,我示意他们趴下,三个人一起观看两只狼和兔子的游戏。
这的确是游戏。两只狼扑打着跳跃着,完全跟着兔子的节奏,兔子往东它们往东,兔子往西它们往西,兔子停在原地喘气,它们也停在原地喘气,兔子盯着它们看,它们也就傻傻地盯着兔子看。虽然有时两只狼的爪子会抓住兔子,牙齿也会碰到兔子,但它们还真的没有想下狠手的意思。
“什么时候喂的食?”我问。
“昨天最后一条戏的时候,吃了很多。”饲养员说。
“怪不得,看来它们不饿,饿了早就把兔子吃了。”另一个饲养员说。
“不,它们根本不会吃,根本不会抓兔子!”我说。
看着眼前的游戏,我心中忽然升起一种惭愧,让我自己都有点儿莫名其妙。这些狼,从小在我们的关心和爱护下长大,虽然吃喝不愁,但缺失了最重要的东西—狼性。它们本该是驰骋在草原上的优秀猎食者,它们本该成为草原的主人享受天蓝地阔的美好,可命运,或者说是我们人类,为了某种目的把它们关进铁笼,围进铁丝网,它们从未真正感受过自由的滋味,却对自由有着与生俱来的向往。这两只狼的表现正是如此,只要一有机会,就会离开熟悉的环境去寻找自由,而追赶兔子的“游戏”,正是本性在驱使它们学习捕猎,这种学习对于狼来说,显然是太晚了,因为,它们只会玩儿追赶兔子的“游戏”,根本不知道怎么将追到手的兔子杀死后变成美味的食物,真是充满“爱心”的狼啊。如果把Cloudy那些狼放回草原,等待它们的只有死亡。因为最重要的生存本领和技能,它们从没实践和练习过,在残酷的自然法则中,它们是“废物”。
想到这些,我内心的愧疚感越发强烈。
一个饲养员的身体移动惊扰了两只狼和兔子,它们扭头看着我们的方向。我站起身,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安德鲁平时在训练时奖励给狼吃的特制“零食”,朝它们挥手示意呼喊着“Good boy, Good boy! Come on!!”两只狼看着我,竟然没有丝毫惊慌,眼神中流露出亲切和熟悉,它们像平时在训练中一样朝我奔了过来,欢快地接受了美味的“零食”,几个饲养员趁机围了上去。我再一次从心底感激安德鲁和他的驯狼团队,正因为他们平时对狼的训练有素,今天即使出现了这样的突发情况,我们也能够如此轻而易举地把狼带回基地。
好了,两只狼终于被“捉拿归案”。离开时,我看到其中一只狼依依不舍地回头看看刚才扑赶兔子的小丘,兔子早已逃得无影无踪了。我心中更加不是滋味,小狼啊,对不起,也许你们很难回归自然了,但我保证让你们幸福地活下去。
“这两个不听话的,回来好好饿它们几天!”大家七嘴八舌。
“不行!给它们吃!谁也不许欺负它们!”我斩钉截铁。
我发誓,要对所有的狼好,比以前更好。
休假的人们纷纷回到基地,人们说说笑笑,气氛欢快而融洽。
安德鲁正和阿诺导演对着剧本,讨论着明天的拍摄情况,我坐在休息室,从窗口望着他们。
他们哪里知道,刚刚发生过一个有惊无险的故事。
《狼图腾》杀青了,终于可以长长地松一口气了,但离别的哀愁却深深地笼罩着我。拍完电影,狼怎么办?所有的人都在问我同样的问题,也是我问过自己无数次的问题。我不想和安德鲁比谁和狼的感情更深,这是不同的感情,但同样的是,我和安德鲁都对这些狼充满了爱,尽管有深深的不舍,但是正因为爱,我只能忍痛放手。
我考虑再三,确定了加拿大是Cloudy和狼们的最好归宿。
我开始给Cloudy和其他要飞往加拿大的狼孩子们,以及几条狗孩子们办理“移民”手续,这是我们中国自开国以来第一例以电影名义对外国进行的动物赠送。因为时间非常紧迫,我在各种手续中东奔西跑,忙碌不堪,甚至忘记了去想念Cloudy,只有在晚上回到家后,静静地闭上眼睛,才一幕幕地回忆着这几年和Cloudy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有好几次,我都盼望着要是手续出了问题办不下来就好了,Cloudy就可以顺理成章地留下来,尽管留下来的生活并不会太好。
直到飞往加拿大的飞机起飞前的几小时,我才将所有手续全部办好,而那时,Cloudy和其他总共十六只狼,包括狼狗Rusty和其他几条狗都已提前运往机场,准备空运了。
我以最快的速度驱车去机场,心中不断祈祷,Cloudy,别走,等等我。
高速路上,往来的车流都幻化成光点,一切声音都归于静寂,我想象着在机场,Cloudy向我奔来,我们再一次深情地拥抱在一起,它不停地拱吻着我,而我在它的颈背上抚摸,最后的告别,一定要留下最美的回忆。
停好车,我一路狂跑,不断地扬起证件,通过重重关卡,几乎没有浪费一秒!
然而,等我终于冲到货运仓库,眼前的一幕让我顿时从头冰冷到脚,那是彻骨的冷!没有飞奔而来的拥抱,甚至都看不见Cloudy的影子,只有一个贴着Cloudy名字的箱子立在那儿。冰冷的不锈钢专用箱,箱体上布满点状的透气孔。Cloudy已经装入箱中等待上机了。我最后的一丝渴求和希望也破灭了。
这时,我忽然感觉到了箱子里躁动不安的气息,一阵阵爪子触碰钢铁的声音,一声声悲伤的嗥叫,Cloudy一定知道是我来了,它应该可以看到我!
隔着布满透气孔的铁箱,Cloudy不停地冲撞着铁箱,发出啪啪的声音,而我,根本没法看清它……这种告别方式让我肝肠寸断。
飞机在跑道上加速,飞上天空,我泪眼模糊,抬起无力的手轻轻挥动:再见,Cloudy!再见,我亲爱的孩子!
2014年10月。
紧张的后期制作基本完成了,难得有了段休息的时间,我尽量地放松自己,看看书,听听音乐,睡到自然醒,去和朋友聚会。可是,我很清晰地感觉到,在内心深处的某个地方,总有一丝牵挂和放不下的感觉。它就在那儿,你不想它,它在那里;你想它,它就会更强烈地凸现出来,让人时时刻刻不能释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