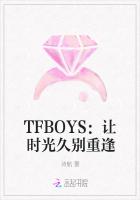萨拉想把加里的手推开,但发现这像掰墙上的砖一样,根本就掰不动。她用手指使劲儿扒拉他的手,不经意间与他眼光相对,令萨拉感到恐怖的是,加里居然在微笑。然后,他放开了她。
这事快失控了,萨拉想。我要快点离开这里。但她不能失态,要保住一些尊严。“很好,”萨拉的声音有些颤抖。“如果你坚持出庭作证,那是你的权利。法庭上见。”
来到走廊上,她看到露西也浑身发抖。这两个女人倚靠在相对的两堵墙上,凝视着对方。“今天很不走运,对吧?”露西说。
“是啊。”萨拉把颤抖的双手按在背后的墙上。“天呐,我在这里干什么?”
露西手忙脚乱地在包里找烟。“这不是你的错。你已经告诉这个混蛋该怎么做了。现在命运掌握在他自己的手里。”
“是啊。像他那种暴脾气,他也许会直接被带走。”
她们从加里的暴怒中缓过神来后,突然觉得这句话无比好笑,简直把她们给笑疯了。一个看守经过楼梯时好奇地朝她们这边张望。萨拉和露西来到法院大门时还不停地咯咯笑着,就在这时,她们居然撞见雪伦·吉尔伯特。
我的上帝啊,萨拉心想。今天这是撞邪了吗?
我不会那么卖力的,萨拉想。那样毫无意义。即使他并没有真正承认,这个杂种也是有罪的,活该蹲监狱。再说了,我累死了。
萨拉站了起来。“大人,我要传加里·哈克作证。”
加里在复述誓言时稍微有些磕巴,但声音有力、响亮。
“哈克先生,你已经听到了控方针对你提出的所有证据。你是否强奸了雪伦·吉尔伯特?”
“我没有强奸她。”
“你是否在去年10月14日,也就是周六晚上,去了她家?”
“我没去她家。”
“很好。咱们一起回顾一下那天夜里发生了什么事吧。那天傍晚你是否在驿栈酒店的派对上见到了吉尔伯特女士?”
“是。”
“请问你为什么去那个派对?”
“我为什么不能去?我有几个朋友在那儿。”
“你是有意去见吉尔伯特女士吗?”
“不。我已经有……6个月没见过她了,大概6个月吧。”
“那你当时看到她是什么感觉?”
“哦,没什么特别的。我是说,我给她买了饮料,邀请她跳舞之类。也就这些,真的。”令萨拉吃惊的是,加里看上去很平静,说话时的态度几乎让人觉着他是个值得尊重的人。陪审团认真地听着,脸上还没露出厌恶的表情。
“她见到你时高兴吗?”
“不太高兴。她有时就像只母老虎。”
加里又开始撒泼了,萨拉心想。你要是想往火坑里跳,随你便。我才不管呢。
“你们是否有出现争执?”
“我让她把表还给我,她说没拿我的表。”
“然后你是什么反应?”
“我说她是,呃……”加里停了一下,朝陪审团瞥了一眼,似乎在努力克制住自己。“我说那不是真的。我估摸着她把表卖了,所以她该还我钱。”
“在争吵的时候,你提高嗓音没有?”
“提高了一点。声音小了听不见。”
“好吧。在争吵的过程中,你是否有威胁她,说可能去她家里把手表拿走之类的话了吗?”
“我没说。”
“那你去她家拿那块手表了吗?”
“没有。”
“那么,你最后见到那块表是什么时候?”
“去年她把我扫地出门的时候。”
这个杂种确实在努力,萨拉心想。到目前为止表现尚好,当然这是对他而言。可是,现在愚蠢的谎言要登场了。加里开始要说那个虚假的不在场证明了。
“那请你自己告诉陪审团,那晚你离开驿栈酒店后发生了什么。”
“好吧,我碰到了我老兄肖恩,我们一起去了酒吧,在那儿猎艳。”
“猎艳?”
“对啊。找小妞。找姑娘。”
“找到了吗?”
“找到两个。”
“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哦,她们是婊子,就是妓女,所以我们就搞了她们。”
“你们付钱了吗?”
“我付了我那份儿。10镑。真他妈贵。”
“然后呢?”
“我回家睡觉了。”
“肖恩跟你一块儿吗?”
“没有。我们碰到小妞后就分开了。我再也没见到他。”
“那个女孩儿呢?她跟着你回家了吗?”
“没有。”
“她叫什么名字?”
“想不起来了,对不起。”
“你在那之前和之后都没见过她?”
“对,再没见过。反正是不能再找她了,太贵了,玩不起。”
“那么,你也听到基思·萨默斯说他那天夜里1点,在阿尔伯特街看到过你。你当时是在阿尔伯特街吗?”
“是啊。也许吧。我可能是在那儿。”
“是你从遇见女孩儿们的地方回家的路上吗?”
“是的,那是回家必经之地。”
“基思·萨默斯说你朝他挥了挥手。是真的吗?”
“有可能。想不起来了。”
“很好。阿尔伯特街与雪伦·吉尔伯特家所在的索普街平行。所以,我再问你一遍,那天夜里你是否去过雪伦·吉尔伯特家?”
“没去过。”
“你强奸她没有?”
“没有。”
“那么你是说,你完全是清白的,根本没犯下你被起诉的罪行?”
“清白?对,没错。我是清白的。”
“很好。请待在原位。”
听到萨拉要传加里·哈克出庭作证,朱利安·劳埃德·戴维斯脸上就一直挂着微笑。现在,他站起来,有些厌倦地叹了口气,手里拿着几张笔记。他全神贯注地看了几秒钟,然后厌恶地扔到一边。
“哈克先生,这些都是你编造的,对吧?”
“什么?不是啊。”
“你并没有叫肖恩的朋友,是不是?”
“我当然有啊。他又没死。”
“那他家在哪里?”
“我不知道。他离开约克了。一定是离开了。”
“你完全是在浪费警察的时间,对吗?”
“我他妈的真没有。是他们是在浪费我的时间!”
不出所料,萨拉想。给劳埃德·戴维斯加1分。不,如果算上他把笔记扔掉的那种姿态,得给他加2分,陪审团太喜欢那种表现了。
“啊,我明白了。你觉得警察调查残忍的强奸案是在浪费时间,是吗?”
“我从来没那么说。”
“噢?原谅我,我以为你是这么说的。”劳埃德·戴维斯不屑地从镜片上方盯着加里,语气中故意装出一副居高临下、饱读诗书的傲慢,萨拉心想:真是不出所料。他已经刺到加里的痛处了。等着加里爆发吧。
她没料到的是,加里居然没有爆发。他那双残酷的大手紧抓住证人席的边缘,面孔涨红,一句话也没说。
劳埃德·戴维斯又发问了。“你记性不是一般的差吧,哈克先生?”
“不。我不觉得。”
“那好,告诉我。你朋友肖恩姓什么?”
“我不太清楚。我一直叫他肖恩。”
“或许,你记得他在哪儿工作?”
“他跟我在一起在阿库姆街的麦克法兰公司工作。”
“阿库姆街的麦克法兰公司。”劳埃德·戴维斯意味深长地叹了口气。“你看,你又在撒谎,哈克先生。警方已经查证过了。当时在麦克法兰公司工作的人中没有叫肖恩的。”
这次加里开始大声反击。“我他妈的没撒谎。当时他在,他和我在一起干活儿。格雷厄姆·杜瓦已经说了!”
“你把陪审团完全当成傻瓜了吧,哈克先生?他们能相信你有个根本就不存在的朋友?”
“我他妈的不是傻瓜!你才是!”
现在的情形正如萨拉预想的那样发展着。劳埃德·戴维斯光滑而突出的唇间浮动着满意的微笑。他刻意选择了下个问题的用词,此举令他很受用。
“那么,你就告诉陪审团。你经常,用你的话说,你经常‘搞’女孩儿却不知道她们叫什么名字吗?”
“有的时候是这样,对你来说可能不是。”
法庭内一片暗笑声,萨拉吃惊地看到两名年轻的男性陪审员居然咧着嘴大笑。劳埃德·戴维斯感到自己在这场交锋中没占上风,于是他的语调中开始流露出恼怒。
“这个故事编的不怎么样啊,因为你提到那天夜里跟你在一起的人实际上并不存在,对不对?全都是你编造的谎言,难道不是吗?”
“不,我他妈没说谎。”
“噢,不,你是在说谎,哈克先生。事实是,当天晚上你见到吉尔伯特女士时你很生气,你想报复她。所以,你离开酒店后就在索普街上等着,直到她回了家,然后戴着头套闯进她家,当着她孩子的面野蛮地强奸了她。这才是事实真相,对不对?”
“不对。”
“事实就是如此,哈克先生。我们都知道这是事实,因为她认出了你。”
“不,她没有!妈的,她不可能认出我,因为……”
加里犹豫了片刻,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前方,显然没看任何东西。萨拉心想:时候到了。这个蠢货真要承认了。倒也是件好事——就算对我不是件好事,至少也能伸张正义。
“呃,哈克先生?她为什么没法儿认出你?”劳埃德·戴维斯洋洋自得地刺激他。他的声音让发呆的加里猛醒过来。
“因为我他妈的不在那儿,这就是原因!因为强奸她的那个家伙不是我!如果警察不是在这儿浪费时间,纠缠这些破事儿,他们早就在想办法抓住真凶了,不是吗?”
两人就这样又你来我往了几分钟,还是毫无结果。劳埃德·戴维斯尖刻地讽刺加里,加里则针锋相对,反唇相讥。当加里终于坐下后,萨拉心想,他既没有完胜,也未酿成灾难。
然而,露西比她兴奋多了。她身上那件特别宽大的蓝色罩衫一点都不适合她,让露西看上去活像一个农妇。结案陈词之前,法官准许休庭15分钟,露西利用这个间隙挑衅朱利安·劳埃德·戴维斯。
“冒昧问一下,你打板球吗,劳埃德·戴维斯先生?”她问道。
“呃,打呀。”劳埃德·戴维斯微笑着回答,这是他在整个庭审期间第一次正视露西的存在。“应该说,周末大多花在这上面。”
“我从你的盘问风格就看出来了。我觉得就像英格兰队被索维托的‘后备队’[2]逼成和局。”
“露西,不带这么损人的。”看着昂首离去的劳埃德·戴维斯,萨拉说。“你总是这样耍弄对方的大律师吗?”
“只有在他们把我惹恼的时候,就像他那样。”
“你怎么知道他打板球?凭灵感猜出来的?”
“哦,不是。他在《名人录》里吹的。他说自己曾经代表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出战。是个佩戴蓝色标志的人物[3]。”
萨拉露出一丝淡淡的微笑,那微笑像冬日的阳光一样明媚,又迅即消失了。
“我猜加里从来没玩过板球。除非他要用球板来杀人。”
[1]证据的统一性:证明某个被指控犯有某项罪行的人正是该罪犯或某项被提交到法庭之物正是该存在争议之物或诉讼所涉之物,或认定两种笔迹同一,以及查明诉讼中涉及的某人的身份等的过程。
[2]后备队:板球运动中,每队由11名球员组成,未入选主队的选手组成“后备队”。这里用来羞辱这位大律师。
[3]佩戴蓝色标志的人物:代表牛津(或剑桥)大学校队参加两校间比赛的运动员,享有佩戴蓝色标志的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