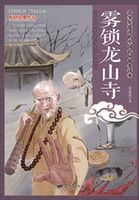10:00-11:00
她对镜子做了一个微笑,嘴才闭上一会儿就不得不张开了。畅快地呼吸了几口气后她把注意力转移到了两条腿上,把自己从椅子上撑了起来。她在房间里慢慢走着。行走的路线因为其实有限的家具:床、电视机柜、两张电脑桌、藤摇椅、餐桌、一只大行李箱而变得蜿蜒。在两扇落地窗前她转身,前一天的晚饭原封不动地摆在她身旁的餐桌上,早已在四个大大小小的微波炉圆盒里变凉。她认为自己看起来平静,每一步都稳当,不过她整个人都顺着脑袋向左边歪斜,像在练习某种神秘的功夫,让人以为她想这样一路斜着上墙。经过好一番细长的行走,她在门边停下了,从门上拿下钥匙,过了一会儿她想起来,自己正在屋里。
她把窗帘拉上,窗外是晴朗的四月(27度),她把身上的睡衣脱了,在床上坐下,把头顶在膝盖上。这时电话响了,她看了一眼,来电显示是她最要好的女友。铃声很响亮,但她并不在意。我一个人,留在这个阴暗的房间里,孤单地,我不需要别人打扰,这样,我的睡眠就会开始了。她拿过床头柜上的闹钟,离她出门,还剩下四个小时。唉,她忍不住又想下床照镜子,脸色不会红润,眼睛有点儿肿,也许眼白上还有血丝,真糟糕。
她感到脑袋右边的疼痛边缘在钝化,这艘船,终于驶进了平静的水域,不再上下起伏,但她还是晕船了。很快就会上吐下泻。于是她又穿上了睡衣。睡衣散发出橄榄油味。F说过她现在的皮肤比他刚和她一起时还好,更滑了,橄榄油确实不错。
厕所在走廊里,她走过去,她的身体仍然向左倾斜着,我是多么轻盈,就像一根缀了几片叶子的枝条,被风吹动了。她不喜欢在夜晚进入这间厕所,老洋房里才会有的鼻涕虫像是这里真正的主人,在白色的瓷砖上匍匐。它们不是唯一的,还有黑黄相间的蜈蚣。她向Y提起它们时,他对她没被蜈蚣咬过表示了小小的惊奇,我很好奇,她说,于是Y开始说了。很小的时候,也许五岁?六岁?记不得了。夏天的夜晚,有风,而晚霞就在半小时前还那么灿烂,火烧云遮盖了整个西边,到现在依然记得。我的父亲早已摆好他的工夫茶具——只等待炭火把水烧开。还有潮剧。在那个年代,我家里就有了一台三洋牌录放机。它总是在我没有选择的前提下播放着只有父母才喜欢的那些剧情。我,短裤子?应该是的,夏天嘛。没有谁能在那个几乎可以称作热带的地区穿着长裤不被人讥笑的。它一定是在那里的了。它就那么咬了我一下,这我很确定,因为它咬我的那刻我正看着它。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更没认为它的毒素可以让我整个晚上无法入眠。我用手指拨弄了它一下,就在那一刻我彻底地感受到了它的出击。啊,真可怕。这样,Y与蜈蚣的故事就讲完了。但在这个立体直角梯形的厕所里(这对它们来说真是巨大的古堡),上楼的脚步声在另半边的顶上轰响,它们一伸一缩地前进,在古堡内消耗着自己的生命。一次她起身后发现一条鼻涕虫已经从侧面爬到了马桶座圈上,震动立刻从她的小腿窜上,穿过她的两根锁骨,击向她的脑袋,很快原路返回。
她扶着水箱干呕了四五次,在那上方横贴了一张A4纸,上面打印了两行字:请勿将废纸扔进马筒(对这个错别字她总想拿支红笔圈出来)里,以免引起堵塞。她的头颈与肩膀一起抖动,没有人听见我,就算现在F在屋里也不会听见,他镜片后的眼睛看着电脑屏幕。她曾经抱怨过他。她对自己什么都没能呕出来略感失望。她打开门,在走廊的水斗前站着她躬着身子的新邻居,在网吧工作的不知姓名的女孩,右手拿着牙刷,左手腕上搭着一条粉红格子毛巾。她经过她的背后,走回自己的房间。很快她又有了便意。我的体重正在做减法,时间就是以这种减法方式向前移动的:现在是上午十一点。她坐在马桶座上撑开木板窗,为她烧饭的绍兴阿姨在窗前走过,一秒钟后她听见钥匙哒哒转动门锁,整幢洋房的这扇底楼大门不好开,得用钥匙捅上好几次。
把门推开,她从厕所里走了出来。阿姨眼中的她与往常一样,穿着睡衣,头发纠结。她努力平稳地移动双腿,它们发麻了。尽管她心情不好,她还是微笑着打了招呼。我想再睡一会儿,她用她飞快的语速说,你今天不用进来收拾屋子,也不用烧菜了。好,你真(客气?爱睡懒觉?)阿姨的下半句话还没有整队出发她就关上了门(刺耳的响声)。小姐那我走了,阿姨大声地说(小姐这个称呼很不恰当)。
如果允许她进屋,她一定会把盖子一一打开:酱烧鸡翅已经凝胶成了一个大圆饼,这么好的香肠炖蛋,把已经发黄了的蒜苗放在鼻子底下嗅嗅,再用一根手指撬开微波小饭锅上的塑料盖,哎呀你们怎么什么都没吃,她的语气会不太高兴。是的,我尝过,味道真不错,可我们昨晚有饭局……哦,阿姨会心不在焉地看她一眼,同时迅速地将它们并进一个大碗,算了小姐我中午就吃它们吧。
她用手抹了抹脸,把自己的两条腿蜷缩到胸前,我的全身都被痛苦笼罩了,但我其实没有资格痛苦,一个人不能为她愿意的事感到痛苦。但现在,她身体上的每一寸地方都挤满了痛苦,请让我进去,理智冷静地提出,但痛苦以它们各自的方式阻止了它。它没法回到她身体里了。在它离开后,她开始感觉到了身上痛苦的重量,它们压迫着她,她向下滑去,地板毫无铺垫地接住了她。红褐色的地板,去年夏天F从后面抱住她,他热热的呼吸吹着她的后脖颈,“中南海”的烟气不时从她侧面飘开。那时她还刚和他搬到一起住。夜晚她在嘴里嚼着口香糖和他一起散步。离他们住处不远有一片拆迁到一半的废墟,一些房子的轮廓还在,到了中段能看见灯光,一次一个穿睡衣的女人在阴暗的墙角无声地闪过,她抓住他的手。最后他们回到这间房间,把灯打开,她喊。他们以每天做爱的方式庆祝她恢复自由。
室外的明亮与室内的寂静。能使寂静变得更强大的是黑暗。她躺在地板上,白色的天花板明亮地打断她,这时我并不真的痛苦,她的眼前出现了Y的脸,一张小脸,脱离了粗壮的脖子飞到了天花板上,像石膏像一样泛着冷光。凸出的眼睛和向后退的前额。一张扁薄的小嘴。她坐起来,那张脸无声地掉下来,和手机一起被她握在了手中。
几个星期前Y来看过她一次,他看到的她是另一副样子。那时她去机场等他,站在机场大巴的指示牌下。他当时看见了她的墨镜、出了油的前额,普通的雪纺连衣裙外面披着一件深褐色牛仔短外套,他在几千公里外记住的是她的杏仁眼。她用飞快的速度说话,他歪着头盯着她的嘴(像一个好奇而疑惑的孩子),这非常容易地使她低下了头。直到他们并排坐下(她就贴在他身边,他可以清楚看到她没有化妆的眼睛下部紫色的血管),陌生感才被经由血液传送的冲动冲淡。
他说他迷恋我的身体,我的皮肤那么光滑,我的小腹紧绷绷的,我可以支撑他奔跑很久,如入无人之境,他怎么创造出这样一个词语,她一边寻找他的号码一边想,我这就告诉他,我去看他。
11:00-13:00
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她就对有限度的疼痛着迷,它们奇怪地让她兴奋也让她麻木。事后她认识到停不下来的危险,她在身体里另外装了一个自己,后者会在这样的时刻紧紧盯着前者的疼痛,介入、穿透并终止。不过这另一个总是在匀速地旋转,有时转到了另一面,完全没有任何警觉,鲜血于是渗出,于是那个走神的家伙把鼻子用力向上皱起,然后迅速转过头来。她开始寻找“创可贴”。
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创造的疼痛越来越少,穿着高帮大头鞋的脑血管痉挛频繁前来,它踩踏她的大脑,从左半区走到右半区,把她五颜六色的小念头碾碎,她只好把书和碟,还有写作扔到一旁,她不得不这么做,它紧跟着她。
她平静地把手机放在一旁,喝下刚热过的木瓜牛奶,又倒了半杯温水,然后脱下睡衣(这件红色的睡衣是F前女友给他的礼物,她穿着太长了),把脚从红色的卡通狗头拖鞋里拔出,在床上躺下。自从她在飞机上服用过“去痛片”后,每次她都把它白色扁平的小身体一个接一个塞进大头鞋的缝隙当中。它们慢慢多起来,融化出的白色粉末覆盖了鞋子要经过的所有地方,它有强劲的腐蚀性,鞋子和那上面庞大的身躯变小了,不再来回踏步,渐渐地,一片白色。
有一次,她塞进太多白色了,它们失去了界线的概念,大脑挡不住它们了,它们有力地一片洁白地向她的心脏蔓延,一个符号,一个向左优美抬起屁股的箭头隐隐出现,它神秘地显示了她的想法:撤消键入。她没有想到死这个字,她只想用手在胸膛上抓个洞。她呕吐,她想,我得睡一会儿。她从周五傍晚睡到周日下午。
她把被子往上提了提,没有F温暖的身体,她感到冷,早晨她就因为冷而睁开了眼。此外嘴很干。在酒吧里她对F说完她的经历后,嘴同样因为干而微微张开了,啊我的,他叹气,这样就开始了持续一个多月偷偷摸摸精密计算的见面。他们常去的室内是浅绿的茶餐厅,她身上的红色裙子在绿色长时间的浸泡下变得模糊,就像长了一层绿毛。偶尔他们去免费开放的公园,光秃秃的草地围着迷你人工湖,那一小圈水见证了它们的哀伤,它们总在抱怨,头发还没长长,就被剃成寸头。他们轻声细语。他们手牵着手。在她的丈夫Z茫然地望着她之前,她在家里看上去还是老样子。但她把她细小的鸟一样的乳房交给了F。还有吻,但她回忆不起来,它们都有些什么味儿。
也许我该出去走走,公园里有树,有盖了草皮的小土坡,她开始洗脸,瓶瓶罐罐一个接一个响,不同气味的护肤品通过她的手指跑到整张脸上,她整理背包,钥匙咣啷落到最底下,牛皮钱包厌恶地看着轻浮的润唇膏滚来滚去。最后她穿上漂亮衣服出门,脸上涂满油腻腻的防晒霜(否则黑色素会一小格一小格地填进毛孔),被墨镜遮掉一小半。可我能看见什么呢?天气热,人们在树荫下坐着,谁也不会抬头看看天,天也还是老样子,一大盆食堂里的蛋花汤,找来找去就那么几朵云。她把被子裹得更紧了。
我想出去,可我哪儿也去不了,Y这会儿应该坐在饭桌边上,他的妻子坐在他对面,小家庭那种程式但还温馨的场景,她对他轻松地说着话,他抬起头看她,他不会把眼睛骨碌碌转起来,他总是目不转睛,听完一段后低下头,继续拨弄那些碗里的菜,他在我面前也这样,而我,我在这里,在被子里,强忍着不哭出来。她的眼睛里渗出了泪水,她睁大眼睛,这样她向上看了,天花板的白色没有变化。
两个月前,她被邀请到雷州半岛采访,就在那里,她与Y上了床。他刚进入她就泄了,她没有对他提出不满,她犹豫地推测,他疲倦过度(有这样的迹象),她继续挑逗他,她的努力失败了,求你让我睡觉吧,他说,我没法动脑了我在胡说八道。她忍受了那一晚,她失眠了,因为她年轻,身体充满活力,一旦点燃难以熄灭。第二晚他们又在一起,她还想试,还想与他再做一次。勉强及格。
他们依依不舍地分开了,他继续和他的妻子生活在一起(六年恋爱加七年婚姻),她背着行李回到家,F带她去了离家不远的餐馆,饭后他们像以往一样并排在人行道上散步,散步时他揽着她的肩膀,她微笑着告诉他,她喜欢Y。他把眼睛低下,好像在回忆,然后用比Y尖一些的声音告诉她,他曾经在类似的活动中见过他。她等了几秒钟,等他继续问下去。他像父亲一样把右手掌搁到她的脑袋上。一段无声的行走后他们走进了房间。很快F进了浴室,水流哗哗响起。那天晚上他们做了爱,他冲撞她就像用力推动秋千,荡到最高点时她将F换下了。你就是想以这样的方式证明你的魅力。几天后F说。她没有为自己辩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