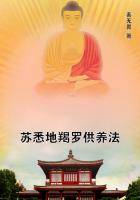执行完任务之后,雾言没有直接回别墅,但终归还是要回去的,总不能莫名其妙的让别人发现自己从家里消失了。她在某个房间里稍作休息,把衣服从身上脱下来换上一身干净的衣服,对着外面五彩斑斓的灯光微微走神。
或许是发呆的时间过长,她似乎做了一个不甚舒服也不甚明确的梦。如果实体化,应该是这样吧,自己走进一个小房间里。会觉得它是小房间,是因为她只看的到前方的三面墙壁,没有窗口,没有灯,却有光。
她看的见,清清楚楚,白色的墙上没有逻辑似的漆满赭红色,在梦中的她伸手去触碰,墙面轻轻一刮就有小碎块剥落。在那个梦里,鼻子除了嗅觉被剥夺外,鼻腔在一次吸气后则一直充满了冰冷的空气。不是熟习的那种隐隐带有霉味的湿冷,而是纯粹的乾燥,像是沙漠突然陡降到零下的错觉,虽然这只仅是她所感受到的冷。什麼声音都没有,却算不上安静,因为她清晰的听见自己体内有水在流动。
严格来说,是流得挺不安稳,十分躁进的激流,从体内的深处像是要冲破皮肤一般,而低头看去却没有半点动静。她伸手去捂住胸口是,看到胸口的位置传来疼痛,于是她低头,看到枯骨般的手从她的胸膛里穿了出来,她却一滴血都没有流,只是感觉到疼痛。
面对这样诡谲的梦境,该是要用力颤抖或者不安的向后退甚至转身逃走,想办法让自己醒过来。于是她猛然睁开了自己的眼睛,冷汗从她的额头上流了下来,那种刺痛的感觉依稀还在,并且感觉如此鲜明。
像是自己已经死亡,身体其实已经腐烂,并且无可躲避。
小时候她其实是一个极为胆小的孩子,很恐惧做噩梦的,小孩子都会害怕做噩梦,只是她比一般人更耐得住恐惧。每当做噩梦的时候,只会死死的咬着自己的嘴唇不让自己发出一点儿声音。从小她就不是一个会撒娇的孩子,不让人喜欢,因为没有孩子还有的活泼灵动。
墙壁上是一成不变的赭红色盖满整个视线,看久了甚至觉得那是会动的,像是有人从她视线死角泼洒新的颜料上去。不知道那是谁选择的颜料,竟然会选择这么刺眼的颜色。
然后她又感觉自己出现了幻觉,鲜红色,与旧的颜色叠在一起,快速的被甩在墙面后又快速的向下滑落,形成一种纷乱的现象。彷佛是垂老的女人用口红涂抹在皱褶的嘴唇上,充满违和。
雾言并没有什麼被惊吓的印象,很自然地转醒,只是还牢牢记得,赭红色乱无章法的泼溅了整个空间的画面。也许是前几日不经意地留意了鬼片的广告,大量的鲜红色,而无意识的带入梦境了吧。
她是这样理解的,关於这个梦。
其实她早就应该注意到自己的异常,只是一直自欺欺人的始终不说也不承认。
又或许是因为自己太过清楚,即使说出来也没有什么用,承认了也没有用。
那种疼痛是无法缓解的。
不是狗血韩剧里的心脏病。
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