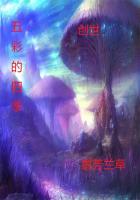英语老师清一色的外籍,教我们的是个英国老太太。让我回答了一个
问题后就批评我的发音,说我是典型的中国式发音,让我面红耳赤,
在一帮初次见面的同班同学面前下不来台。
那时候我很脆弱,失去父母,失去家,失去我所有的幸福。寄
住在舅舅家里,小心翼翼,把破碎的自己一点点藏起来。学着看舅妈
的脸色行事,讨好表妹,替她讲奥赛题帮她补习。十六岁以前我也是
父母的掌上明珠,唯一的公主,老师最骄傲的得意门生,亲友称羡的
好孩子。可是一切都没有了,我所倚仗的一切都没有了,成绩再好有
什么用,爸爸妈妈永远都看不到了。
放学后我一个人躲在操场里哭,有人在塑胶跑道上跑步,脚步
沙沙的,从我身后过去。我背对着跑道坐在草地上,把头深深的埋在
双膝里,看着眼泪一滴一滴落在草丛中。我想起很多事,大部分是小
时候,爸爸妈妈带着我去公园,划船、坐碰碰车、买汽球。小时候有
一种棉花糖,是用白糖做的,很大一团,篷松松软绵绵就像是云,我
吃的时候总会糊在脸上。爸爸就爱拍我出糗的照片,那时候全是胶卷
,一年下来,爸爸能替我拍好多卷胶卷的相片。
我哭的很伤心,连有个男生走过来都不知道,直到我看到他的
球鞋,雪白的鞋底上沾着一片叶子,他蹲下来用右手去拨掉那片叶子
,左手却递给我一包纸巾。
我愣了好几秒钟,都没去接那包纸巾,他把纸巾随手搁在草地
上,然后就走了。
第二天我才发现这个男生就坐在我后面一排,他叫萧山。
萧山的父亲是外交官,他十二岁前都在国外,说一口流利标准
的牛津腔,可以跟英国老太太在课堂上辩论词组的用法。数学更好,
好到我这种人都望而兴叹。他偏不是勤奋的那种学生,好成绩纯粹是
天才。下课十分钟都能见缝插针跑到操场上打篮球。有次上数学课,
刚打铃,他气吁吁抱着球跑回来迟了,站在门口喊“报告”。教数学
的老奔最讨厌学生迟到,扭头看了他一眼就恍若未闻,他只好站在门
口当门神。没过一会儿老奔开始发上次全市联考的试卷,老奔的习惯
是每次按全班的分数念名字,由高到低,念到一个分数名字,学生自
己上去拿。既不人道又伤学生自尊,可老奔不管,他就爱以分取人。
结果这天念的第一张卷子就是萧山,150的满分,老奔扭头看
了门外的萧山一眼,不情不愿的没好气:“还不进来?”
全班同学都埋头忍笑,萧山从老奔手里接过试卷,倒大大方方
:“谢谢老师。”
附中里优秀的学生很多,但像他这么优秀的也屈指可数。班上
有许多女生暗恋萧山,豆寇年华情窦初开,谁对这样出色的男孩子没
点幻想。我没有是因为完全没那心思,父母的离去让我完全没有了对
这个世界的应对能力。虽然他就坐在我后面一排,但我除了偶尔跟他
借下英语课笔记,基本没有和他说过话。
真正跟萧山熟起来是在寒假,英国老太太给我们布置的寒假作
业就是分组排一幕莎士比亚的剧。全班按座次被分成若干个小组,有
的小组选了《罗密欧与朱丽叶》,有的小组选了《仲夏夜之梦》,有
的小组选了《哈姆雷特》……我和萧山被分在一组,我们这组选了《
威尼斯商人》。等春节过了,每个小组都要在班上公演,然后分别评
分。
我很喜欢寒假排戏的那段日子,因为可以不用呆在舅舅家里,
越临近春节我越有种无家可归的凄惶。舅妈总念叨过年要置办的东西
,表妹吵着要买台新的笔记本电脑。几年前笔记本还没像现在一样滥
大街,表妹已经有台联想笔记本了,但说是班上有同学用索尼新款,
舅舅于是许诺她考到全班前二十名就买给她。
表妹就拉着舅舅撒娇:“爸,你看表姐都说了。”
我只觉得心酸,去年春节的时候,我还拉着爸爸妈妈的手撒娇
,可是现在不管我想要什么,都没有人买给我了。
那时候我对周遭的一切非常敏感,又非常脆弱,所以宁可躲出
去,省得心里难过。
排练一般在萧山家里,萧山家里很宽敞,又没有大人在家,只
有他姥爷姥姥。我到现在还记得两位老人家和蔼的样子。我们关在暖
气充足的书房里,旁若无人的大声念对白,姥姥在厨房里给我们做了
点心,拿盘子端出来。
有时候是糯米藕,有时候是桂花年糕,有时候是水晶烧卖……
统统都非常好吃。萧山的姥姥是南方人,做的点心都是家乡风味,姥
姥又总是最关照我这个唯一的女生,让我常常吃到很撑。
那时候我还不适应北方的冬天,干燥得让我常常流鼻血。有天
在萧山家里对台词,背着背着就有同学叫:“哎呀童雪,你流鼻血了
。”
我一低头鲜红的血点就滴在襟前的毛衣上,毛衣是白的,滴上
去看着格外触目惊心,我晕血,一下子整个人都软在了那里。最后还
是萧山架着我去洗手间,胡乱把我头发捋起来,拼命用凉水拍我的后
颈窝。姥姥在一旁帮忙,用毛巾擦着我脖子里淌下来的水,一边擦一
边说:“唉哟,这孩子,看着真受罪。”
萧山微凉的掌心,拍着冷水在我的脖子里,他啪啦啪啦拍着,
血仍不停的往下滴,滴到面盆里。水龙头开得很大,哗哗的声音,听
得我更觉得眩晕,只看见一缕缕血丝很快被水冲走了。隔一会儿他总
要问我:“怎么样?怎么还在流啊?”
姥姥嗔怪他沉不住气,然后又掐我手上的穴位,姥姥掐了一会
儿,就让他掐:“你劲大,用点力气掐住了,就不流了。”
他的手劲果然大,狠狠一掐,掐得我眼泪都涌出来了。看着我
哭他又连忙撒了手,姥姥又怪他:“你怎么这么蛮啊,女孩子的手,
嫩着呢。”
我于是一边流鼻血一边流眼泪一边还要劝姥姥:“您别怪他,
他也是想快点把我掐住了。”
他竟然在一边笑出声来:“掐住了……这说法怎么这么怪啊?
”
姥姥在一旁拍他:“臭小子,还笑!”
那天我都忘了我的鼻血到底是怎么止住的,只记得后来我鼻子
里塞着药棉,然后吃姥姥做的枣泥锅饼。姥姥一边劝我吃,一边说:
“枣泥是补血的,多吃一点儿。”
我对排练的那段日子念念不忘,一多半是因为姥姥对我好,她
对我真是太好了。
快到春节时我们已经把台词倒背如流,有一天排完之后时间还
早,不知是谁提议去遛冰。我是南方人,根本就不会遛。但排练到如
今,可以说我们小组几个人已经是铁板一块,那友情比铁还硬,比钢
还强。几个同学死活都拉我一块儿去,萧山也说:“有我们在,摔不
着你。”
穿上冰刀后我连腿都不知道怎么迈了,两位同学一人牵着我的
一只手,我小心翼翼迈着步子往前蹭,他们稍微快一点我就吓得大呼
小叫。最后有位同学不耐烦了,转过头去叫萧山:“你来带她吧。”
又对我说:“萧山退着滑最棒。”
萧山教的非常耐心,他一边退着滑一边跟我讲解动作要领,就
像他平常讲数学题那样。寒假小组熟悉起来之后,我偶尔问他题目,
他总能讲得头头是道,思路清晰,而且一定是最简单的解法。滑了几
圈后我自己慢慢悟了一些,他看我遛的不错,就渐渐松开了手:“你
学这个还有点天份。”
我不好意思被他夸:“不是,原来玩过轮滑鞋,所以知道一点
平衡。”
我第一双轮滑鞋还是爸爸去美国出差买回来给我的,我还记得
那双鞋是粉红色的,爸爸总喜欢给我买粉红色的东西,因为在他心里
,女孩子就应该是粉嫩嫩的。那鞋买的稍大,我一直穿了几年。后来
国内也有类似的轮滑鞋卖了,可是样式要简陋得多。学着玩轮滑也是
爸爸教的我,拉着我的手,就在家门口的篮球场里,遛了好几个星期
天我才学会。
我狠狠的摔了一跤,萧山一把把我拽起来,没好气的说:“想
什么呢?还没学会呢就一心二用,你怎么总这样啊?”
我没有作声,有时候我问他英语阅读理解,讲半天我还在发愣
,他就这样不耐烦,觉得我笨,又不用心。从小没人说我笨,过去老
师也总夸我接受能力强,可是在他面前我就是笨,因为他太聪明。
他怕我再摔着,一直没再撒手,拉着我的手带我慢慢滑。那天
有一点点风,吹在脸上并不冷,我没有戴帽子,头上就用了条围巾随
便绕了一下。我长这么大,从没跟男孩子手牵着手这么久,虽然都戴
着手套。但上次我和男孩子手牵着手,好像还是小学的时候,“六一
”儿童节表演节目。想到这个我的心突然跳起来,跳得很快,微微让
人觉得难受。萧山却根本就是坦荡荡,他紧紧拉着我的手,就像拉着
个妹妹,或者拉着位同学——我本来就只是他同学而己,我不再扭头
看他,只是努力让自己显得更自然。
滑完冰后我们去小店喝珍珠奶茶,热乎乎的珍珠奶茶捧在手心
里,显得格外醇香。大家七嘴八舌说过年去哪儿玩,还有人提议逛庙
会。我一个人不作声,只是喝奶茶,正吸着珍珠呢,忽然听到萧山说
:“呀,你脸冻了!”
我摸了摸脸,有个硬硬的肿块,痒痒的,我从来没生过冻疮,
没想到第一次生冻疮就在脸上。听人说生冻疮会破皮化脓,如果长在
脸上,那岂不得破相了?我连奶茶都不喝了,使劲按着那个硬肿块,
想把它给按没了。萧山说:“别揉,越揉越糟,我家有亲戚给的蛇油
,明天拿点给你吧,用蛇油抹两次就好了。”
第二天就是除夕,早就说好了这天到正月初五都暂停排练,毕
竟要过年了。我原本以为他说说就算了,谁会在除夕从家里跑出来啊
。谁知道刚起床不久,就听到电话铃声。表妹还没起来了,舅妈怕吵
醒了她,连忙把电话接了。听了一句就叫我:“找你的。”
我怕舅妈不高兴,很少把家里电话告诉人。所以不知道是谁会
在除夕的早晨打电话给我,忐忑却听到萧山的声音,他说:“你的电
话可真难找啊,问了老班才知道。”
舅妈就在旁边的沙发上,有意无意的看着我,因为从来没有男
同学打电话到家里来,我怕她误会什么,连忙问:“今天不是不排练
吗?”
“你忘了?昨天说给蛇油给你,你出来拿吧。”
我还有点反应不过来:“啊……”
他说:“我就在军博地铁站门口等你。”
那是离舅舅家最近的一个地铁站,走过去只要十分钟,我飞快
的拿了主意:“好,那麻烦你等等我,我马上就来。
搁下电话我告诉舅妈,排练的稿子有改动,所以同学打电话通
知我,我得去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对舅妈撒谎,也许我认为告诉她
一个男同学给我送蛇油,她会想歪了,也许我就是单纯的不想告诉她
。
舅妈也没太在意,倒是舅舅问我:“那要去哪儿拿?”
“他们家住回龙观,有点远。”我脸不红心不跳的继续撒谎:
“要是堵车,我就不回来吃午饭了。”我其实是想留点时间独自在外
边逛逛,哪怕去超市发呆也好,因为今天我就想一个人呆着。
舅妈说:“还是早点回来,都要过年了。”
出门之前我在玄关换鞋,舅舅过来塞给我一百块钱,我不要,
他说:“拿着吧,那边老堵车,要是赶不回来吃午饭,就买个汉堡。
”
一拉扯舅妈就看到了,笑着说:“舅舅给你你就拿着嘛,又不
是别人。”
她这么一说,我只好把钱收起来。
我揣着那一百块钱到地铁站去,果然远远就看到了萧山。他个
子很高,长胳膊长腿,很醒目。我一溜跑到他面前,这么冷的天他连
羽绒服都没穿,外套还敞着,露出里面的格子围巾。见着我咧嘴一笑
,露出一口洁白的牙:“来得挺快的。”
我今天戴了帽子,却忘了围巾,一路跑过来,脸被风吹得生疼
,尤其是长了冻疮的那个地方。我一边用手揉着脸,一边问:“蛇油
呢?”
结果他手插在兜里根本没动:“我还没吃早饭,你请我吃早餐
吧。”
我在心里直叫万幸,万幸兜里有舅舅给的一百块。我说:“请
你吃麦当劳吧。”
他倒也不挑:“行!”
我没想到萧山竟然是个大胃王,一个人吃了两份套餐还意犹未
尽,幸好他没要第三份,不然我那一百块说不定就不够了。他吃的快
,可是喝的很慢,两杯热饮喝了半天还没喝掉一杯。我吃东西一向慢
,就这样我吃完自己那份套餐,他还在慢条斯理的喝饮料。这样单独
跟一个男生在一起,我也不知道跟他说什么好。只看着他眼睫垂下来
,似乎专心至致的在那里吸吸管,长长的眼睫毛微微颤动,就像有隐
形的精灵在上面跳着舞。我忽然不敢看他,于是拿了垫在盘子里的纸
,随手叠来叠去。
我最后叠出了一只很胖的纸鹤,萧山忽然“噗”得一笑,放开
吸管,说:“这是什么,丑小鸭?”
我觉得很郁闷,虽然胖也是只纸鹤好不好?
他把纸鹤拿过去重新折:“你叠错了。”
他重新折过的纸鹤果然很漂亮,他去洗手间的时候,我思想
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