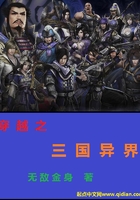厅中众人还敬语连连,那黑衫男子便是几步而来,洒然自得,已是报出家门,众人纷纷转头一看。
两随从男子身披锦袍,站定在厅门之内。一男子手握苏旭递去的锥帽,满颜展笑,对着众客。另一男子则是面若冰霜,夹抱这一把纸伞镇定而立,环视着屋中众人。
两随从衣着貌相竟是相似之极,倒如那孪生亲兄弟一般。众人感奇处,再看两人袍间那若隐若现的长柄横刀,不用多想,这必是苏先生的贴身卫士,连卫士也这般威武,那来人也不该是寻常角色才是。
一席黑衫的苏旭几步开笑而来,狨平和龙广即是迎了上去。
“苏先生,不停那快马能亲来赴这寒宴,真让龙某由感荣幸之至啊。未能来得及相迎,还请勿要见怪,快请,快请。”
苏旭还礼处,文儒一笑:“将军可真当是言重了,在下这不请自来,搅了众位宴席之乐,无礼冒扰之处,还请将军包涵才是。”
龙广早已过了知命之时,已近花甲。却是恭敬的得对着一个小子后生般模样的黑衫苏旭和笑道:“先生这是哪里话。”兴然之处,龙广回头对着众客笑引道,“龙某这给大家引知引知,这位便是烟蓉才郎苏旭苏先生。”
众人一听,显得不知,互顾相望,唯有那驻京重官王大人显出惊诧之色,起身拱手相礼处,还不时打量着黑衫苏旭:“敢问这位可真是苏旭苏先生?”
苏旭面显一笑,轻点几许头:“正是在下。”
王大人摇叹处,再做打量。苏旭明眸秀眼,真当传言那般芙蓉如面柳如眉,行貌昳丽,如美妇人般,可是丝毫不输侍郎秋官张昌宗半分。如今身在眼前,还如那二十出头之样,孰知,这位号称烟蓉才郎的苏先生本是和龙广年纪相仿,两人站在一起,倒显得如父子辈一般。
“来,苏先生请快些入座。”王大人这一句话倒比龙广先行出口,神情激动,啧啧称奇之处竟忘了自己也是来客身份。
对于才貌双绝得苏旭,更多的传言则是这位才子巨擎早年隐于山川,不得让世人窥见真容,能与圆策大师齐名必不是寻常之人,诗词曲赋样样精通不说,更兼一幅化外修禅之心。苏旭让世人所念叨的便是“武皇亲临寻秘山,不得烟郎一回容。”但又有几人得知烟郎便是面前的苏旭,也许他的诗才造诣早已被世人遗忘,留下女皇曾对他寻觅佳话。
苏旭出于蜀川益州之地,师乘扶摇子,入蓉门大家。当年一曲《离凰》之音传遍长安大街小巷,俘的万千蔻女之心,而后又著神韵《洛河图》,使得女皇还有心寻见他人数日,但也未能寻迹到丝毫。也有些微风言传是,长安当年红极一时的曲魁冉姑娘便是师从苏旭。只是后来不知何故,冉姑娘同苏旭一般消失在繁华之中。
听过王大人的孜孜讲述,众人再把敬仰的目光投向容美昳丽的苏旭。但见苏旭倒是在众人的往来言间举止悠闲,不时还察望着龙塍这处,这倒使得龙塍坐立不安起来。
“不知苏先生为何一直看着在下,是为何意?”
龙广投来示意目色,稍显责备:“塍儿,怎么说话的,不可对苏先生无礼,今日苏先生和众位大人可都是贵客。”
“我…我…”龙塍听着龙广的责备,又是无言作对起来。
见龙广责备龙塍,苏旭连忙劝下龙广:“龙大将军,此言言之过重了,在下虽是常年居于风连寨中,对外界之事也是听得一二,龙家两位公子一位勇武。”苏旭指着龙湛。又看向龙塍这方,再行言道,“这位公子虽是书衣打扮,可一股英气可是透体而出,日后定也是有番大作为才是。”
龙广作笑而回:“先生真是谬赞了,犬子若真有先生十之有一,那龙某人便心慰不已了。”
“诶,自古英雄出少年,龙二公子还有好些路要走,此时定下结论怕是为之过早吧。”
“苏先生所言也对,自上次风连寨一别,也有好些年头不见先生了,先生还是那般旧日风采,不改一丝,今夜到此,必要好好款待先生才是,已报当年还马之恩。”
龙广言语一休,把酒相邀,众人纷纷高举。那王大人的目光却落在苏旭身上,过会儿必是有心寻教。
龙夫人见众人谈笑饮酒,也不再作何逗留,起身告别之后便招呼了下差又上了些许佳菜。领着遮面的叶娜和小婉那念念不舍的目光出了厅门。
龙塍见是母亲领着叶娜出了去,那苏先生还注视着自己,心里虽是不自在,又怕父亲怪责,也只得坐在远处。
……
此时神都的轮亲王府中,李隆基和李旦正对视而立,两人久久不曾言语一句,只是李旦面上显着焦急,强忍镇定。
“三郎,今夜你这般又是想要做何?为何要阻挡为父出这府门?”
李隆基再视杵定在旁的李林甫,见他一面担忧害怕之色,两人本是先前商量好了的,如今李林甫怕是准备打那退堂鼓,李隆基心感无奈,这才正声对着李旦,道:“父王,三郎早已加冠为王,也不是弱冠之年的人了,此刻冒昧斗胆问父王一言,父王近日不上朝堂,不进朝柬,对府中之事也是不闻不问,难道真是贪恋上了那对弈之趣不成?三郎见怕是没有那般简单才是,特此才行此举,斗胆求问父王所行之事,亦可言之于三郎,是为公,三郎和林甫兄长自当尽力相帮,添些绵薄之力;若为私,三郎绝不会掺手阻挠。”
话音字字传来,铿锵有力,李隆基面上表情毫不作假,这也使得李旦不由再多看一眼李隆基,欣慰之处却也是不知该如何答言。
“难道你今夜和林甫所行阻挠便是为此?若是为父不愿作答,你将何为?”
一个猝然,李隆基落地而跪,只听的膝盖与地板的撞击之音,害得李林甫惊惶失措,慌步来扶。
“三郎,三郎…好好的怎么又行此态。”
久扶不起固执的李隆基,李林甫显得一脸为难之色,婉言向着李旦那处:“王叔,你看三郎这…这…”
李旦丝毫未曾料得李隆基会出此举,加之对这三子的万千溺爱,再思近日所行秘事,一时胸中闷火,怒意生起。
“李隆基,本王命你速速起身。”
常言道知子莫如父,可这次李隆基不知何处来的坚决之心,面色如铁,丝毫不可动摇一般。
李旦冷眉再对:“父王的话难道你不肯听进。”
“王叔,且先不要动怒,听得林甫一言,三郎今日如此这般,林甫也当有罪,我这就劝下三郎,还请王叔不要怪责。”
李林甫再行搀扶:“三郎,我看今夜就此罢了,万不可惹王叔生气才是。快些起来,来,快…”
纵使李林甫万千言语相劝两人,这一跪一站的两位王爷,却是对峙在这大厅之中。此时父子两人丝毫不肯让对方一步,李林甫万般劝阻无效之下,索性把心一横,陪着李隆基跪在地上。
李旦怒色早已淡去几分,面上阴云刚刚散去,此时见两人同跪在地。
“林甫…你…”但瞧这阵势,今夜能出这厅门怕是万般艰难,李旦冷眉而视片刻,压下心中怒火,语气平和了几分,“三郎,难道你今夜非要求出为父所行之事的目的?”
李隆基振声回道:“父王可且言明于我,坊间也有谚言道是,打虎还得亲兄弟,上阵须教父子兵,如今父王一人秘行所谋之事,三郎早已猜的半分,唯恐不能出些绵力。”
李旦看着李隆基,眼中惊疑之色陡增,试探问道:“告诉我,你听闻到了何许?”
“有常言道,知子莫如父,可是父王也忘了,还有一句,知父莫如子。昔日皇祖母禁足太子皇叔,张柬之大人几番命柬上书,不惜冒杀头大罪,才能使得太子皇叔入朝参政,而后再柬不应修那星泰神宫,冒皇祖母之大不违。今日朝中张大人再行进言,罢修星泰神宫,皇祖母龙怒行威,当着众位在朝大臣的面,听得梁王建议,被当众行杖半百,事后还游行到轩门之外,如此过分之事,我和太子皇叔怎可袖手旁观,但行向皇祖母求的一言,望求龙颜开恩,却奈何我同太子皇叔皆是被皇祖母责斥闭过一月,不得参与朝堂政事。”
两位王爷此刻在府中大吵,一旁的婢女纷纷退了出去,心怕会得知了一些不该知道的秘密。
李旦看府仆都走了,沉目道:“那这些与我出府何干?我已不问朝堂之事。”
“但怕如此不符父王秉性,三郎虽加袭临淄王,众官视我年幼,唯有权彦桓大人力挺于我,但是三郎心知,父王虽是不过问朝事,可心依旧在那朝堂之上。梁王二张兄弟所行恶事,世人皆知,父王怎会袖手旁观?今日朝堂之上,皇祖母也已罢黜张柬之大人的辅相之职,另招杨再思归朝,怕是赴那辅相之位,如此这般,父王这个相王之位怕是早晚会被架空殆尽,而这偌大的大唐基业便是要毁在那群武姓之人手中了。再观近日父王出入之地,大多是新任御林军都统朱祁府上,此中之事,三郎也是忧怕不已,所以今夜行此心言,父王是否要行那…”
李隆基话语到此,李旦却是高声出言打断:“不要再说了。”
李旦一声怒吼之音,把厅门之外的婢女也是给吓跑了去,留的厅门之外一片昏黑。
待到厅中安静些许,听的见屋外的蛙声连鸣之后,所有人都没了方才那般激动情绪。李旦几经思索之后,卸下皱眉,松下气来,轻声道:“三郎,林甫,你二人先起身吧,随我来一趟。”
……
长安驿馆之地,见那萤星微光,闪闪断断,龙塍背依柱栏长叹一口。
“二公子,你为何跑到此处来了?”
回身一看,龙湛正笑容满面站在龙塍身旁,烛笼之光下,龙湛红着脸倒显几分醉意。龙塍心中还担忧着昨夜李宅旧府之中见到的秘密连图。
“大哥,你说这世道好么?”
“咦,二公子今日一直冷面若霜,不苟一丝言笑,难道就是在思考这些事情?”
龙塍接道:“近年风言朝中已是腐政,皇上更是不闻不问,放纵不管,如此下去,真怕如此会出一些事端。”
龙湛又作一笑:“二公子何时开始关心这治国之事了,我就觉得咱们龙家历代操武,为天子守那藩外之地,恪忠尽职便是,朝中之事还是如父亲言说的那般,不加过问,绝不参与。”
龙塍叹道:“要是无国,又是何来的藩外之地?!”
听得龙塍的叹言,龙湛才把笑意消去,显出一丝惊讶:“龙塍,今夜为何又是如此多的感慨,难怪席到中处便是出了来,害得我一人陪坐那群京官与苏旭先生修文赋句,好生无趣,所以这才也出了来。”
龙塍心中积忧,苦闷无比:“兄长,我昨夜发现一秘密之事,想要同大哥你讲讲,但请大哥勿要轻易说出。”
龙湛面对龙塍今日连连出现的怪异之言愈感疑惑:“你且说来便是,大哥定会守口如瓶。”
龙塍回转左右,见是无人在这附近,再沉下一气,小声道:“大哥我发现有人想要谋反!”
一听“谋反”二字,龙湛着实吓了一跳,环顾左右后连忙问道:“是谁?你是如何得知的?”话语一完,龙湛还感不放心一般,面色起得严肃之色,“走,去我房间再讲,此地切不可胡言乱语。”
烛台之火熄了三分,屋中暗淡了些,龙塍把自己所行所见之事一一告知了兄长龙湛,当龙湛听到龙塍口述中的连图之时,其惊讶程度比这亲眼见到的龙塍还要严重。
“二弟,你的意思是国师想要谋反?”
龙塍摇头道:“我也仅仅只是推测而已,却也未能有半分证据。”
龙湛做出了一幅思忖之态,稍久之后,只看屋中已是越来越暗,才听龙湛恍然大悟道:“我就说国师怎会如此心急把他孙女秘密送出宫,冒着杀头的大罪,送到长安来,等等,不对呀,国师怎能凭借一人之力掀起波澜?”
龙塍也是陷入沉思之中:“这也是我想不通的地方,老国师本是一祀官虚职,如何行那谋变之事?!”
正当两人相继陷入沉思之时,只听龙湛似乎想到了什么一样。
“我想起来了,是相王李旦。”
“轮亲王李旦?!”
“对,咱们还尚在神都之时,便是听得有人传言,相王荒误政事,时常出入国侯府中,言传是贪上了那修棋对弈之趣,如今想来,怕是没有如此简单。”
……
轮亲王府之中,李旦看了一眼低头不语的李林甫:“林甫你也算是我看着长大的,你的脾性我当自知,如今王叔我接下来要讲之事,事关性命,不知你愿和王叔一道行事否?!”
李林甫本是和李隆基从小玩大的发小之人,两人情同手足,只是李林甫荒废前景,爱去游山玩水,可一出游,遇上些稀奇之事也会回来一一告知于李隆基,有时还会带上奇珍之物,赠给李隆基。所以,李林甫时常来王府之中也是无人阻拦,如入自家一般,屋中仆差也是听得李林甫随意差遣,这也亏得是李旦的宠爱。
见是两人点头,李旦心感时机成熟,可以对李隆基全盘托出,也没把李林甫当作外人。
“今夜我要告知你二人之事,绝不可泄漏,你二人可知?!”
两人又是齐齐点头,只等李旦开口。
李旦见是两人已做聆听之色,严肃道:“如今朝堂之上,梁王等同党羽已是把持朝政,皇上沉迷宫中,对此也是不闻不问,先有张氏兄弟私卖官爵一事,再有梁王有谋夺取储皇之嫌,后又罢黜忠正之官,祸乱朝纲。太子秘令于我,为保大唐基业,须铲除梁王等同党羽,择其良机之时,勤王除佞。”
李旦话语一出,李隆基虽是心中早已做了准备,此刻再是得听李旦之言,仍不免显得惊恐:“什么?父王果然谋得的是此。”
李旦无奈叹气闭目:“我本不想让你二人参与进来,可事到如今,张柬之大人和权彦桓大人也被梁王相继诟害,此事能托之人也是不多了。”
李林甫常年历游,胆色也是增了不少,不但没有李隆基那惊恐之色,把头抬了起来,一脸认真之样:“王叔,接下来又当该是如何行事。”
【已修,求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