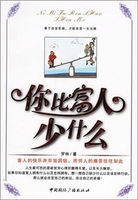大安现在之所以发笑,一方面是想起了那忍俊不禁的往事,另一方面,是因为师父一语道破了天机,使他当下悟到了自心即佛、心外无佛的真理。他想了想,又问:“识得自己本来就是佛以后怎么办?”
百丈仍是借牛说禅:“找到牛还会怎么办?骑上牛回家呗!”大安点点头,说:“师父,我知道了。可是,今后如何保持呢?”百丈道:“你不是经常放牛吗?你就像平常放牛那样,手拿鞭子看着它,不要让牛偷吃了人家的庄稼。”百丈大师叽里咕噜地说了一堆庄稼汉的禅。这时的大安,早已成了劳作者的一分子,所以能领悟到师父“庄稼禅”的奥妙。从此,大安休歇了自己那像猢狲一样向外驰求的心,一心一意做个本分的庄稼汉,老老实实牧自己的牛。一边放耕田之牛,一边驯心性之牛。久而久之,终于打成一片,样样精通,一举两得。
后来,与他最为要好的灵师兄,奉师命独自一人到湖南大沩山开辟道场,但很久都打不开局面。俗话说,一个好汉三个帮,元帅离不开中郎将。大安禅师主动请缨,带领几个同门小师弟来辅佐师兄。他拿出在百丈山学到的看家本领,开荒种地,供养大众。山中有粮,心中不慌。他的躬耕助道,真的起到了续佛慧命的作用。因为大沩山中粮食充足,禅僧们可以安心修行,所以前来求佛问禅的人多了起来,并渐渐发展成为住众一千五百人的天下第一丛林,成了当时规模最大的禅宗道场。
沩山灵圆寂之后,大众请求大安主法。他是百丈亲手教导出来的牧牛汉,上法堂说佛法自然离不开牛:“你们这些人总是请求我接任住持之位,是想得到什么呢?如果想成佛,很简单,你自己就是。你们哪,担着自己的佛不知且不觉,却到处向外寻找。这就像焦渴的麋鹿去追逐太阳,什么时候才能解渴呢?我们都知道,那在远方的阳光下,看起来波光粼粼的岚气,并不是真正的水呀!等你受它的诱惑走到跟前之时,就会发现它仅仅是一种幻象。所以,你们若想做佛,只要舍弃颠倒梦想、攀缘邪恶、污垢不洁的众生心,就是初发心的正觉佛。除此之外,还能向何处寻觅?因此,大安我在沩山三十年来,吃沩山饭,拉沩山屎,就是不学沩山禅。我只是看一头水牯(gǔ)牛,如果它离开大路去吃路边的草,就拽紧鼻具把它拉回来。它刚想去偷吃人家的庄稼,就用鞭子狠狠地抽它。这样训练久了,它便通了人性,能听懂人的语言,变得十分乖巧了。到如今,它已经变成了一头露地白牛(象征清静佛性),常常跟在面前,打都打不走。”
大安禅师将参禅喻为牧牛,可谓形象至极,恰到好处。他说得通俗易懂,一方面,使得禅僧们面对没头没脑、无从把捉的禅,有了一个浅显的入手处;另一方面,将禅修与日常劳动拧在一起,能结合实际,体味到禅的妙用。
后来,晚唐时,著名的禅师雪峰义存很敬佩大安自然淳朴的禅风,他在山里采到了一根树枝,形状很像蛇。他将树枝做成禅杖,在上面题写了八个字“本自天然,无须雕琢”,派人送给了大安。大安拿来欣赏了一会儿,吟道:“本是住山人,且无刀斧痕。”两位大师都在借事说禅。
一天,石霜庆诸禅师在大沩山住了一段时间,来向大安辞行。他刚要礼拜,大安问他:“有句无句,如藤依树,子意如何?”
这是大安时常问学僧的一句话,后来演化成了一个著名的公案。当时,石霜庆诸尚未开悟,无言以对。他怀着一颗惆怅的心,离开大沩山,来到了禅师道吾宗智的寺庙。道吾与大安是好朋友,他得知庆诸从大沩山来,关切地问:“大安有什么言句开示呀?”
庆诸学说了“如藤依树”的公案。道吾说:“你为何不回答他?”庆诸老老实实说“:因为我腹中空空,说不上来。”宗智说“:你替我看家,看我去给你报仇去!”
宗智急匆匆赶到大沩山,大安正在和泥抹墙。他回头,忽然看见宗智站在背后,惊奇地问道:“智头陀(苦行僧),你好稀罕哪!什么风把你给吹来啦?”
宗智拉开一副好斗的架势,说:“什么风?禅风!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我来问你,你总是问诸方禅僧‘有句无句,如藤依树’,是不是这样?”大安说:“是。”宗智反问:“树倒藤枯时如何?”
大安用手指着宗智,什么也不说,只是一个劲儿哈哈大笑。宗智被他笑急了,猛扑上来,扑通一声将他摁在了泥水里。大安不管不顾,躺在泥里,仍然手舞足蹈,哈哈笑个不停。
这件事,在后一代禅师中间还引起了一场法战,煞是好看:罗山道闲禅师在禾山之时,与清贵上座叙说禅林掌故。清贵说:“禅林之中没有谁能排位第一。比如大安禅师,他教化一千五百人的高僧,却犹输道吾宗智一筹。”罗山道闲禅师大惑不解:“大安输给道吾?何以见得?”
清贵将大安与宗智的法战说了一遍之后,评论说:“大安被问得无话可说,只能呵呵一笑,最后被摁倒在泥里。这不是输给宗智了吗?”
罗山道闲禅师道:“小孩子在看一幅画的时候,总是先看它画得像不像。若是画得十分像,就认为是好画。听君说禅,就犹如小儿论画。你怎么就没想到,宗智是恼羞成怒,才摁倒大安的呢?”
清贵狡辩不停。道闲正色道:“上座,你三十年之后,若是住持寺院,千万别再举这个话头,省得丢人。”清贵反复不肯认输,一定认为宗智有理。罗山禅师大义凛然地站立起来,一把将清贵从座位上擒了下来,摁倒在地。他大声对法堂里的众僧说:“各位,请注意一下。我今日与清贵上座,为大安与宗智‘如藤依树’的公案展开法战,以雪他横加在大安禅师头上的委屈。且请诸位评判。”
正在这时,匍匐在地的清贵突然大喊:“知道啦,我终于知道!是我错啦!谢谢罗山禅师,我明白过来了。”原来,在被罗山揪下座位,并摁倒在地时,清贵突然明白了,大安禅师那“有句无句,如藤依树”的法语是在激发参禅者起疑,要你截断两头,得个转身之处的路径,免得你就像那缠树的藤子,只是依附在他人的知见上,万年也无法独自站立!
景深
有关牛的禅话,在禅宗诸大祖师的语录中记载颇多。可以这样说,如果离开了牛的公案,中国禅宗必然是另一副模样。
较早出现的“牛公案”,是怀让以“打牛与打车”的机锋,纠正了马祖道一对坐禅修行形式的执着,由此,拉开了禅宗新阶段的大幕。此后,马祖开辟“洪州禅”,天下为之瞩目。一时间,大江南北学禅修禅谈禅蔚然成风,好不热闹!在马祖的儿孙中,许多人都曾直截了当地以“牧牛”来誓喻修行。先有石巩慧藏的“一回入草去,蓦鼻拽将回”,后有百丈、大安句句不离牛的“牛禅”。而南泉普愿禅师,更是将活生生的牛直接牵进了庄严、神圣的法堂。他说:“我从小就养了一条水牯牛,想到河的东边去放牧,恐怕它吃了国王的水草;往河西去放吧,也怕它侵犯了国王的水草。不如就随便放放,总不见得有什么过错吧?”
为什么“牧牛”的公案多发生在马祖一系的传承中,而非同时代的禅宗另一大体系石头希迁那里?这实际上非常客观地反映出当时的一大史实:马祖建丛林,百丈立清规。
禅僧们肇建自己的道场,自立门户,必须首先在经济上获得独立,做到自给自足。这就需要大力提倡从事劳动,搞好农业生产。马祖及其弟子启建的丛林中,禅僧们每天必须下田干活。试想,农业生产,耕、种、拉车、拽磨,哪一样能离开吃苦耐劳、力大无比的牛?
它默默耕耘,为主人播种希望;它全力以赴,帮助人们越过坎坷;它奉献血汗,为人群换来丰收……百丈、南泉等大师高扬农、禅并重的大旗,倡导劳动即禅修、日用生活即佛法的全新理念。他们将修行、禅悟与耕种紧密结合起来,在说禅讲法时当然离不开手边事、家常话。而牛,是他们一天都离不了的亲密伙伴,禅话里自然就少不了它了。
祖师们以牧牛来教导弟子,真是美事一桩:活干了,禅也修了;粮食瓜菜大丰收,开悟的禅僧一大群,真可谓一举两得!
牛与禅的渊源至深,以至南泉与沩山两大师干脆说自己百年之后去做一头水牛。其禅旨意趣很值得深入参究一番。所谓的牧牛,也就是一个调心的过程。大安禅师的牧牛话,将调心的修行程序通俗化了,使我们每一个平常人都可以从这里入手进行禅修。我们像手牵缰绳牧牛一样,牢牢盯住“牛”--自己的心念,不瞌睡、不走神、不妄想,这就是最好的修行。在“牛”没有驯服之前,绝对不能放松。久而久之,牛与人合二为一,我们就能在日常生活中保持一种平和、恬静的心态,显发一种类似灵感的智慧,从而得到真实的受用。
心语
禅宗以“牧牛”比拟调心,惟妙惟肖,形象至极。野牛有一股犟脾气,需要很长时间驯化;恰如我们的心,妄想纷纭,杂念丛生,极难降服。
百丈怀海说:“如牧牛人,执杖视之,不令犯人苗稼。”石巩慧藏说:“一回入草去,蓦鼻拽将回。”禅宗这一调心方法,完全可以移植到现实生活之中。由于种种缘故,我们每一个人几乎都养成了一些这样或那样的不良习惯。
这些习惯或者说习气都是长时间形成的(佛教称之为“熏习”),久而成性,很难改变。比如抽烟,所有抽烟者都知道其有百害而无一利,但真正能戒掉的人少之又少。
下决心改变旧习气,就要像牧牛一样,时时保持警觉之心,当其欲念刚刚冒出头时,马上“蓦鼻拽将回”,绝对不能迁就。只要你用意志力矫正一次,其惯性就会减弱一点点,如此坚持下来,你的觉照力就会越来越灵明,而固执的习性却越来越弱直至消失。
“鲍鱼之肆,久而自臭;幽兰之室,日增其芳”。不良习性与好的习惯都是自己养成的。笔者曾是二十五年的烟民,每日吞云吐雾两包,用此法七日戒绝,而今已十五年。相信自己,你也能。
〔1〕蠹(dù)鱼,即书虫。也用来形容爱书人。
〔2〕业师,指教育过自己的老师。
〔3〕圣果:即正果,指佛教修行所达到的圆满境界。
〔4〕岚气,指山林间的雾气。
〔5〕肇建:创建,始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