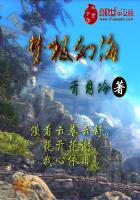街道已经灭了烟火,这是林慕白闻到的。
林慕白站在二楼,能望到街上绑着黄巾的巡逻兵,挂着长枪,腰间挂着明晃晃的大刀。行人也陆续多了些,据说伤兵把鬼子撵走了,拿命换的,活着的跑南边去了,只有几家大户和乡绅组织了慰安会,直到有人接受了军务,再移交权力。
已是黄昏,落霞分外红些,也许为了祭奠亡魂才这样,只为那些拿自己性命赶走鬼子的士兵。
许太太备了三两个小菜,熬了一大锅面疙瘩,就着剩下的那半瓶黄酒,算是回门宴。许太太说,这是好兆头,阎王放命的意思。
次日天亮了,城里的秩序好了,中午时分,连沿街的店铺都开张了,纷纷贴起红纸对联,报平安。
林慕白把银元归还给了大小姐,大小姐拿了一些给许太太,让她买些红纸,也沾沾喜气,顺便给芝诺带些甜糕回来,便躺藤椅上午睡了。
许太太领着银元,看了一眼他俩的神色,心里甜得都腻出了泪花,一转身,念着小姐的吩咐了出门,路上却是想着红纸买回来,该让林慕白写什么好?要不不写平安对联了,改成剪纸好了,自己还记得喜字怎么剪呢!嘿嘿一笑,不行不行,皇帝不急太监急,自己都不带把的,更不能急,不能急着瞎操心!得让林先生写字!不过,也不知道林先生字写得好看不?想得出神了些,不小心被什么拌到了脚,抬头一看,正是东街棺材铺门口新进的木料,碎了嘴沫,直喊晦气。
却不料被店家小二看到了,追着骂许太太,“你着个青楼货色,咒我家的生意,你个臭婆姨。”
许太太一听,气得不清,想着对骂几句,一抬头看是鲁家的招牌?赶紧转过身子跑远了,心想那天鲁先生来了,不是说他们要去南边吗?什么时候回来的?什么时候开了棺材铺了?呸呸呸,连唾了几口,她才骂自己混,小姐只有林先生配得上,应该照着林先生教的想,开店的都回来了,代表北边打赢了,这下这边就安全了。这样下去,岂不是得帮小姐准备嫁妆了,嘿嘿。一想起嫁妆,又叹了口气,唉,要是小姐不卖了铺子赎自己的身契,倒还有着嫁妆,唉......小姐的病,这些年那么药下去了,还只是不治根,花了那么多的冤枉银子,不知觉中,连脚步都沉了些。
林慕白摸了下刘小姐的额头,还是有些低热,躺在正堂藤编躺椅上估计已经睡着了,还有点小呼噜,盘发也散了几缕挂在嘴边,慵懒而惬意。怕章芝诺惊着她,便带着丫头出了门,把远门掩实了,才朝茶店走去,问了梓琳药房的地址,回头看芝诺与书源才见面便熟络得很,便留下她在茶店玩,看着白熙一点头算是放下心了,才自个朝药店赶去。
近的那家药店没开,只能沿路打听过去,董氏药房关门,齐氏药房也是,问了巡街的安保,才告之鲁氏药店开着,在十五奎街附近,急忙赶去一看,长长的队,只得沿队排着。听着边上人彼此间的招呼,都“可好”都换口成了“死了几个”,抬头叹气,这世道,唉……
林慕白抓了两帖退烧药,涨价了一倍,想着店家都想把被抢的赚回来,骂了句黑心也罢了,转身往回走。路过章氏香料店的时候,突然记起刘毓菡红唇的高脂甜味,挠了挠耳朵,买了一小盒牡丹唇纸,据说拿嘴沾水含了也甜,还有股幽静的香,便爽快掏钱了。路过滋味观,又出手买了些甜糕,包了一串,两户人家够份。颠着脚步晃到了茶店,只有王子琳看店,她看着他却假装忙着,躲开了眼神,乖乖的。一听,孩子的嬉笑隔着门帘从后院传来。
林慕白掀开布帘,看到白熙背着身不知道在做什么,也没来得及招呼,便被两个小家伙瞅着了,机灵地过来抱着了自己的腿,分了甜糕,说,“以后都得乖,下次还有甜糕吃。”
“好。”书源拎着甜糕放茶条上,把芝诺的放在一边,仔细地抽开了打结的纸绳,掀开自己的纸包,塞了一大块芝诺手上,犹豫了一下,自己拿了块碎的,“妹妹先吃我的,吃完了再吃你的。”
“好。”芝诺哪能明白哥哥的心哪,估计等她拆开自己的,哥哥大概会说他吃饱了,妹妹留着吃吧。林慕白暗暗点头,又摇头,唉。
“白熙,你父亲呢?”林慕白上去拍了拍白熙的背着的肩膀,没动静,只得把肩膀转了过来,发觉她脸上的泪倏然滑落,“怎么了?”
白熙突然拉着林慕白走到院子边上,眼泪突然洒了下来,一边哭一边揉眼睛,轻声说,“慕白,许太太方才来了,刘姐姐……刘姐姐她,她不在了?”
“不在了?也许上街抓药了,我方才出门忘了跟她说。”捧着白熙丫头的脸帮她擦泪,林慕白笑笑说,却发觉她泪串得连成了线,都来不及擦,才醒悟了她说的不在了的意思,怎么会?不可能呀,刚才还好好的,怎么?轰的一声,脑子空了。
白熙使劲抱了一下林慕白,用了好大的力气,借着林慕白的身子挡着孩子们的眼光,悄悄拿袖子擦了眼泪,低声说:“芝诺留在这吧,你不要惊着了孩子,你去看看吧,我在,孩子们都好好的。”
林慕白顾不得打招呼,一愣,一醒神,转身便走。离着家门好几步,便听到了许太太的哭喊,红纸撒得一院子都是。正堂梁上的白绸布,只留下半截,风刮得一抖一抖的,躺椅边上白崇文背着手,王子瑾红着眼,牙齿咯得崩甭想,许太太倒在地上。
躺椅上的她,双目紧闭,微蹙的眉额,垂搭下来的手,松散着手指,手心空空。
林慕白上前扶起了许太太,看了一眼白崇文,白崇文轻轻摇了摇头,心里冰凉。
“林先生……我……小姐要红纸,我回来……已经这样了,可是……这不可能呀,芝诺是……小姐的根呀,小姐……不可能自尽呀……对了,一定是章泼妇来了……一定是的,小姐是被她逼的,你要替小姐报仇呀!”
一根绸布却吊不直许太太的心腰,歇斯底里的喊了几声,坐地上了。林慕白含住了悲哀,扶她坐板凳上,却看板凳却撑不起她的腰,白崇文立马扶住了晕厥的她。
林慕白正欲上前掐她人中,却被白崇文制止了,一看他的眼神,懂了,或许没有哭声的悲哀,祭奠起来更加透彻些,也顺利些。
王子瑾傻傻地站着,目不转睛地看着藤椅,林慕白瞬间确定了,那个背影,那晚朦胧时楼上的动静,还有多出来的面粉,还有芝诺口中的黄哥哥,都是王子瑾。只是自己没又想到江南人口音偏薄的事实,黄跟王的口音是差不多的,“是不是你做的?”
王子瑾没有吱声,只是含着泪花看了一眼林慕白,林慕白却不知道了。
白崇文把许太太安置到了东厢,才出来拍了拍林慕白的肩膀:“事有蹊跷,绸布勒不出这细痕的,估计是金刚丝之类的才……”
顺着白崇文的手指,林慕白才注意到刘毓菡脖子上勒痕,比烟还细的勒痕,渗出了淡淡的血迹。
“子瑾一直在店里,与我一起修铺门呢。”白崇文注意到林慕白的眼神,冰冷地盯着王子瑾,便拉着林慕白到了院子,将许太太来店前后说了一通,“慕白呀,人死为大,后事办了吧。”
“子瑾,过来。”白崇文喊过了丢魂的王子瑾,重重拍了下他肩膀,“还愣着干什么,跑东街棺材铺定口棺材,一匹白布,一些白纸,速去速回。”
王子瑾耷拉过了神色,复杂地望了一眼林慕白,又朝白崇文一躬身,步履磐重地出了门。
林慕白捡起了一地的红纸,和白崇文把柴房门板下了,简单地搭制了灵棚架子,垫了一床被子,把刘毓菡抱在板上。
不一会,王子瑾鼻青脸肿地回来了,门口停着板车,上面拖着黑亮的棺木,三人搭手一起抬进了院子,都没了动静。
许太太不知什么时候醒了,看见王子瑾脸上破了几个口子,拿了些棉布递给王子瑾,哪知他挡开了,急忙忙出了院子,丢脸魂魄似的。许太太更难受了,估计着他可能买棺材是被刁难了,因为早上的话吧。回过头,看着小姐的模样,想到了些刚才还活生生的,忍不住又低声哭泣,被林慕白回头瞪了好几眼,才停住了哭。
“许姐,替小姐更衣,把口红上了,让她安安心心地走。”林慕白递过盒子,抓着中药往院子一扔,毛毛细雨,沾着了散落的中药,掉了一地的苦味。
林慕白回了屋子,撕了许太太递过来的白纸,铺开方才院子捡起的红纸,研磨,起笔:雨中竹叶含珠泪,苦雨凄风悲永别。落了笔,又呆坐了一会,看着茫然的许太太,便说:“许姐,多弄些面疙瘩,我饿了,说不定白掌柜他们晚上也饿。”
许太太犹犹豫豫地挪不开脚步,林慕白走进了,搭着她的肩膀又说:“许姐,我在,家在,芝诺小姐便在。”
许太太噙着一对汪眼欠了一福,擦着眼泪进了柴房,都不知道掉了多少进了面疙瘩汤里。
林慕白转身出了屋子,白崇文走了,只有她安静地躺着。望着她,淡淡地望,静静地看,却是发现她肌肤还是那么的白,嘴唇还是那样的红,暗道了一声:毓菡,今晚我陪你,我留下,明天,我再送你,送你葬在心里。
俯身摸了一下她的秀发,还是一手的滑柔,眼泪却还是像秀发一样,滑落,滑落。
......
二更时分,白崇文风火地进了院,王子瑾抱着一大团白布。
许太太招呼着大家吃了点面疙瘩,便拿着剪子扎起了灵堂的白花,没有哭声,也没有吱声。
四更,白熙领着睡意惺忪的孩子来看了一眼,书源大概想到了自己的姐姐去世的模样,呜哇一声哭了出来,把芝诺也带得哭出了声。
天亮了。
“慕白,封棺吧,这乱世,上山入土吧。”白崇文回头喊上了王子瑾,三人合力盖了棺,抬到院外,已停着驴拉的板车。
一行径直往吴山赶去。
几捧土,一阵泪,红色的丧字被火一点,冒了一阵烟。
拍掉手上的土,蹭了眼角的泪,抬头看天,有阳光,可惜只有一点。
一场红丧,一点阳光。
……
不知几天了,官家只是说了个自缢,没了下文。
林慕白羡慕孩子的心性,拥有健忘的孩提天性,避免了刻意淡忘般的熬骨过程。
芝诺一大早依旧往茶店跑,喊着去教书源练字,已经持续几天也不腻,许太太绷着脚步一路小跑跟随。
西冷周刊那边走了一遭,拿了第一笔稿费,梁钟希望他趁着如今得闲,尽快写多些,万一时局乱了,估计物资什么的不花费力气是难办的,手无缚鸡之力的便只能靠财力了。林慕白想想也是,芝诺得活着,便一直窝在房间,饭菜有许姐,烟纸油墨白熙倒送得勤快。
十一月的夜变得冷了些,也短了些。
许太太怕林先生着了凉,夜里摸过来几趟,都发现烛火通明,有心提醒些,却不知如何说起,重复着叹气,悄悄回屋。
夜里时分章智山来过,许太太悄悄掩了院门,跟他外面说话。高大的男人张口闭口称呼小姐为“她”,让许太太反胃。她更看不起章智山这个男人,他给的钱财一分不少都收下了,替小姐,替芝诺,这是他应该对她们付出的责任,这是他的良心债,她收了,小姐也不会怪。
“毓菡走了,我心很疼。”这个男人说话了。
许太太眼中却只露出了丝丝戏谑,他接着说他听说小姐不在了,来看看能帮上什么。
许太太没说话,冷冷地看着她。
他明白了,她们报官得来的确实流寇或者自缢之类的说辞,她们不信。
“是自缢,我查了。”这个男人低声说话。
“哈哈,章智山,你到底姓鲁还是姓章?”
“姓章。”他接着说他要带兵出去了,家人也都回了西子地。他说他怕鲁素蔓不死心,针对芝诺不放之类的说辞。
“你姓鲁,你叫鲁智山,你是鲁秋山的女婿,你是鲁素蔓的男人。”许太太腻了他的说辞,冷冷的一句,把他关在门外,换成小姐在,一定也是这样的;这个家又林慕白在就够了,换成小姐在,一定也是这样的。
夜色下的章智山索然并且无奈,或许娘亲临别的话语在理。或许许太太的话在理:“鲁家走了,小姐活着,鲁家来了,小姐死了,下一个是不是芝诺?还是我这我破婆姨?瞎眼的苍天生了你,你和你爹造了天煞的孽,你娘瞎眼才让你入了赘。”
......
天明了,许太太扣开了林慕白的门,跟他说想让芝诺搬到二楼住,毕竟是刘家小姐。
林慕白说好。
许太太还说楼上能不能添个床板,她好夜里照顾着芝诺,方便些。
林慕白想来也是,便帮许太太一起把东厢的床拆了,分趟搬上了楼,又给装上,看着满眼喜色的芝诺,心里突然被扎了一根思念的刺,疼痛难忍。
或许人去楼空,比物似人非引起的疼,会轻些。
“林先生,以后你得听我的,姐姐不在,家里我最大。”章芝诺学着大人的口气,叉着腰站在床上说。
“这个我得先去问问书源,貌似有个小丫头,在茶店答应书源听我话的。”林慕白摸了摸她滑滑的脸。
“额……那好吧,书源最大,看在书源的份上,我也听你的话。”她拍走了讨厌的手。
林慕白想摸摸她的脑袋,哪知芝诺巧妙地躲开了,并说:“白姐姐说的,女孩子家家的头,只能被喜欢的人摸,不然掉头发,长秃头。”
“好吧,许姐,我得去西冷周刊一趟,你看着芝诺,她不乖,去茶店告诉书源。”林慕白背着芝诺朝许太太眨眼。
许太太一声“好勒”,心底深处却越加佩服林慕白来,想想要是小姐还在,那该多好呀。回过神,才发现芝诺拿着小手帮自己擦眼泪,一下子涌出了更多的泪花,暗道,小姐你看见了吗,芝诺懂事了。
“许姐不哭,我也听你话就是了。”
“好,好,好。”许太太回过身,发现林慕白已出了院门,正合上院门。
林慕白路过茶店停了,进屋,王梓琳站柜台,白崇文在二楼招了招手,便上了楼。
“慕白,喝茶。”
“闲知,我看最近城中倒也安稳了。”
“呵呵,水面上的,做不得真。”
“怎讲?”
“唉,背后言人,实非雅事,做人哪,两难,活着难,死也难,想说却难出口,不说却难舒畅,唉。”
“还记得在淞沪时,闲知可是这么跟沈秋楠说的,秋楠哪,闲知难呀,娶你难,弃你难,天时不易,佳人难和哪。”林慕白想起那些往事,也学起了捋胡子。
“咦,林先生来了?”背后窜出来的白熙,冷不丁让俩人很是尴尬。
“白熙,不好好教书源写字,又功夫偷闲凑热闹!”白重温激动得胡子差点打了结,道貌岸然的正经不外如此罢。
温烫的开水从林慕白口中回到了茶杯,还引起一阵剧烈而绵长的咳嗽。
“父亲,我得去河坊街置办写宣纸,有墨无纸,总不至于隔空练字吧。”白熙微微一福,刮了一眼林慕白手中的稿子。
“外头不太平,等王子瑾回来了他去买办吧。哦对了,慕白,王子瑾进民团训练了,不知能否熬练出他的心志。”白崇文的目光,落在街上懒散巡街的长枪兵上,叹气摇头。
“闲知,正巧我得西冷跑一趟,白熙要多少宣纸,我带回来。”林慕白盯着白熙看,却不料到她摆着一张方脸给自己,瞬间觉得热心贴着冷屁股上了。
“唉,白熙一起去吧,慕白啊,女孩子家的挑剔,还是由着她挑好,不然厚了薄了多了少了什么的,闹心。”白崇文盯着白熙说,看到她红了半边脸,才收了口。
“谢谢父亲,女儿去了。”白熙朝父亲一喜,顺手帮他把衣领弄齐了,一路小跑跟上了林慕白。
“唉”,白崇文一声叹气,或许只是乱世,他便没了坚持,“活着的日子,得有个盼头才是。”
林慕白在前,白熙落后一小步,安静地跟着,跟了一会,有心想提醒他脚步慢些、女孩子家跟不上,抬头望着他凌乱的头发,想着没女人照顾的男人真可怜,一下子涌起了一阵心酸,咬了牙,忘了步伐应该的矜持。
“要不,先去西冷周刊,可好?”林慕白脚步一停,在十五奎街分岔口。
“嗯。”
一会便到了吴山,一个拐弯到了西冷园子,门口的牌匾改成了维安周刊了。
入了屋,梁钟正满脸黑纹,低头看着什么。林慕白不敢惊扰,白熙也安静地靠着林慕白站着:他原来高我一个头呀!
“慕白来了?坐,小妹妹也坐。”梁钟抬了下眼镜,翘起了二郎腿,丝毫没有文人的儒雅。
林慕白顺势坐在期刊上,板凳留给白熙坐。
白熙心中一暖,瞬间有了决断:喊我小妹妹的那个老头,肯定没有慕白的文采,气度也比不上,所以,心也没有慕白细。
林慕白递过去手稿,梁钟略做改动又递回了林慕白。
“慕白,你看这样可行?”
“行,回去复抄了,明天给你送来。”
“好,不远送了。小妹妹走好。”梁钟和蔼地说,顺势摸了把脸,没有什么,怎么那丫头盯着自己,虎视眈眈似的。
“对了,梁老,牌匾怎么成了维安周刊了?”林慕白回过身。
“只是一些上不得台面的事,慕白勿忧,得看这。”梁钟摸了把胸膛,暗指心吧,算是委婉给了说辞。
“那好,明日见了,告辞。”林慕白出了屋。
白熙安静地跟着,直到快到河坊街,才忍不住发问:“林先生,手稿是折花祭下册吗?”
“是,才稿写了几章。”
“能让我看看吗?要不我帮你抄写,我也好练字。”
林慕白想想也是,一来可以专心稿写新章,一来还能帮她练字,点头便做答应了。
河坊街买了纸,顺路在滋味观带了些糕点,俩人便各自回了家。
傍晚时分,白熙送芝诺回了刘府,顺便带了明日要交的稿子,她已经抄写好了,拿给林慕看。
白熙的字很漂亮,这是林慕白能形容出来的,便考虑再三,答应了白熙抄写上部的要求,喜得她亲得芝诺一脸的呆愣。
次日,林慕白独自去了西冷,出来时还去了刘毓菡的碑前,念了一阵,抽了三根烟,抹了眼泪,便径直回了家,进屋铺纸专心打稿。
一场红丧,在版刻师傅的刀下,印进了折花祭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