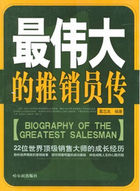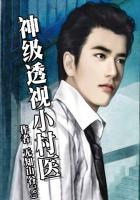一天早上,我接到一封由坎特伯雷寄到博士院的信。我多少有些吃惊地读道:
我亲爱的先生:
由于事不遂人愿,我离开我亲爱的朋友已有些时日了。每当工余闲暇之时,怀念往事,
思及旧时情意,顿觉无比快慰。事实上,亲爱的先生,你以其高才而显赫,我何敢再以科波
菲尔来称呼我年轻时的朋友呢!可是,这一称呼将永远和我家各种债据和抵押文书(系米考
伯太太所保管的与我家旧房客有关各种文件)一起受到珍视,受到敬爱,我敢以我的名誉作
此保证。
现在这位执笔写信的人处于危急中,如将沉之舟,盖因过失和恶运交加。因此我不能在
此将恭贺之词多陈,还是留**行更高洁的人士来说吧。如果先生真地能将此信读到这里,
一定欲知我写此信用意何在?你当然有理由作此问,而我也须声明:吾意不在金钱。
指挥雷霆,纵释怒火,我是否有这样的能力且不论,但我想在此向先生相告:我已再无
希望――再无平安可言――再无力快乐――我的心脏已不复在正位――我亦不复能在人前昂
首阔步。花香虫毒,杯满酒苦。虫毒正盛,花亡无日矣。越早越佳,我不想多言了。
我心极苦闷,而米考伯太太虽身兼异性妻子、母亲于一身,亦无力对我宽慰。我想作短
期之躲避,以48小时之限重游京城旧日行乐之地。至于说到我避难养心之所在,最高法院
拘留所乃我必去之处。后天晚上7点整,我将听凭上帝意愿在民事拘留所的南墙外侧。写到
这里也正是我此信的目的达到了。
吾旧日之友科波菲尔先生,或我旧日之友内院托马斯?特拉德尔先生如能屈尊光临,重
叙与吾之旧情,真乃此生所愿。然所愿也,不敢请耳。我得承认,在到上文提及的时间和地
点时,你等可以看到已倒坍的塔楼之残迹
威尔金?米考伯
附:我当说明:米考伯太太尚不知我计划。
我把那信读了好几遍。虽然知道米考伯先生的文风一向浮华,又极喜欢在一切可能或不
可能的机会写长信,可我仍然相信,在这封信的吞吞吐吐下藏有什么重要的东西。我放下信
来,想了想,再拿起来读了一遍。我仍在揣摸而且很困惑时,特拉德尔来了。
“我亲爱的朋友,”我说道,“我从没像现在看到你这么高兴。你是在最合宜的时候用
你冷静的判断力来帮我了。我收到米考伯先生一封很怪的信,特拉德尔。”
“真的?”特拉德尔叫了起来,“真有这样的事?我收到了米考伯太太的一封信呢!”
特拉德尔说着,把那信拿出来和我交换。他因一路走来而脸色红红的,由于运动和兴奋
的联合作用,他的头发像看到活鬼那样连根竖了起来。他研读了米考伯先生的信后对我抬起
眉毛说道:“‘指挥雷霆,纵释怒火!’天哪,科波菲尔!”――这时我也耸起眉头来认真
看米考伯太太的信。
这信是这样的:
向托马斯?特拉德尔先生致以最热烈问候。如果你还记得曾有幸和你结识的人,你可能
接受我的恳求而抽空读这封信呢?我向T?T①先生保证,若非陷身于困惑中,我是决不会
冒昧相扰的。 ①T?T为托马斯?特拉德尔的缩写。
说起就心痛,一度曾极顾家的米考伯先生现与其妻及其家人非常疏远,这就是为什么我
向特拉德尔先生写此信并求助。米考伯先生的行为同以前大异,其横蛮粗暴已非特拉德尔先
生可以想象了。这种变化日益加剧,每况愈下,他已有精神错乱的迹象了。特拉德尔先生可
以相信我的话――他的病几乎每天都发作。我已习惯于听米考伯先生说他已卖身给了恶魔。
他不再那样相信人而是多疑多诈。我说了这些,你能想象出情形是怎样的了。一旦不小心触
犯了他,哪怕是极其轻微的话(如问他晚餐想吃什么)也会使他忿忿吵着要离婚。昨晚,双
生子要两便士去买本地一种叫“柠檬宝”的糖果,他竟向其举起蚝刀。
请原谅我,特拉德尔先生,向你谈这些小事,可是不这样,T先生又怎么知道我有多伤
心呢?
我可以冒昧请求T先生理解我此信的目的吗?
我能获许向T先生请求帮助吗?我是了解T先生心地的人。
女性由于专情而眼光敏锐,不易受骗。米考伯先生要去伦敦了。今天上午早餐前,他偷
偷写地址于一小纸上,并挂到一个棕色的旧小提包上。他虽拼命遮盖,而念念不忘夫妻情分
的我仍看到那最后几个单词。这一次,他要马车送到金十字街。我能冒昧地请求T先生到该
处看我丈夫并对其晓之以理地劝诫吗?我可以冒昧地请T先生为米考伯先生和他苦闷的家属
调和吗?说不,如果我的要求太过份了的话!
如果科波菲尔先生尚能记得我们这等无名之辈,可能请T先生亦代我向他问候,并转致
我的同一恳求?切记切记,此信要绝对保密,万不能向米考伯先生提起。我不敢抱此奢望,
但如蒙施惠肯复信于我,请寄坎特伯雷邮局交E?M即可。这比写明收信人姓名所引起的不
幸后果会小得多。
爱玛?米考伯
“你觉得那信怎么样?”特拉德尔在我把那信读了两遍后看着我问道。
“你觉得那一封又怎么样?”我问道,因为我见他依然皱着眉头在读。
“我觉得,把这两封信合起来看,”特拉德尔说道,“比起米考伯夫妇平日信中写的更
要有意义――可我不知道是什么。这两封信都写得很诚恳,我相信,是没有串通后才写的。
可怜的人!”他是指米考伯太太的信而言。于是我们肩并肩站在那里把这两封信做比较;
“无论怎样,给她写封信会于她好,还告诉她,我们一定去看米考伯先生。”
我对这意见大为赞同,因为这时我感到自责――我对她前一封信太不重视了。她的前一
封信曾使我在收信当时想过很多,正如前面说过的那样。可是,当时我自己的事太多,加上
和那一家人相处的经验和又没听到更多消息,我就把这事渐渐抛开了。我过去也常想到米考
伯一家,但主要是猜想他们在坎特伯雷又欠下了什么样的金钱债务,回想米考伯先生成了尤
来亚?希普的文书时见到我怎么窘。
不管怎么说,我当时就用我们两个人的名义给米考伯太太写了一封安慰的信,并由我们
两人签名。当我们步行去城里寄信时,特拉德尔和我进行了长时期的讨论,还做了种种揣
测,这里就不再多说了。那天下午,我们还请我姨奶奶参加我们的讨论;不过,我们唯一的
结论是:我们必须按时赴米考伯先生之约。
我们到达时比约定的时间还早一刻钟,而米考伯先生已在那里了。他抱着双臂面壁而
立,神色颇伤感地看着墙头的大铁钉,仿佛它们是他年轻时被当作蔽隐之处的树枝。
我们招呼他时,他态度更加狼狈,也比过去更少绅士风度了。为了这次旅行,他没穿那
法律家的黑衣,而是穿了他的旧紧身外套和紧身裤,但旧时风度已不多存了。我们和他谈话
时,他渐渐恢复了常态;可是他的眼镜挂在那里似乎不那么自在,他的硬领虽然仍和旧时一
样高,也有点点软沓沓地垂下来了。
“二位先生,”米考伯先生闲聊了几句后说道:“你们是患难中的朋友,也是真正的朋
友,请允许我敬问?现?在的科波菲尔夫人和?将?来的特拉德尔夫人(这就是说,我的朋
友特拉德尔先生似乎还没和他所爱的人儿作同甘共苦的结合)**安康。”
我们对他的客气表示感谢,也做了合体的回答。然后,他指着墙开始说道:“请相信
我,二位先生,”我便对这种客气的称呼表示反对,请他像过去那样和我们交谈。
“我亲爱的科波菲尔,”他握着我的手答道,“你的诚恳征服了我。对于一度被称为人
的圣堂的残片――如果我可以这么说我自己――给予这种礼待,表明一颗归荣耀于我们共同
天性的心。我要说,我又见到我度过我一生最快乐的时日的安静地方。”
“我相信,那是因为有米考伯太太,”我说道,“我希望她平安?”
“谢谢你,”听到我这话米考伯先生的脸色便暗了下来,“她还一般。喏,”米考伯先
生伤感地点点头说道,“就是这个监狱了!在这里,多年来第一次听不到聒噪不舍的逼债
声,在这里,不会有债主来敲门,这里也不需要应付诉讼,续行监禁通知不过从门口投进来
就是了!二位,”米考伯先生说道,“当操场的石头地面上映出墙头铁钉影子时,我曾看到
我的孩子们躲开黑影的点点线线从那交错纵横的影子里穿过。我熟悉那里的每一块石头。如
果我显得软弱,你们一定知道应该原谅我。”
“从那以后,我们都有了变化,米考伯先生。”我说道。
“科波菲尔先生,”米考伯先生伤心地说道,“我住在那个避难所时,我还可以正视我
的同类,如果他冒犯了我,我可以朝他头打过去。现在,我和我的同类不再保持这种光荣关
系了。”
米考伯先生怏怏地转过身来背对监狱的墙,他挽起我伸向他的胳膊,又挽起特拉德尔在
另一侧伸向他的胳膊,由我们相伴走开。
“在往坟墓走去的旅途上,”米考伯先生恋恋不舍地回顾道,“有一些里程碑;若不是
处心不正,一个人怎么也不愿跨过去。那个监狱在我多坎坷的生涯中就是那样的。”
“哦,你的精神不怎么好呢,米考伯先生。”特拉德尔说道。
“是的,先生。”米考伯先生说道。
“我希望,”特拉德尔说道,“这不是由于你对法律怀着憎恶――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
律师呀,你知道。”
米考伯先生没有做任何回答。
“我的朋友希普好吗,米考伯先生?”我在一番沉默后说道。
“我亲爱的科波菲尔,”米考伯先生一下变得紧张起来,脸色苍白地说道,“如果你把
我的雇主当作你的朋友来问候,我对此感到遗憾;如果你把他看作我的朋友来问候,我予以
嘲笑。无论你以什么身份问候我的雇主,我请你原谅,我的回答只会是――不管他的健康怎
么样,他的相貌狡猾,且不说是凶恶狠毒了。请允许我以贫贱之身谢绝谈论在我的职业中逼
我于绝境的这一话题。”
我为无心触及使他这么激动的问题表示歉意。“我可以,”我说道,“避免再犯以前的
错。问问我的老朋友威克费尔德先生和小姐好吗?”
“威克费尔德小姐一直是一个典范,”米考伯先生的脸色这时转红了说道,“她是光明
的化身。我亲爱的科波菲尔,她是那悲惨生活中唯一的灿烂星光。由于我对那年轻小姐的尊
敬,对她品格的赞美,因为她的慈爱、忠实和善良我对她的忠心――”米考伯先生说道,
“把我带到一个僻静地方去吧,因为,说实话,在目前这种精神状态下,我受不了这个!”
我们把他扶到一条很窄的胡同里,他拿出小手帕,背朝墙站着。如果我也像特拉德尔那
么仔细打量他,他准会不欢迎我们的陪伴了。
“这是我的命运”,米考伯先生不加掩饰地呜咽道――但他就是呜咽时也还保持了几分
旧日的上流风度――“这是我的命运,二位,我们天性中比较美好的那部分感情成为我的惩
罚。对威克费尔德小姐的敬意是我胸中的利箭。请你们扔下我,任我去流浪吧。害虫将加倍
地快来结束我了。”
我们并没听从他的要求而是一直陪着他。后来,他收起小手帕,拉起硬领,为了不让路
人注意,他又歪戴着帽哼起小曲。这时,一直担心他会出意外的我建议道,如果他肯坐车去
海盖特,我一定会非常高兴把他介绍给我的姨奶奶,而且他能在那里过夜。
“你可以为我们配一杯你一向长于配制的潘趣酒,米考伯先生,”我说道,“在回忆比
较愉快的往事中忘掉你的心事。”
“二位,”米考伯先生答道,“你们愿意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我是海面上一根草,任
大象儿把我吹向四方――对不起,我应当说任天气。”
我们又臂挽臂走去,发现刚好赶上要动身的马车。我们一路平安地到了海盖特。我心里
很不安,也忐忑,不知说什么才好,或做什么才好――特拉德尔显然也是这样。米考伯先生
基本上愁云未开。他也偶然试着哼小曲来振作一下,但他那帽子歪的程度、硬领一直扯到眼
睛的模样,只能使他的悲戚更动人。
由于朵拉生着病,我们就没进我家而去了我姨奶奶家。一听到通报,我姨奶奶就迎了出
来,非常诚恳地接待米考伯先生。米考伯先生吻过她的手,又退到窗边,掏出小手巾和自己
的心情挣扎。
狄克先生在家。他生来就极其同情看上去不快活的人,也能马上发现那种人,所以在5
分钟里他和米考伯先生握手次数不下于六次。这在患难中的米考伯先生看来实在是令人感动
的热情,而且还出自一个素昧平生的人。每次握手时,米考伯先生都只能说:“我亲爱的先
生,你征服了我!”这话又大大鼓励了狄克先生,他便怀着更大的勇气再次去握手。
“这位先生的好意,”米考伯先生对我姨奶奶说道,“如果你允许,小姐,让我从比较
粗俗的国民竞技语汇中取一个比喻――把我击得一塌胡涂了。对于一个在烦恼和不安压力下
挣扎的人来说,我向你担保,这是一种难以消受的盛情呀!”
“我的朋友狄克先生不是一个寻常人,”我姨奶奶骄傲地答道。
“我相信这话,”米考伯先生说道,“我亲爱的先生!”因为狄克先生又在和他握手;
“我深深领会了你的好意!”
“你觉得怎样呀?”狄克先生面露不安地问道。
“没什么,我亲爱的先生。”米考伯先生叹口气答道。
“你应当提起精神来,”狄克先生说道,“尽可能让自己自在些呀。”
这几句友好的话,加上狄克先生再一次的握手,使米考伯先生十分感动。“在人生变幻
无常的万花筒中,”他说道,“我曾遇到过绿洲,但从没遇到过现在这块这么绿这么美好的
一片呢!”
如果是在别的时候,这种情形会让我开心;可现在我觉得我们都很拘紧,都不自在。米
考伯先生显然处于想说点什么又想什么也不说为好的两种意向间犹疑不定。特拉德尔坐在椅
子上,瞪着眼,头发更竖得直了,眼光在地面和米考伯先生两者之间轮流巡视,没有半点想
说什么的意思。而姨奶奶呢,虽然我看到她锐利的目光很认真地盯着她的新客人,却比我们
都更镇静;因为她硬让他交谈,而不管他是否愿意都得说话。
“你是我侄孙的老资格朋友了,米考伯先生,”姨奶奶说道,“我早盼着有机会结识你
了。”
“小姐,”米考伯先生答道,“我真希望我早就有机会认识你了。我从前可不是你现在
看到的这么一个没体面的人哪。”
“我希望米考伯太太和你的家属都平安,先生。”我姨奶奶说道。
米考伯先生低下了头。“小姐,他们只是,”他停了一下,最后像豁出去一样地说,
“像贫困无助的人所希望的那样平安。”
“天哪,先生!”姨奶奶用她那种生硬态度叫道,“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我们的生计,小姐,”米考伯先生答道,“危如累卵,我的雇主――”
说到这儿,米考伯先生像故意和人为难一样打住,开始剥柠檬皮。那些柠檬以及一切供
他调潘趣酒的原料,都是由我指挥着陈列在他面前的。
“你的雇主,你知道,”狄克先生像一个温柔的提词人那样碰碰他胳膊说道。
“我的好先生,”米考伯先生继续说道,“你提醒了我。我很感激你。”他们又握了回
手。“我的东家,小姐――希普先生――曾对我说,如果他不雇我,我大概要做一个跑江湖
卖艺的人,去吞刀、吞火;如果不这样,我还可以教我的孩子扭屈肢体来表演挣钱,而米考
伯太太可以拉手风琴助兴呢。”
米考伯先生信手挥了挥他手里的刀,以示他活着就决不做这种事。然后,他又带着绝望
的神气继续剥柠檬皮了。
姨奶奶把胳膊肘支在她常坐在其侧的小圆桌上,注意地看他。虽然我不愿意有人去引诱
他讲他本不愿讲的话,可是我还是会在这时接过他的话讲下去的,要不是我这时看到他的动
作很奇怪――他把柠檬皮放在罐里,把糖放到鼻烟盘里,把酒精倒进空瓶里,还很坚定地想
从蜡烛盘中倒出水,这些都是他让人注意的举止。我知道大事不妙,果然如此――他把所有
的杯盘叮叮当当放到一起,从椅子上站起来,拉出那条小手帕就大放悲声。
“我亲爱的科波菲尔先生”,米考伯先生用小手巾捂着脸说道,“这是一切工作中需要
静心和尊严才能干的一项,我干不下去了。这是不可能的了。”
“米考伯先生,”我说道,“这到底是为什么?请说出来吧。
这儿没有外人哪。”
“没有外人,先生!”米考伯先生重复道,于是他压在心底的秘密全讲出来了。“天
哪,正因为没有外人,我心情才如此。这是为什么。先生们?为什么不是因为这样呢?就因
为那恶棍,就因为卑鄙;就因为欺骗、伪诈、阴谋;这一切坏东西的名字就是――希普!”
姨奶奶拍拍手,我们大家都像着了魔一样地站了起来。
“斗争已结束了!”米考伯先生说道,一面激动地大幅度挥动那方小手帕,时时舞动双
臂好像在难以想象的困难下游泳一样。“我再也不要过那种生活了。我是个可怜人,被剥夺
了一切可以使生活像生活的东西。过去,我受到那恶魔的钳制。把我的妻子还给我,把我的
家人还给我,用米考伯来代替现在这个脚穿靴子走来走去的小可怜虫,就是明天去吞刀,我
也干,我心甘情愿那么干!”
我从没见过这么激动的人。我想使他平静下来,以便大家能好好商量一下;可他越来越
亢奋,根本听不进一句话。
“在我把那――哦――可恶的毒蛇――?希?普――炸碎之前”,米考伯先生像挣扎在
冷水中一样喘着气、叫着、呜咽着,“我不和任何人握手!在我把――哦――把维苏威火山
――移到那可耻的恶棍――?希?普头上――啊――并引爆前,我不接受任何人的款待!在
我把那――那个骗子――说谎话的――?希?普的眼睛――哦――闷瞎之前,尊府的――哦
――饮食,特别是潘趣酒――哦――我一口也吞不下!在我把那――那个最大的伪君子和骗
子――和作伪证的人――?希?普――压成――哦――肉眼看不见的原子前――我――哦―
―不要再认识任何人――也决不――哦――决不说一句话!”
我真有些怕米考伯先生会当场死掉。他那么费力地说出那些含混的句子时,样子真可
怕。后来,他倒到椅子上,大汗淋漓,瞪着我们瞧,脸上出现了各种不正常的颜色,喉结不
断起伏,好像要挤上前额一样。他看上去真像要死了。我想去救助他,可他对我摆摆手,也
仍不愿听进一句话。
“不,科波菲尔!――在威克费尔德小姐――哦――从那坏透顶的恶棍――?希?普那
里――受的损害得以赔偿之前――没什么可说!绝对保密――哦――别告诉――哦,任何人
――下星期的今天――哦――还有很友好的先生们――都去坎特伯雷旅店――哦――米考伯
太太和我――都会在那里――一起唱《友谊地久天长》――还要――哦――揭穿那令人发指
的恶棍――?希?普!不说什么了――哦――也不想听什么劝告――马上就走――去追踪那
该死的不忠不义之人――?希?普――不能――哦――再见朋友!”
说完这些后,米考伯先生就冲出了屋,让我们忐忑不安又心怀希望并惊奇万分,结果我
们的心情也不比他的好什么。不过,就是在那种状态下,他仍压不住他写信的嗜好;因为当
我们还十分忐忑却又怀着希望并惊奇万分时,附近一家酒店给我送来下面这封如田园诗一样
美的短信,这是他专门去那酒店写的:
绝密!
我亲爱的先生:
我恳求你,代我向你的姨祖致歉,因为我刚才失态而无礼了。由于我内心激战,有如蒸
腾之火山久抑未发,今日一发便不可遏止,此情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我曾约各位于下星期此日之上午会于坎特伯雷社交之处。我夫妇将与各位齐唱特威德这
位流芳百世的收税人之著名歌曲①亦在该处。恐怕当时未能言明,特补嘱之。 ①系《友谊地久天长》。
行看我已履尽我责,也将我过尽补(因唯有补过后我方有面目向世人),我将不复于人
世。但求我之骸骨能被置于世人归宿之地,其碑但求刻以:
小村中已故老前辈何其多,
人人各自安眠在小小墓穴中①
――然后刻以贱名。
威尔金?米考伯 ①这是英国18世纪诗人ThomaoGray作的挽歌中诗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