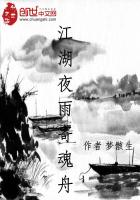雍熙二年五月
.
林色向晚,知客僧说,还有一柱香关门,礼佛求愿是来不及的。
「先前来了些女客。」
他合十略弯腰:「施主随我来。」
山门由天王殿充作,迎面是弥勒佛笑脸,两侧天王持器耀武。
侧口有张桌,老和尚卖香丸、打瞌睡,有人来了问一声:「买香啊。」
屋檐顺下的雨,宽厚地打响阶前,珠复一珠,催人困倦。
眼睛有点胀,囫囵着懒意没有理睬。
南朝佛家盛极一时,寺庙多为敕造,墙垣殿院,通刷黄色。
灰天濛濛,格外地近地,大雄宝殿被层云压住,使人同病相怜地气闷。
绕过去走了点泥路,望见一片僧房。有一间门口,偶有个女客走出巡视。
「能把观音扔在外面么?」
镜子说的是大雄宝殿后头一尊观音巨像,脚下石莲绽放。甚么天王罗汉,都能在庙里,把观音大士吹风淋雨。
我忽生个念头,却怕知客僧取笑,没有说:在屋里的尘埃落满,在外的反而干净。
但他会错意,或者听岔,答道:
「那是对观音菩萨的不敬,施主不要效仿。碰到了,就捡回来擦干净,用干净布包好,放在家里干净的地方,是有福报的。阿弥陀佛。」
那紧张样儿,看得我们忍俊不禁。
来到那间房,是歇脚等候的憩所。芍花门众人散坐,只站着个蟋蟀眉。
知客僧:「这两位是女施主的客人么?」
「我找曹姨。」不等质问,自报来意。
唐姑娘迟疑了一下,僧人沉头行礼便走。
.
外面传来小鼓声,众僧唱偈,虽在远方,嗡嗡震耳,一派肃穆。
「唵伽啰帝耶莎婆诃。」
「唵伽啰帝耶莎婆诃。」
「唵伽啰帝耶莎婆诃………」
「你们认得她?有何贵干?」圆脸少妇没好气,她盘腿坐着,凶目侵人。
钟声响起:「上祝诸佛菩萨光照乾坤,」
「萍水相逢,都是些小事。」
「下资法界众生同归一乘。三界四生之内各免轮回,九幽十类之中悉离苦海………」
「去罢。」她迟疑了良久,钟又敲了两下,余音里挥挥手,唐姑娘便走过来。
往里走,她推开小门便走了,留我们自行解释。
斗室里曹姨正闭目冥想,闻声开眼,见了我,礼节性地微笑。
等我关上门:「你是太白山陈家的孩子罢?」
她大约四十不足,但声音还挺清亮,在钟声、偈唱里分明。这个角度看,脸也不是很方。
「前辈见过我。」
「这剑法我知道。」
「那一定是见过家父。」
「乖乖,坐过来。」
手腕被拉了一下,摆到她面前。
我走过去,跪坐相对,未听见回答。也许是很轻地点过头,而我没看到。
「曹姨在芍花门有许多年了罢?」八成与父亲故交,便改了称呼。
「我从外地来,带艺投师,算今十几年了。」
「晚辈想打听一个人,或许数年前,是贵门的弟子。」
「芍花门中都是妇人家。」
「也许不涉私隐。」
「必无一字可说。」
她这般决绝,怕惹烦了,不合啰嗦,又怀疑真相已近,功亏一篑:「曹姨………」
「你要问谁,还是那个姐姐?跟我去漕帮、江帮,消息灵通着呢,不信没个讯。」
镜子耐不住沉闷,叫了起来。她站在门口,居高临下,因显得颇不客气。
钟声阵阵,偈唱未已。
「这是小雁子?」
「不,是伯舅家的。曹姨,我过天王殿,回见韦陀杵着地,此寺不留外人,何况女客。」
把话题带开,舒缓尴尬。
「韦陀杵着地,不接待的是云游僧人。」云游者身无分文,是故不予吃住。
「芍花门要在此过夜,应该出了不少钱,却是为了甚么?」
「不该问的,不要问。」
无心之问,却惹得她脸露不快。毕竟,无端何必借宿,多是不好告人的机宜。
「天色晚了,赶紧回家罢。」镜子劝道。
「天黑小心点。」曹姨也催促。
是我失言犯了忌讳,惹她在撵客,颇多懊悔,可是还有些不甘,只为心里一个结。
「大前年……」啊,万一佳儿与她们没有了断,不敢直问,「贵门可曾走失过年轻弟子?」
她抬手向旁,虚抖几下。
镜子侧边的木墙上,有一个简笔但深浅有致的芍药图案。
这时门上敲了两下:「黑三娘来了。」
本以为遇了父亲旧友,真以为好说话,那想受此警告,自不敢再多嘴:「如此,叨扰了。」
镜子打开门,我也走出去,雨声噼啪,看见个熟面孔———邵伯镇的女庄主。她已换了行头,身后好些女侍,个擎纸伞,最靠近的抹了薄面纱。
她见着我:「你是小……他。」
仓促记不起名字,就用小他代指。
不知如何回答,轻点头。
她关照侍从留步,在蟋蟀眉指引下进了斗室。
大房宽敞,也坐不下三十个,黑三娘的随从,有几个站在屋门口,雨脚如麻。
「你认得三娘。」薄纱下的脸庞若隐若现,俏眉俊眼,留无限遐思。
高挑白皙,不施粉黛,自生雍荣,隔着面纱,便使我相信:说是平生所见最靓丽,也毫不为过。
情人眼里出西施———这很冤枉,世间从未有动情先于色者。
「昨晚在她庄子上过了一宿。诶,她姓黑么?」
毕竟肤色并不深,也没见穿过黑衣。
「江湖上起的诨名:孝义黑三娘,说的是心黑、手段黑。」
听得出,三娘对这评价喜爱有加。
镜子:「城门关了。」
外公家在城东厢,顶多绕点路,但叔公家在城墙里。本来说好,晚上镜子去叔公家住的。
「雨停了你就回家,我还有事。」
心里还有个期待:跟曹姨问不到的事,黑三娘或许肯说。
忽而听见斗室内争吵声,黑三娘推门而出,怒道:「还有甚么好谈!」
美侍从迎了上去。
三娘:「都是群混帐。」
我看她乘怒,又不敢问了,但她看了我一眼,强堆笑容:「想起来了,你叫小陈。小佳呢?」
「走失了。我也正想问三娘,她的事。」
.
寺里给众女客早就安排了过夜的宿室,黑三娘的要沿着长廊绕半圈,隔了一块草地,廊下与中间有几株矮树。
她带我到了房间,美侍从和镜子在长廊说话。
「五年前,」三娘关上门,「有一对母女来到芍花门,那丫头就叫小佳。」
就是佳儿么?
「大前年,芍花门去淮北办事,屡遭恶贼突袭,据报母女都死了。
但是,焉有这么像的人……连名字都……」
三娘目光移向窗外,「挑她说话,又好像甚么也不知道,不肯相认。」
「一定是不愿再见你们,她才故意走失了。」
赖到她们头上,才能彻底的心安。
黑三娘没有回答,我满足地推开门,镜子还在闲扯着。
她跟美侍从说,我是从太白山来的,秦岭是何等巍峨,蜀冈这样的,只能算土丘。
但瞥见我,就又不说好话了:
「但那有甚么好?出行累死啦。」
「用不着天天上下。除了过节罢……」平时就待山上。
扶着门框,有脱罪的一时悠暇。
「那更不好了。整日待山上憋坏啦。」
「你常出去玩么?」反倒是我羡慕了。
「金陵、苏、扬、润,是常走的;山阴、杭州,也能。」
「爹娘可放心?」
「有甚么不放心?」
她不明白我的奇惑,但不消追问,我已了然:
江淮的山,少且低矮,难以成为剪径强贼的藏身之所。
何况,富庶的地方,都忙着赚钱,武风自然不振。
有茅山派在后,镜子言行无忌,已然习惯。
.
叠声尖叫,回头见黑三娘猛窜身跃窗而出。
紧随其后,青草灌木,晃眼在后,落足憩屋。
斗室门半开,数女围立,震恐无状:「她这是死了罢!」
黑三娘推开她们,跟过去,只见直脚倒在地,无疑是曹姨。
挪一步探身看去,喉头鲜血刺目,犹在一鼓一鼓地涌出。
「是匕首。」
三娘扒弄了一下尸体,站起身,手上沾满血。听到匕首,心里害怕,怕是佳儿做的。
「明明是剑伤。」有人议论道。
「少装模作样,不是你,还是谁!」蟋蟀眉按剑怒喝,直视三娘,「你早就………」
「不可能。三娘就和我在一起。」
她没有听从我的证言:「曹姨说过,若生不测,定是你干的。」
但这不足为据,语气自然地无力。
三娘冷笑,两下里磨鞘响,蔑然一笑:剑身清白。
众女与僧陆续到场,惊呼、痛哭,议论、念经,喃喃一团。
三娘同蟋蟀眉清点了人数,都来齐了:「劳驾小师傅,端一盆水来。」
她将剑头浸没水中,而后插在地上,又把鞘按入盆里,舀水竖起又倒出。
镜子与我随着众人依次照做,水清如故。
「曹姨起身开门,未半为人平刺入喉未穿。匕首多用以横切,此创口狭窄,确似剑伤。然而,扬手挺剑,通常刺在胸腹;高刺咽喉,会向上斜贯。不信,自来看罢。」
众人剑均不曾沾血,自无疑问。
「本门中,能以匕首杀曹姨的,有谁?」
「是外人干的罢。」有人说道。
「无量无数无边众生,佛皆使入无余涅槃灭度之。见、思二惑与所受五众之身,俱得灭尽,无有遗余,是名无余涅槃。」
住持年事已高,左手拄着禅杖,右手由个小沙弥搀着,不知何时到的,微微摇头,晃晃走上前来。
这些颠三倒四的东西,听着头疼。想入用心处,便听不到聒噪。
曹姨隔空按了手印
———如果嗤嗤戳几个洞,那是半吊子。虽以凌空指力,相隔却不出一步,吓不住我。
但花瓣深深浅浅、各具层次,便很吃本领。
她是不常见的高人了,练功吃了多少苦,竟死得这般轻巧。
幸而他好好说话了:「三年前,曹施主杀白施主,便在此屋。转今命丧于此,阿弥陀佛。」
世上真有鬼魂么?
三年前……那个小佳……暗暗将她们联系起来,却想不出结果。
万一是佳儿杀的,她就在附近;而我,定不可教人察觉真相,就算是要让谁蒙冤,也决不能牵出她。
「唵,钵啰末邻陀宁,娑婆诃。」
猛觉住持已在房中,我走上前去,他正闭目、含胸念忏,手势奇怪、交叉。
脚下尸体,腥得骇人。
三娘说得对,剑术通常刺在胸腹,或撩臂点腿。
陈家有一招『拗步斫龙头』,横斩颈项,算很接近了,但也要先扫伤敌腕,不然易回避、挑开。有这样本领的,大底并不会强求直刺封喉这样华而不实的招式。
三娘确信芍花门无人能做到,那便是外人所为,或已远去,又或许还藏在某处。
她委托僧人寺中巡视,看管尸体,吩咐各自回屋,不许走动,捱过这晚。
曹姨一死,此处无人与她地位相埓,即使不归管束,也都遵照。
她说:「夜路危险,你们也留下。」
事发之时,我正和她说话,镜子同那美侍从在一块,并无嫌疑,应是真心顾虑安危。
长廊上我还在想,如果让我来,会怎么杀。
曹姨来寺里,与三娘约见,是早有的打算,可以查知。
但她身边常有侍从,本该无从下手。只有内贼才知道,她会独留斗室罢!
且她既说,不测必为三娘害,为何还不严加戒备?
「以匕首……近身点刺,颈血涌出,必会溅在身上,何况……会将尸体迎面带倒,前仆于地。除非拔刃时扶住、推一下,便不免喷了一脸。」
镜子闲不住,这浑水也要再搅,可听下来,竟也有些疑虑。
我们赶来时,颈血还在涌。所以曹姨刚倒下,便被发现了,仓促之间,凶手或许能脱身,但说弄干净满身的血迹,混回人群,是无稽之谈。
「三娘摸过创口,边缘可有些豁口?」
黑三娘否认了。
「短尖扎喉,剑身在外,长长引出,即使手上撇动,也顶多略微压大一侧伤口;匕首短小,在血肉间夹得紧,即使不去刻意摇松,也会自然地抖出豁口。」
没有练过匕首,想象了一下,好像有些道理,又不能确定。
三娘推开门,让镜子和我待着。
「三年前,是怎么回事?」
「怎么,你也信是鬼魂?」
也不好说完全不信,但世上事多数还是人为。
「曹姐来芍花门十余年,有功有劳。但她本是别派弟子,改换门庭,终究低人一等。那时候的掌门姓白,算是我们的小师叔,其实……也算不上,她只是个习武不成器,退而管生意的,和我们都不熟。放别的门派,怎么也不会接任掌门罢。可芍花门最重利字,正是要吃断生意的时节,故而由她掌管。三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