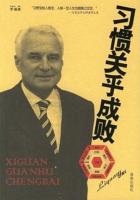幽都的夜景极是好看,即便是在较为落后的南城,依旧有着其他城邑难得的都城气魄。各家各户但凡需要挂上灯笼的地方,总会亮着一星半点儿属于它的光彩。
曾有诗人在用“勒马刀兵,不胜娇羞”这样的诗句来形容幽都的夜景,算得上是对幽都夜景最好的诠释。
卓煜一个人抱剑而行,确是在欣赏这景色的壮阔优美。与临沧不同,与云夔不同,与整个天下都不同。
哪家屋檐飞起挂上月半流辉,哪处灯火娇媚顾盼女子纤柔,哪地声色欢愉是处酒肉成林,哪里窗扉紧掩是有女子针纺。
这般行走在幽都的街道,卓煜没有所谓的疲倦,他兴致很高,甚而至于连他自己都不曾发现。
现在,他是十八岁的一品武者,现在,他已然脱离了敌人的追杀,而不久,他将登上龙台,亦或者,迈步龙台。他的梦啊,他的敌人啊,他的这漫长一生的过往匆匆啊……
卓煜喜欢在繁华的地带品味那种一个人行走的孤单,那种感觉很奇妙。就像是那时在洱海中面对碧海苍穹一般,渺小的人,广阔的天海,心境能够在这一瞬间舒缓,即便是,在面临生死的时候。
从洱海归来之后卓煜甚至不知道他的心境较之从前有了提升,但卓煜能够感觉到,他的实力在不断进步。
对于一个一品境界的武者来讲,再进一步,或许就是半虚乃至虚境的境界,然而卓煜没有触碰到那层虚境的壁垒,只是感受到体内气息的强大,尤其是,流溢在经络之中的元力更显醇厚。仿佛经脉本身,就在不断被那元力冲刷拓宽。
这种感觉如同而今正在漫步观赏夜景的感觉异样,都很美妙。
卓煜漫步行走的这条街道是真正的红粉香销之地,是整个幽都最为繁华的几处商肆集中的地段。
最好的酒楼,最红的歌舫,最阔的赌场,最大的缎庄。
这里比之卓煜先前所去的珍古街,更显人气,更显阔气。当然,这里的歌舫是清歌舫,是不做那些皮肉生意的。因而进这些歌舫的,不但有男子,还有一些女子家眷。
亦或者说,而今即将参加朝试的一些清贵公子,都会来到这里,听上一曲清音,酌上两盏杯酒。或许会意外结识到一些朝中大臣,又或者,结交到一些豪阀公子。总而言之,临近朝试这段时间,这里的清歌舫,唱的的状元及第的清歌,这里的酒楼,宴的是同窗高中的酒席。
卓煜倒是没有抱着这样的打算,因为他走的不是文试,而是武试。文试所倚靠的外力太多,他孤单一人,又怎可能借此完成夙愿。
就纯粹是想听听曲子,听一听佳人浅笑的清歌。正巧身上又有着不菲的钱财,他一个人若是省吃俭用怕是一辈子也花不完,因而卓煜头颅微扬,将他那张俊秀面庞对与星辉,抱着那柄剑,循着依稀所听清歌最妙处而去。
是处楼台,谪玉轩。
卓煜不禁莞尔,想着这天涯何处不曾见小,哪里都能遇见曾今与往昔岁月中记忆的点滴。他不禁想起云夔那个衣衫曼妙舞姿的司徒莞秋,想起那个一指琴弦将他拨进琴道的芸娘,想起了初识因不忿弹奏的《拓枝》,本以为三年打铁能够沉下的心境,却是在荒洲之后才真正沉下。
当初在云夔,即便他再如何努力,再如何勤奋执着,再如何抱有复仇的意志,其实都不过是一种单纯到绝望的希望罢了。三年时间沉浸在武道与打铁之中,原以为自己这样的人即便再愚笨,只要稍一用心,就可以触碰到武道志高的境界,到时一剑横秋,斩断那些缠绕的仇恨,却不曾想,十七岁依旧只有五品境界。十七岁五品的武者虽然不多,但对整个云洲而言,其实也见得平常。因而那时的复仇,不过是一种执念,只有现在,他才真真切切看得到复仇的曙光。
他已经触碰到真正帝雀的力量,他已然跨入武道一品的境界。他能够从荒洲决然的奔袭杀戮之中冲杀而出,因而卓煜有理由相信,他能够成为进入郢都复仇的那人。
心境上的提升使得此刻的卓煜看待一年前那些所谓的意气之争更加显得幼稚,因而卓煜笑了笑,将那些先前一切存于脑海中的想法摒去,他只是想要听一曲清歌,那便就是去听歌而已。
哪管他洪水滔天舞不出沧浪雄姿,哪管他白浪咽歌道不尽江山姽婳。我一脚走进,不过是放下了一些杀伐之后的疲倦,放下了一些辗转奔波的劳累。得一释怀,得一愉悦,如此而已。
今夜的谪玉轩,唱的不是那曲临沧江畔的拓枝;也并非曾经大齐流传甚广的《鹤冲天》。这几日往复唱的曲子,决计少不了那一声《蟾宫桂》。
那一身少年装郎,玉带粉旁,金銮殿上,未央宫里,唱给那万世皇家,一身坦荡荡磊落恰若蟾宫,仙子折桂……
这是一曲完全没有章法可寻,完全听不出曲子何意的唱曲,然而却最是能够表现那时春风得意,马蹄乱疾的恣肆张狂。因而这曲蟾宫桂,唱的真是那些士子高中的张狂。
为何会如此,不外乎燕国朝试的文试的确是天下间最为诡异的一场考试,那些五关六将大步流星而来的无数士子,原以为得了天下一石才气中的七八斗还多,却最终饮恨所谓的一张试卷,零星文字,的确是让人抓狂入魔近乎想死。
只是朝试既然还没有开始,那先前的放肆与舒意假做张狂便只得压抑,然而考前的紧张定然不能免去,那就只有到这清歌曼舞的楼台佳处听一曲清音,换一份心情。
当然,而今还能够淡定若斯到这里来的,除了自负才华之人,多是世家富贵之辈。反正历年朝试全无章法可循,何必枯坐屋中看那所谓文章,且恁偎红翠,风流事,平生所畅而已。
池台之上一曲蟾宫桂还未唱罢,一群衣着讲究,异常华贵的世家公子款步走了进来。
未见其人装貌若何,已闻环佩振振之音。
卓煜坐在的位置是一处较远的僻静所在,背身对着谪玉轩粉楼雕门,盘腿坐榻,桌案上摆了几碟价格不菲的佐酒小菜,喝的是燕北醽醁,听的是谪玉轩清倌儿唱的曲子,自然一番享受不说。
那些随风而进的世家公子,管你容貌家世天赋若何,也懒得前去理会。
那些人自然进了所谓的雅阁,听音佐酒,又有美相携,自也是十分快意。
池台之中歌舞轮转,酒桌之上杯盏迭换,卓煜虽则只是一个人默默饮酒,却不知楼上阁台,已经有人瞧上了他。
“夕玥妹妹,在望些什么呢?舞绝的曼舞怕是还要等些时候。”说话的那人是燕阙侯裴矩的幼子裴渡,正是今年参加朝试文试的士子。裴渡在武道修为上的天赋远没有其在文道阵法一途上的天赋高,因而裴家对他的关注往往要高于裴矩的长子,朝试当年二甲第五的武道天才裴炎。
阵法一途极其艰难晦涩,难以揣摩,一般人终其一生也无法入道,而裴渡却是在十岁那年便已然入了阵法一道,在整个云洲来讲,也是排得上号的少年天才。除却阵法,裴渡本身武道修为也不差,未满二十的武道五品,加之文道兵法之上也颇多感悟,因而裴渡自有一番张狂。
澹台夕玥是裴渡的表妹,过了年没多久就到了幽都。原先听人说这个表妹机灵古怪,很是俏皮可爱,但真到见了本人,才觉得她温婉可人,娴淑静仪,加之容貌天成靓丽,形态娇小含羞,已然成为世家贵女圈子里手捧的人物。
裴昭渔送女儿到幽都,自然是为了太子妃人选的竞争。她自信凭借自己女儿的容貌加上裴家与澹台家的操作,定然能够有所作为。这种秘辛的事当然也就只有澹台家与裴家少数几个人知道,太子选妃当然还有一段时间,甚至说等上几年也未可知,然而燕国世家适龄的女儿,谁又不将这看作是维系家族关系与登跃龙台的一次机会呢。就连澹台夕玥自己,也默认了这样的安排。
澹台夕玥这般早来到幽都,其实就是为了寻觅机会,若是娴淑莞尔,秀外慧中的名声传到了宫里,也能为澹台夕玦竞选太子妃增加不少筹码。
当然,所谓的秀外慧中不可能仅仅只是待在屋中。更需要适时地表现出来,需要与幽都之中的世家嫡女们打成一片,或者说在世家公子中赢得名声。而作为原本在这个圈子里就混迹得不错的裴渡,自然就成了澹台夕玥的领路人。
裴渡还不曾知道澹台夕玥这事儿,因而看向澹台夕玥的眼神中不免流露出了一丝暧昧。
今夜这场宴却是为一位世家嫡女庆生提前组的局,说是提前,自然是因为庆生当天无法如此,因而那位贵女才会如此。
而来到谪玉轩,却是听闻最近几月,这里出了一位容颜绝丽的女舞,被幽都的歌舫红楼冠以舞绝之称,与幽都原有的歌绝,琴绝并称“三绝”。
心思本就玲珑剔透,又岂会不知道自家表哥心中那些想法,只是不愿理睬,于是愈发显得有些清高。
然而澹台夕玥的这种清高其实并不惹人厌烦,在一众女子看来这样的不争对她们来讲其实是最好的。况且对方又是七姓之中的嫡女,身份本就高贵,因而许多原本显得更为清高的女子也愿意攀折结交,就比如今日酒宴的那位贵女,而这,倒是澹台夕玥始料未及的。
“刚饮了几杯,有些乏了,就在这里看看歌舞,解解乏。”澹台夕玥的说辞显得有些牵强,然而裴渡却是欣然一笑,“那我陪夕玥妹妹在这儿坐会儿。”
澹台夕玥没再理会自家表哥,两人之间有种淡淡的静默,像是隔阂,却被裴渡理解为身旁那女子的温婉。有时候暧昧的产生往往来源于误会,而误会的本身就是一种单相思般的想当然耳。
杯中有酒,裴渡轻酌,不经意间将目光顺着澹台夕玥望着的方向看去,看到了一个男子的背影,一个修长巍峨,带有一丝荒客气息的男子的背影,却又在那份豪阔中流露出一种静淡的纤柔,很复杂的一种气息。而那男子的桌案上,放了一柄剑,被古朴的剑鞘收拢,却并未显出特别。
裴渡瞧见澹台夕玥望着那人的眼神越发奇怪,甚至铸剑带有一种回忆的依恋,不由蹙眉,却是没有说话。
此时珠帘轻挑,从中走来一位女子,那女子一身白衫,做男子打扮,腰间缠有青色玉带,玉带之上,珠坠轻摇,白皙脸颊之上透有醉酒微醺的粉色,很是诱人。
“夕玥妹妹怎的出来这般久?还有你,裴六,难不成外面的姑娘比我还好看?”那女子倒不是有些醉了,只是本身说话便如此大大咧咧。
“安曦公主是取笑裴渡的吗?说是公主都入不得裴渡双眼,那天下女子,渡还能瞧得上谁?”裴渡呵呵一笑,杯中酒尽。
那女子不是别人,正是燕皇慕容昌幼女,大燕九公主慕容安曦,母亲陈阀陈梦珂,领后宫六院。
“走,进去了,大伙儿还等着呢!”安曦说着将夕玥一拽,拉着就是往屋里走。
裴渡望了望方才夕玥盯着的那人,摇了摇头,许是随意看看吧,是自己多想了,随即举着酒杯,进了雅阁。
谪玉轩的熏香用的是碧落海的龙涎香,佐以珞珈山的桃泥,因而香中醉有桃花,花中略带碧水,让人痴醉。
“裴六,今日还未有尽兴,怎的就避战了?”席间一锦衣公子举着酒杯,对着裴渡笑骂道。
“谢本初,就冲你方才那句话,我自饮三杯。”说罢桌上酒来,也不推避,直接就喝了三杯,“但今个儿这酒,咱俩得说道说道,若是我饮一杯,你谢本初也得饮一杯,若是我饮一壶,你谢本初也得应战!”话音刚落,取过身旁紫色檀香镂刻青竹的酒案之上所陈列的玉贡花雕,揭开瓶封,仰头如垂虹倒吸,一饮而尽。
裴渡豪饮之时,满座欢声再起。
那被唤作谢本初的男子,乃是谢家子弟,同裴渡本就是穿着一个裤裆长大的发小,饮酒的本事自也不差,“好啊你个裴六,要本初大爷我今个儿在这儿出丑不是。我还真就不信了,就没一次喝过你的时候。”谢本初本来酒量不错,但比之裴渡,还是稍逊一筹,但今天饮的这玉贡花雕本身度数不高,就算多饮也不妨事。说着谢本初也是取来一壶花雕,对嘴就是尽饮。动作虽没有裴渡那般潇洒,酒可没少了半点。
谢本初的酒还没喝完,安曦一拍桌子,将腰间挂的那块儿内藏苍龙符文的佩玉往桌上一拍,也不怕摔碎,“好,本公主做庄,来看看今个儿谁先倒下,赢了的这块紫玉和田就归他了!”
和田玉,尤其还是紫玉,本身就珍贵异常,而内刻皇室苍龙符文,则更显珍贵。临战之时,怕是能挡虚境龙象全力一击也未可知。
然而这块玉对席间这些人来讲,倒也算不得太过稀罕。只是公主既然发话,那定然是要死磕到底了。尤其谢本初瞧见,竟像是打了鸡血一般,没等裴渡再喝,连饮三坛,不见醉色,竟是把裴六少,也给当场唬住了。
裴渡外表上虽然是个风度翩翩的世家公子,骨子里却带有三分所谓的纨绔无赖气息,当然,纨绔对的是圈子外的人,无赖却对着圈子里的人。
瞧见谢本初连干四坛,神色还算清醒,裴渡不由暗骂了一声,谢傻子,别因着公主在,就这样玩命啊,即便是玉贡花雕,喝多了,那也是会醉的。
裴渡张望了一下满座等着他饮酒的人群,嘿嘿一笑,“方才纯属玩笑,玩笑。”然后对着安曦说道,“你说是不?公主?玩笑!”说着摆摆手,将方才还握在手中的酒坛放下,又是嘿嘿一笑,自顾坐了下去。
就是澹台夕玥瞧见,也不由一笑。
裴渡心中一喜,为博美人一笑,他着也算是自掉身价了。
“诶!裴六,你小子怎的……”那句“怎的这般无赖”还未说出口,谪玉轩中,灯光变幻,丝竹骤停,然后池台之上,烟雾而起,女子红裙,款步而来,身后婢女娉婷,却非莺莺燕燕,而是白甲长缨,手持刀盾。
破阵乐舞!
琴音浅奏暂歇,胡笳铁筝,鼙鼓乍响,笙箫渐次而起。破阵乐舞,自然要配以破阵之乐,金鼓之声渲染,边城塞上,哪家少年骑马,持刀破阵。
破阵乐的关键不在于铁甲轻剑如何绚烂,而是那身红裙轻慢妖媚,而带泪雨的我见犹怜。无定河,将军杯酒,将士亡,不见红绸。
破阵乐初现之时,时人以其异于常有的铮铮杀伐之音而痴迷其中,而后一女子红裙醉舞,含泪悼亡,才真正赋予了而今破阵乐的灵魂。
无疑,那个最重要的红裙女舞便是安曦等人今日要来看的那人,舞绝——司徒莞秋。
至于先前谢本初想要说的话,自然被众人抛诸脑后,安曦拍了一下谢本初的脑袋,示意他安静,一个人轻蹑手足,来到月台,凭栏歇处,望着那裙红艳,显得有些痴迷。
众人自然紧随,只有谢本初觉得脑袋晕沉,没走出两步,瞧见一张椅子,兀自坐了下来,趴在桌上,蒙头大睡。玉贡花雕,哪是这样的牛饮法。
舞绝?究竟是谁才能够担得上这样的称谓,澹台夕玥先前听人说这名号,却是不曾知晓舞绝的名字就是司徒莞秋,舞绝的真人,便是云夔谪玉轩云夕夜那位艳惊四座的绝美女子。
因而当澹台夕玥随着众人望向楼下池台之时,愣了愣,然后像是陷入了某种回忆。
她将目光盯向先前那道背影,只是此刻谪玉轩内灯光昏暗,烟雾缭绕,瞧不清楚此时回头往舞的那人的容貌。
而卓煜,瞧见场中司徒莞秋之时,竟不知该说些什么。他闭上眼,想起了云夔,想起了自己住了四年的地方,想起了南十三巷的貉血与油梭面,和铜驼门外冬雪飘摇的景色。
然后卓煜睁开眼,静静地看着司徒莞秋,看着她的舞,就仅仅只是一种纯粹的欣赏。
难怪这几碟小菜就如此昂贵,原来是司徒的舞相伴,加了价码。
舞至一半,似乎失去了兴致,本身也就不是来看司徒莞秋的舞,因而卓煜起身,将青蛾剑一抱,朝门外走去。乘兴而来,败兴而归,何必言舞,何必看司徒。
人们都在看舞,因而注意到卓煜的就只有澹台夕玥一人而已。
瞧着卓煜打算离开,澹台夕玥似乎笃定了什么,慌忙转身,朝着楼下赶去。没有人看到此时身后,澹台夕玥已经下了楼,直到半晌之后,裴渡打算回眸给澹台夕玥一个明媚的笑颜,才发现她已经离开,而再往楼下一看,竟是瞧见澹台夕玥出了谪玉轩的门。
裴渡顾不得其他,也不说他本身对夕玥就有爱慕,单是他将夕玥带出来,就定然要负责她的安全。幽都之中,不长眼的二世祖很多,裴渡还真是怕有人对夕玥起了歹心。
谪玉轩外,卓煜抱着剑,东张西望,也不知是在瞧什么,但就是想要看一看而已。
他突然感觉到身后有人拍了自己一下,而且叫了他一声,“嗨,卓煜!”
难道是司徒莞秋瞧出他了?卓煜心中诧异,微微一愣,却是转身过去,望见的事一脸兴奋的澹台夕玥。
“卓煜,我就……”澹台夕玥突然住了口,原本的高兴骤然溜走,神情有些怏怏。
我就什么?我就知道是你?我就在这儿等你?还是……
他们认识不过几个月而已,也毕竟只是比陌生人好一些而已。然而澹台夕玦走后,澹台夕玥发现,这个世界,似乎对她来讲,都是陌生。连带着而今这偌大个幽都,也是如此,看不透的陌生。
这个身不由己的世界,真的好累。
“姑娘……”卓煜正打算开口,却被夕玥的声音止住。
“抱歉,我认错人了。”澹台夕玥微微一揖,“公子的背影和我一个朋友很像。”
“朋友……”像是在自言自语,又像是在询问什么。
澹台夕玥莞尔一笑,甚是妩媚,“嗯,很要好的一个朋友。”说着又是一揖,“叨扰公子了!”
在澹台夕玥打算离开的时候,身后传来裴渡的声音,“夕玥,怎么不说一声就出来了?”然后他将目光盯向卓煜,一个很俊美的男子,有着一种令人倾心的气质,他手中还抱有一剑,十分朴素的剑鞘。他跟夕玥究竟什么关系?裴渡心中竟生出了淡淡的敌意,“这位是?”
“认错了,以为是一位朋友。”澹台夕玥对着裴渡解释道,“先前抱歉啊,没跟大家说一声就出来了。”
澹台夕玥脸上先前流露而出的那种甜甜的笑容已经敛去,卓煜对着裴渡微微颔首,是要打算离去,去不曾想裴渡此时开口对他问道,“还未请教公子名姓?”
“楚歌,南楚的楚,清歌的歌。”卓煜的声音很好听,然而却已经不再是曾经的声音,对而今的他来讲,变一种声音,比改变身上的气息要容易许多。
裴渡保持着世家公子的风度,同样颔首道,“在下裴渡,先前舍妹多有唐突,还望楚兄莫怪。”
卓煜一笑,看了看而今澹台夕玥那张已经安静下来的面孔,同样一笑,“倒是没甚大碍。”说罢转身,阑珊灯火,抱剑而去。
今夕何夕?今夕非昨。只是当时,而今还有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