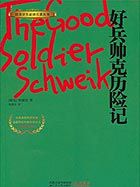这样,这顿饭的最深印象是我被芥末粉皮给辣得流眼泪。吃完饭出来,姜勤勤就笑开了:“这两天我一直委屈,没想到今天这么开心!”我抗议地说:“你这种开心不好,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别人的痛苦之上。”她边笑边为自己解脱:“你不知道,这是瑞五区公安局十几年的规矩了,给新人接风都要上一盘芥末粉皮的;而且所有的老同志都要吃上一口,不能点破,这样新同志吃过以后就要忍受芥末油强烈的辛辣。这也是对新来的人员的一个教训,一方面让他们学会忍耐,另一方面也教导他们不管干什么事情都细心地观察,因为我们面对的是案件。”没想到吃一盘芥末粉皮还有这么多的附加内容,我颇感意外。我问姜勤勤:“那你为什么还要骗我说还不错呢?”姜勤勤说:“我昨天晚上看电视,听一个大嘴巴的主持人说了个笑话,没想到今天中午就给你练习了一下,所以我想看看你的表情。”“什么笑话?”我问她。
我们开始上楼了,邓子一直在前面和田霞说笑,后面是快枪刘和胖子,夏队走在最后面。姜勤勤看了看后面的夏队说:“等有时间再给你说。”说完,一脸的天真和神秘。
不就是一个笑话吗?我的电脑里多的是,我上网聊天的时候整天把那些人逗得哈哈大笑,她还在这里给我留悬念,小儿科!
办公室里的电扇坏了一个,修电路的工人说到晚上才方便停电修理,所以我们只好集中坐在姜勤勤旁边,她头上的吊扇是好的。她好像很不习惯有这么多男人坐在她身边,坐在那里很不安宁。她看着我,一直想说话。我正在看《滨河晚报》,一个叫梁朝伟的记者吸引了我--我很奇怪,梁朝伟怎么会跑到《滨河晚报》当记者呢?肯定是重名,这个记者的名字看来比较容易记了。
五
我并没有看那位记者写的什么内容,或者说我还没有来得及看,夏队就开始布置任务了。除了原定的排查和登记指纹外,还要添加一项任务--要记下一款“方向”牌子的锁。因为抢劫犯在作案现场留下了两个这个牌子的锁盒。据公安高等专科学校侦察系的几位专家分析,这两个锁盒可能是抢劫犯用来放置自制雷管的。
我去卫生间的时候看到了这几位教授,他们也在那里蹲着,其中一个还给我带过课,教我们犯罪心理学。我叫了他一声“老师”,他随即也认出了我,高兴地看着我说:“你已经到这里来了?”我边点头边往外走。老师在卫生间里洗了手才从后面跟过来,我才想起来,我忘记洗手了。楼下的车很少,院子里感觉有些静。老师问:“你在‘2·11’专案组?”我说:“是,我也是刚上班,还没有……”我本来想说自己还没有找到感觉。
老师并不在意我要说什么,他好像急于要说完他的话:“你在这里一定要注意向老同志学习,不只是学习他们怎样查案子,还要学习做人。”“学习做人?”我在内心疑问了一下,但还是向老师微笑着点了点头。是啊,做人有时候是需要学习一下的。我还小,有的只是单纯和满腔的激情,还不懂得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不仅仅是我,这是所有刚走出校门的学生的弱点。
老师还要对我说什么,但我们的办公室已经到了。我停住脚步,想请老师到办公室里坐一下,可老师却要回到小会议室里--他已经满身是汗了,小会议室里是有空调的。
办公室里好几个人都围在邓子身边,原来他们在看强奸犯李大江的问讯笔录。因为有姜勤勤在,所以不敢大声念出来,但他们都在那里一点点地看,边看边发出笑声--那样子,是非常会心的笑。
姜勤勤应该在睡午觉吧,可她现在坐在我的椅子上,头枕着胳膊在看着什么。我走近,才发现她在翻我的文件夹。我的文件夹里面只写了两句口号,她在看什么呢?但她确实在那里一页一页地翻着,非常认真,直到她看到我。
“他们真无聊,在那里拿着一个案卷笔录当黄色小说读呢!”姜勤勤说着用眼白了一下旁边的几个人。我笑了一下,没有接她的话。我想,要不是她说这句话,也许过不了一会儿我也会加入他们的无聊。
男人都是好色的,只不过有些人暗暗好色,有些人更光明些罢了。譬如邓子,这家伙就是个光明的好色男人。他把那本笔录合上后,大骂了一句:“这家伙,照我说,给毙了得了!”
下午3点的瑞五路仍然很热,不少女人都撑起了伞。路边的树和建筑都那么安静,行驶的车辆也那么安静。我坐在昌河车的后面,看着这安静的周围,感觉这个城市很安全,并没有什么坏人。邓子不知从哪儿弄了一辆昌河车,对我说,以后这辆车就是我们的了。我有些欣喜,以为是夏队给配的,没想到邓子说是一个黑社会给送的--“妈的,不要白不要!”
我吃了一惊,想问一句什么,但看见邓子一脸的无所谓,就住了嘴。
时间还早,邓子把车直接开进了瑞五路西头的铁路家属院。他把车停在家属院门口的一棵树下,然后下车,敲着车窗子说:“我要进去找一个人,你等我半个小时啊,不要走动。我们有一点要紧的事情要谈,晚上他要请我们吃饭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样的饭菜才叫过瘾!”说完,他晃着脑袋走了。我发现邓子的衣服今天没有反着穿,而且他的手上也没有戴戒指。邓子今天有些太平常了。
我开始听车里的磁带,都是王菲的歌。我打开一个叫《我愿意》的专辑来听,然后静静地打瞌睡--王菲的歌不影响睡觉,因为她不会唱着唱着突然大声起来--我听了不大一会儿就睡着了。是有些困,我睡在五月滨河的街头,居然还穿着警察的服装,说起来实在是一件丢脸的事情。
我忽然想起昨天晚上看的那个叫《春江水暖鸡先知》的女主角。李二叫真会编造故事,在这个三级片中他是这样编剧的:一个女孩子因为家里穷来滨河打工,到了一家按摩馆学习按摩。因为家里急需要钱就答应了老板的非分要求,给老板来了个特殊的按摩,但女孩始终不答应卖身。后来,一个男人开始追求她,女孩就把自己给了那男人。之后女孩才知道,原来自己所爱的男人只是老板雇佣的一个男妓。从此以后她便恨透了男人,她拼命地和不同的男人做爱来发泄自己的恨。后来她的欲望越来越强,她彻底成了一个妓女。
我努力地克制自己,但是李二叫他们拍摄的内容也太写实了……正在睡觉的我忽然醒了,发现自己身体起了变化,我梦见那个女主角了。
女主角年龄不小了,但风韵犹存。其实那个女人也就是20多岁,可做妓女一旦超过20岁就算是年龄大了。我看了看表,已经半个小时了,邓子还没有影子,就继续听音乐、睡觉。我的眼睛刚闭上不久,就听见车窗玻璃响。我睁开眼睛看见窗外有一个老太太,我母亲一样的年纪。她那善良的眼神感动了我,我赶忙摇下了玻璃,看着她。她问我:“警察同志,我是外地来的,在这里等我的儿子,能问你现在几点了吗?”我看了看手机说:“2∶20,大妈。”
我没有听她说“谢谢”,就摇上了玻璃。天太热了,我把两边的玻璃窗都留了些缝隙,然后继续睡。可能是一阵风过来了吧,风里有路边自行车的声音,有汽车刹车的声音,有女人吃吃笑的声音,还有路过车辆里的男人和女人打情骂俏的声音;风里还夹杂着女人午睡后从床上沾染的淡淡的香水味,有浓浓的汽车尾气味,有旁边一个医院里的消毒药水味,还有夏天里最常见的果皮被风干了的味道。我一边辨认这些声音和味道,一边算计着时间。我终于要睡着了,可这个时候,车窗又响了。还是那个老太太,还是那种善良的眼神,把我刚刚培养的睡意又驱走了。我摇下玻璃,问:“大妈,还有事?”大妈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小伙子,现在几点了?我儿子说20分钟后会到,怎么现在还没有来?”我正要回答她,只见她一抬头,兴奋地叫了起来:“三儿,三儿,我在这儿呢!”
我接受了她的感谢,目送她走远,又朝着铁路家属院里望了一会儿,仍然没有邓子的影子。我心想,这小子和女人去鬼混,却留下我一个人在这里晒太阳。可是,我的睡意把我的气愤压制了下去,只一会儿,我又听不见窗外的声音了。
我想我也许能睡到晚上。可不幸的是,不到20分钟的时间,又有人敲窗子;我以为是邓子,睁开眼就想骂人。一看,是一个陌生的中年妇女。让我泄气的是,她的问题一点创意也没有,几乎是复制刚才那位老太太的话:“大兄弟,我是外地来的,在这儿等我的兄弟,能问一下你现在几点了吗?”我看了看不远处的公交车站牌才明白今天停车的位置实在不好,都是下车了就等人来接的主儿,一个个都是从乡下来,不知道时间。我只好又看了看手机,说:“2∶55!”
我实在有些担心:她要是再过20分钟还来问我时间我怎么办?我又没有办法制止她来问我,除非我不想回答她;其实我并不是不想回答她,实在是想睡一会儿,可这儿的确也不是睡觉的地方……想来想去,我又有些睡意了。又一个人从我的车子边经过,他离得实在太近了,惊醒了我。看来我已经怕有人敲窗子了,我一定要想个办法制止谁再敲我的窗子。我在车里翻了一遍,没有找到一张纸。我看看左边,在公交车站牌的不远处有一个邮政报刊亭。我走过去,向那个正在哄孩子的女老板借了一张纸,她随手给了我一张杂志的招贴画。我翻过来一看,是干净的。于是我就用水笔写上了几个大字:“我在休息,请勿打扰!”本来我是想写上“我不知道现在几点钟”的字样,但是我怕有人多管闲事,说不定过了一会儿有一个人敲开我的玻璃叫醒我然后告诉我现在几点了,那就惨了。
我睡得很好,直到傍晚的时候才被一阵刹车和倒车的声音吵醒,发现自己在滨河东郊一家温泉酒店的停车场里。四周众多豪华的轿车夹着我睡觉的这辆昌河车,我下车后感到有些孤独。是的,旁边的景物都是静止的,旁边站立的两个保安笔直笔直的,一动也不动,也像是静止的。在这个静止的豪华停车场里,只有我是运动着的,我从昌河车的前边走到后边,又从后边走到前边,然后又钻进车里。
手机终于响了起来,是邓子懒洋洋的声音:“你小子睡醒了?知道现在在哪儿吗?”
我揉着眼睛说:“没看出来,是不是在国内啊?”邓子笑了:“对,在国内,国你个头啊!上来吧,四楼416房间。”上楼要坐电梯的,只有我一人,一个漂亮的女孩给我做电梯驾驶。
她训练有素地微笑、做摆手的动作,只是她的牙齿有些难看,当然那并不影响接吻。
真是的,黄色影碟真是害死人,我现在看到女人就想着她们适合干什么。我一边脸红着,一边骂自己无耻。
四楼的走廊里,邓子正在接电话,来回走动,腔调很正经。看到我他招了招手,然后把手机挂掉了。进了房间,他向一个胖胖的男人介绍,这是我们新来的小赵,小伙子很能干的。然后他又向我介绍那个胖子,是这家温泉酒店的老板。握手的时候我想起来应该用力让这个胖子栽个跟头,但我看邓子对他挺客气的,也就没有搞恶作剧。倒是这个胖子挺用力的,握手的时候他的手很有劲。
胖子老板把名片递了过来,我才知道他叫李星海,原来这家星海温泉酒店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说的话都是套话,我不感兴趣;吃的东西都是我没见过的,我很有食欲,从第一筷子下去开始我的筷子就没有停过。吃饱了以后,我才开始认真听他们说话。
我刚刚吃饱,一个书生气质很浓的戴眼镜的年轻人进来了。邓子介绍说,这个年轻人是研究生毕业,正在攻读医药学博士学位,是李星海的儿子,叫李木森。李星海介绍他儿子的时候说,这个孩子缺木,所以起了这样的名字。邓子感兴趣地问李木森的生辰八字,然后又胡乱地算了一番,说这个名字挺好的。
我不懂邓子说的那些话,也不信那些话,一边听一边和李木森说着话--对话是李木森开始的,基本上是他问我答。“你刚参加工作?”“是,今天是第二天。”“邓子是我的好朋友。”
“看得出来。”“你老家好像不是滨河的?”“滨河的邻居,云阳的。”
“我最喜欢云阳了,那个地方最适合居住了,小桥流水的样子。”“嗯,还不错。”
“你平时喜欢干什么?”“喜欢……喜欢看影碟。”其实我真的不知道自己最喜欢做什么,说是看影碟吧,也就是那么回事儿。看看美国大片,看看香港的周星星成龙周润发李连杰。这些都说不上是爱好,只是无聊时打发时间。我还喜欢干什么呢?一时间我开始整理自己的爱好了--喜欢上网,其实还不是在网上和摸不着的女人打情骂俏?
“喜欢下象棋吗?”
“喜欢,水平一般。”事实上我象棋水平很高,虽然少有机会下棋,但罕逢对手。
“我们这里有保龄球馆,你打过吗?”“打过,差一点受伤。我打得不好。”
“好,待会儿,咱们一块去打一会儿?”
“那看时间吧,我和邓子应该还要执行任务的。”我忽然想起了任务,我和邓子要到瑞五路去登记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的指纹。这件事情一下刺激了我,看了看手机,已经7∶30了。包间的电视关着呢,要是开着的话,宋英杰也该出来说天气了。
我转过头来看着已经微醉的邓子说:“邓哥,一下午我都睡了,我们的任务可是一点也没干呢!”
邓子斜着眼看着我:“噢,不慌张,待会儿我们就开始。”
我喝不惯白酒的,喝了两瓶啤酒脸就有些红了;而邓子不知道喝了多少白酒了,他依然面不改色。
临走的时候,邓子对李星海说:“李叔,市里这一段时间风声紧,又出了个抢劫大案,所以这一段时间你们酒店最好少出事。”
李星海一边抱拳一边说:“放心好了,我这边好着呢,该打点的早就打点过了;只是偶有治安事件发生,要是用得你的时候,小森就给你打电话了。”
这样,我和邓子就撤出了星海大酒店。邓子一边打酒嗝一边说:“今天喝的那个酒真不错,要不是你跟着我,肯定会再给我捎两瓶。”邓子的话有些醉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