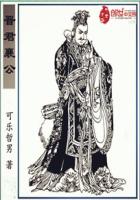我看到吴仁杰的车上还坐着一个漂亮女人,就明白了眼前这一切。吴仁杰看到了我,我的警服吸引了正在撕扯的他们。女人像遇到救星一样地跑过来,她扑通一下跪在我面前,涕泪交流:“警察同志,你可要帮帮我,他还没有离婚就带着个女人跑来跑去的,是不是犯罪啊?”
我的手被吴仁杰的妻子紧紧地抓住了,而吴仁杰却上车逃走了。
意外的事情还有。当我骑着摩托车回到住处的时候,发现有人在胡同口来回地走动。我的直觉告诉我,门口这个穿着讲究而且拿着一个手机假装听电话的人是邓子的手下。他看我的眼神是躲避的;如果他自然地看我且自然转移到别的地方,我是不会怀疑他的;可是,人一旦心里有了鬼就无法表演完美,他在我走过之后就再也不说话了。我向后看他的时候,他正看着我--他的表演太业余了,甚至还不如李二叫那三级片中的妓女。上楼,照例要吹口哨。厕所里有女人的咳嗽声,声音陌生。
我快速地开门,用毛巾擦脸上的汗。毛巾上的臭味差一点让我吐了,我拿着毛巾去走廊的水龙头那儿洗脸。侧身看到邻居家的门都开着,一个女人在屋里哼着,另一个女人在忙碌着炒菜。已经是下午4点多了,她们才开始吃午饭。
我边洗毛巾边看邻居家的门,其中的一个出来了--吊带上衣,没有浓妆,脸上的气质还不错--让我对先前的猜测有些拿不准了。回屋,我把上衣脱下来,把风扇开到最大的一档,坐在那里吹。电视里正在唱歌,这个叫周杰伦的家伙唱歌极其懒惰,哼哼唧唧的,不用力。歌的节奏倒是挺缠绵的,歌名我记住了--《东风破》,但歌词我是一句也没有听清。
我习惯性地换台,滨河教育电视台又在重播电影。真巧,又是王家卫的《阿飞正传》,我坐下来,确认是。
接下来的几句台词是一定要看的,我深坐了一下,头靠在沙发的背上。
张曼玉:你到底想怎样?
张国荣:我只不过想和你做朋友而已。
张曼玉:我干吗要和你做朋友?
张国荣:看着我的手表。
张曼玉:干吗要看着你的手表?
张国荣:就一分钟。
张曼玉:时间到了,说吧。
张国荣:今天几号了?
张曼玉:十六号。
张国荣:十六号,四月十六号。一九六○年四月十六号下午三点之前的一分钟你和我在一起,因为你,我会记住这一分钟。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是一分钟的朋友,这是事实,你改变不了,因为已经过去了。我明天会再来。
用于清凉的毛巾突然从我的脖子上滑落,掉在地上,沾满了泥。我的脖子上一阵凉意,我清醒地意识到这一场景数月前出现过。张曼玉的旁白很快过去了,镜头在不停地切换。
我的毛巾掉在地上,我已经做好姿势去拾毛巾,可是眼睛却被张国荣和张曼玉的对话吸引。
张曼玉:我们认识多久了?张国荣:很久了,不记得了。张曼玉:我表姐快要结婚了。张国荣:是吗?替我去恭喜她。张曼玉:她说结婚以后会搬到家公家婆那边住。张国荣:那就是说……张曼玉:那就是说我得找地方搬了。张曼玉:我想搬到这里和你一起住。张国荣:好。
张曼玉:那我怎样跟我爸说呀?张国荣:说什么?张曼玉:我们的事呀。张国荣:我们的什么事?张曼玉:你会不会和我结婚?张国荣:不会。张曼玉:我以后不会再回来了。
镜头一下子给换走了,这一段情节我好像从来没有看过。我想了想,大概是看电影的时候正好在和女人接吻吧--我一下想起了大学时惟一吻过的女孩小麦。
毛巾仍在地上,电视仍在演,我却陷在回忆中。我最甜美的回忆不过是林田田在篮球场边给我加油,我喜欢她;只是她那个时候是班里的公众情人,所以她不但对我微笑,同时也对其他19个男生微笑。
小麦是情人节里的一枝孤单的玫瑰,我那天不知怎么碰倒了她。我一直没有想清楚,她为什么那么结实地撞在我身上了?反正是她当时就哭了。
后来我哄她,给她读当时正流行的情人节笑话,然后一起去第三食堂吃饭,再然后去校外的一个小影厅看情侣电影。大概电影开始15分钟后,我们就开始接吻--那是我的初吻,小麦不是,她有些疯狂,甚至是放荡。
一出电影院,她就甩开我的手,消失在女生4号楼。我从第二天开始等,等了她整整一周,也没有见着她。她不是我们学校的。我那时候有些傻,仍然一直在女生4号楼前等,大概等了一个月,以孤单告终。
正是那一种等待打动了林田田,那以后她对我好了一些。可是,我假装单纯地沉入对小麦的回忆中,对眼前的风景视而不见,直到林田田的耐心消失。
大学时代的枯燥有时候是因为孤单,有时候却是因为虚荣。那个时候我们时常想表现自己,却又不知道该表现自己什么。那真是一种没有方向的煎熬,学习和训练反倒成了一种发泄。
我无疑是发泄得比较好的人。我的身体是班里最好的。全校的长跑我每一次都会获得冠军;我被瑞一区公安局借用,参加警察自由搏击比赛,获得了第一名;又被瑞一区公安局刑警大队借用,参与侦破一起绑架案。然而,我越优秀,林田田却越躲避,直到后来,我们之间想说一句话也找不到机会了。她好像有很多的心事。
电视里张国荣和刘嘉玲在吵架,语速很快。我的手机响了。手机在桌子上,一声、两声、三声……我把毛巾随手捡起,放在鼻子边闻了一下,又差一点儿吐了。是姜勤勤。
“你在哪儿?这么吵,在家里?”她的猜测往往很准确。这种让男人无处躲藏的女人,按照邓子的观点,是不能娶的。“嗯。”我把毛巾扔到脸盆里,把电视声音关小了。“你怎么了?刚看过黄碟啊?有气无力的。”姜勤勤又在猜测。“什么时候学得这么无聊啊?我刚才只是回忆起上学时候的事了,有些伤感。”说完后我感觉有些可笑,就哈哈笑了。
“夏队让我提醒你,晚上一起吃饭,他请客。别忘记了,我们俩得陪他去警校上课。”姜勤勤说。“噢,你不说我都忘了。好吧,吃什么啊?这么热。”“朝鲜冷面,瑞六路上有一家正宗的。你骑着摩托车来局里,还是我去接你?”姜勤勤问。
“都行吧。”
挂了电话,我忽然想起邓子,好像我们说好要一起去瑞十路上的冬芭手烧吃饭的。我赶忙回拨了姜勤勤的电话,却一直占线。
《阿飞正传》还在演着,面孔也多了起来,刘德华、张国荣、刘嘉玲、张曼玉……我忽然失去了耐心。电视声音很小,一点点地飘进我的耳朵里,台词像棉絮一样,暧昧而温暖,让我在这样一个炎热的下午出汗不已。原来是电扇停了,我又一次打开它。
再次拨打姜勤勤的电话,通了。
“我们不是和邓子说好的一起吃饭吗?”“噢,我咋把这一茬给忘了?对了,我待会儿给邓子打电话吧,咱们改天再吃那个冬芭手烧。”姜勤勤可能走出了办公室,她的电话里传来刹车声,“夏队让我们俩一起去听课,可能是想让我们明白一些道理吧,你一定要去。对了,我待会儿就去接你。你那里有西瓜吗?我想吃了。”
“没有,要不,你上来的时候买一个吧,我给你钱。”“好,一斤西瓜一百块。”姜勤勤说完挂了电话。
四
一场真正的爱情总是来得突然,我和苏浅浅没有准备好,就都陷进爱情的泥泞里。大雨让局里的车拥挤起来,姜勤勤被这场大雨阻在家里。她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正准备出门。她说她的车子由夏队开着。我的任务是去淡水鱼网吧等苏浅浅,但走到祥五路的时候,忽然想到要请她吃饭的,就沿路向南走了走。我的伞只能照顾我的上半身,而我的下半身已经湿透了。苏浅浅的办公室电话没有人接。我不熟悉她们的规章,只好站在她们单位门口等她。时间一下子慢了下来。
我一开始站在路边数过往的行人,后来数过往的出租车,再后来我站到一家干洗店的门口避雨。
雨一直没有停,旁边的女人拿着手机一直说个不停。我听她的口气像是个电视台的记者,一会儿说录制内容需要补拍外景,一会儿又说还有一个嘉宾没有定下来。
路边全是经年的老树,是法国梧桐。树上栖着鸟和爱情,是的,鸟在树上生存,爱情在树上生长。我在祥五路路东第五棵树上看到这样一行字:1998年6月22日,一只鸟儿飞过,我爱上了一只叫做陆小雪的鸟,张路(珞)--最后的那个字不知是“路”还是“珞”。
这场爱情的读者有无数个,从1998年6月22日开始就不停地有人点击。
点击,我忽然就想到了这个词汇。如果这棵树是这位张路和陆小雪的个人主页的话,那么我也是他们爱情主页其中一个的过客。我这样想着,心里变得快乐起来。
每一个从小院里出来的人都被我细细地阅读,有一个女孩看起来很像苏浅浅,我叫了一声“苏浅浅”,那个女孩回过头来看我--她穿着一个淡黄色的透明雨衣,样子比苏浅浅要活泼些。她大概是苏浅浅的同事,看着我,问:“你找苏浅浅?”
我点点头。“她一会儿就出来了。”说完她截了一辆出租车就走了。视野里一时间只剩下雨了,人的孤单就是因为眼睛里找不到焦点。
我现在孤单了,直到我叫出苏浅浅的名字。我站在那里想那棵树上的字,眼睛里突然又出来一个女孩,我认出了她。
苏浅浅惊讶地站在那里,忘记了向我打招呼。我招手,她这才慌张地跑过来。
“你在这里做什么?”“等你下班。昨天不是说好请你吃饭吗?”“你在这里等了好久了吗?”“我打你们电话,一直没有人接听。”
“我们在会议室开会。”
“没什么……我正好看风景。”
“下这么大的雨,我以为你不来了呢?”苏浅浅把伞合上,靠近我,整理头发。“嗯,怎么会?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顺手把她的伞接了过来。“重要的事情?你有事情找我啊?”苏浅浅看着我问。“没有,我是说请你吃饭这件事情很重要啊!”我抬眼又看见那棵树以及树上的爱情。
“呀,你的衣服都湿透了。”苏浅浅的手伸向了我的衣服--那是一种情不自禁的关心吧。
“没什么,那棵树比我湿得还厉害。”我指了指那棵爱情树。
雨好像突然变小了,仿佛是为了配合我们接下来的行走。我把伞给苏浅浅撑开。
“你看到这棵树上的字了吗?”我指着那个张路的名字给她看。字很小,苏浅浅说看不见。我说:“在那个大脚印里面。”“呀,我看见了,原来这里真有一场爱情啊!”苏浅浅兴奋地踱了踱脚--她的动作那样矫情,又那样充满单纯。我们步行向北走,过瑞一路,过瑞二路,过瑞三路,来到八中旁边的一个小吃店,吃他们的特色饭--砂锅炖鸡块。“味道很好。”我看着苏浅浅说。“他们做的时候放了中药。”苏浅浅看着我说。“我吃出来了,有枸杞子。”我看着苏浅浅说。“还有一种叫不出名来的中药,我的同事们都说吃了有助于消化爱情。”苏浅浅看着我说。“消化爱情?”我有些疑惑。
“嗯,爱情有时是坚硬的,我们不一定能消化得了。”苏浅浅边往外吐骨头边说。“爱情是鸡骨头吧?”我说。我们俩都笑了。
我们一起去网吧。雨很小了,路上撒满了浪漫的种子,两人一把伞的故事遍地开花。我试着不打伞,跟在苏浅浅的身后。
“你说,那棵爱情树上的字多久才会消失?”苏浅浅突然转过头来问我。
“多久?7年吧。爱情不是有保质期的吗?”我感觉自己的答案挺哲学。“不对,我相信那些字永远不会消失的,因为爱情永远不会消失。”
苏浅浅倒着走路,好和我说话。我们只顾得用上半身思考和交谈,完全忽略了下半身所接触的地面。苏浅浅正笑着,突然就被绊了一下,她的一只手在一瞬间伸向我,又在一瞬间往地上摔去。我连想的时间都没有,向前一倾,就拉住了她的手;然后一只腿跪倒在地,怀抱住了她。整个过程只有一秒钟,引来很多路人观看。
苏浅浅吓得在我的怀里喘了好几口气,她那不大的乳房挤压在我身上,她全部的心跳印在我的身上。她好像在我的怀抱里睡着了一样,直到我把她扶起来。
苏浅浅的脸红了。
沉默,牵手,一些词语在手指间流淌。我们牵着手一直走进了淡水鱼网吧,才放开了彼此。“我们……”我们同时说出了这两个字。“你先说吧。”我看着她。“我们……一起去看邓哥吧?”苏浅浅说。“好啊。”
“你想说什么?”“我忘记了。”我忽然忘记自己刚才想要说的话了,怕苏浅浅不相信,又说,“我再想想,待会儿再告诉你吧。”
我们坐了昨天的位置。我掏出兜里的一张纸--是昨天晚上夏队在台上讲案件的时候我在下面写的一首诗。我也不知道算不算诗,想拿给苏浅浅看,思忖了一下,觉得不如直接贴到网上。
我输入网址:www.womenclub.net,然后就上去了。
QQ上有好多留言,大多是世界杯开始前的一些预测,最后的一条是苏浅浅刚刚发过来的。
寂寞烟花:你想起来了吗?
陶瓷了:想起什么?
寂寞烟花:你刚才想要说的话啊。∶D
陶瓷了:噢,还没有想起。
陶瓷了:我昨天晚上写了一个东西,你待会儿看吧。
寂寞烟花:好啊,你发上来吧。
我开始录入昨天写的这首没有标题的诗,一边录入一边替换用词。
最后我又给起了一个名字--《怀疑》。
我走在街上
常常怀疑走在我身后的人
会杀掉我
我想
杀掉我就杀掉我吧
反正我满脸孤单
那么我可以选择一下我身后的人选
我喜欢她是一个温柔的女人
在路边的候车亭里
我们不期而遇
我希望她是长头发叫张曼玉
或者我们有共同语言
可以坐下来说说诗歌
可以走在落叶上谈谈哲学
在杀我之前
我可以选择一个餐厅吃饭
用温暖的音乐陪伴着我们说话
然后我们开始行动
各不相干的行动
手舞足蹈却又张口结舌
我想要的那个节目尚未开始
一张脸的单纯被另一张脸的冷漠替代
温柔藏在公交车上
我们相互伤害
用相反的脚步离开
用冰冷的眼神杀死刚刚的暖意
在冬天的一条街上
我们的速度极快
会撞倒正在读诗的你和他
于是
我看到我慢慢倒下
身后的事情排列整齐
在我被杀之前
我要求一场大雪铺垫在野外
我要用洁白思想来考验你们
我忘了当时为什么会写这么多的感受,是因为那天下午那个在我住处附近徘徊的人吗?是因为我骨子里有一种惧怕吗?还是因为我忽然间开始多愁善感起来呢?
我转过头看了苏浅浅一眼,说:“我贴上去了。”
寂寞烟花:你的语感原来这么好!
陶瓷了:语感?没有,我只是随便写的。我感觉有些零乱,也有些矫情。
寂寞烟花:是真的好,我喜欢极了!
陶瓷了:是昨天,我心里有很多复杂的想法,一时间无法排遣。
寂寞烟花:能不能和我说说?陶瓷了:好啊,都是工作上的事情。寂寞烟花:我知道一些有关邓哥的事情,我知道一些你们俩的事。
陶瓷了:你知道我们俩的事?你知道什么?
苏浅浅的话让我一下紧张起来。
我和邓子一起去李木森那里,一起去找女人,一起去做了多少坏事啊--难道苏浅浅都知道了吗?雨停了,不少人开始关机,网吧里安静了许多。苏浅浅等不及我回话了,扭过头来看我说:“有一个很好玩的图片你要不要看?”“你给我地址。”我说。
苏浅浅从QQ上把地址发了过来,原来是“我们社区”里的一张图片:一个西瓜,切开以后里面全是生的,只有一个拳头大小的地盘是红的,最好玩的是,那形状很像一颗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