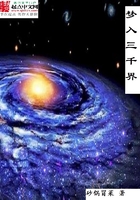上官浅韵一行人虽然早早的逃离了皇宫,可宫里的事却远远还没结束,而只是一个开始。
这件事太后自知瞒不住宫里的那些妃嫔,索性便也不瞒了。
上官羽下令将宫中妃嫔,只要是有名分的,不论高低,全都召来椒房殿,让太医一个个的把脉,让稳婆一个个检查身子。
这件事一出,位份低的妃嫔倒没什么大事,可位分高的妃嫔却觉得自己被羞辱了。
其中第一个出手的是宋夫人,她是在皇后嫁给上官羽之后,便仅隔一个月被册封的侧妃。
而当年的上官羽还是王爷,她已是位居正王妃之下的侧妃,受尽宠爱多年,虽然上官羽待她不如从前好,可依仗着她娘家势力,她也在宫里从没吃过什么亏。
只不过,自从去年开春她失去第一个孩子后,便不愿意再见人了,也与上官羽不亲了。
可就算她不受宠也不想争什么了,那她也还有娘家哥哥和母亲安氏给她撑腰,怎么着也沦落不到任人这般羞辱的地步。
上官羽本来就在气头上,此时见这个在她身边最久的妃子,竟然出手推开了上前要把脉的御医,并且还这样愤怒的瞪着他,他心里的火气不由得更大,一挥手便无情下令道:“将她拖下去仔细查。”
宋夫人见上官羽竟然要让稳婆查她的身子,她羞愤欲绝的拔下金簪,抵着自己的脖子,悲伤落泪道:“皇上,想素素伴你身边多年,从你还是王爷时,素素便陪着你,多少年过去了,为了你,素素放下了所有的骄傲,和众多女子侍一夫,更因此失去了孩子,自此再不能孕。可就算如此,我恨遍了所有人,甚至是送我为你侧妃的父母,可唯独不曾恨过你,因为……当年少女情怀,我最不该的便是动心。呵呵……你要我死,真的是何其简单?真的大可不必这般羞辱于我。而我宋素,也绝不接受这样的侮辱。”
“不要!”上官羽已被刚才宋夫人一番话说的心软了,可没想到这个对他柔情温婉多年的女子,性子竟然是这般的刚烈,宁死不辱。
宋夫人一根金簪了结了自己这可悲的一生,当她倒下的那一瞬间,她感觉天地都在旋转,耳边最后传来的……是那个她错爱了一生的男子,那也有一丝惊恐后悔的声音。
太后也被这突发事件吓到了,这位宋夫人性子自来的温婉,对她这婆婆从不忤逆,对她儿子也永远都是柔情似水的,待宫人也都宽容,可说是宫里最性柔和善的一个人。
可今日,她却宁死也不受辱,这般刚烈的性子,让她想起了宋夫人的母亲安氏,安氏可是太后的娘家侄女,当年宁愿嫁给一个五品小官,也不愿入宫为妃。
而她的女儿,就算不像她一样性子刚强,那也绝不可能是个逆来顺受之人。
宋夫人这一生自认活的很悲哀,她为了这个无情的男人,将一身的刺都一根根的拔掉,害得自己遍体鳞伤,也只是想守着他一辈子。
可最终,她守着的男人,却这样逼死了她。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她就不该因父亲愚孝,听从祖父的话,嫁给上官羽这个无情人。
上官羽望着宋夫人倒在血泊之中,那般悲伤的至死都在流泪。红颜易碎,这个默默以真心待他的女子,终是被他逼死了。
在这个宫里,也许只有这个默默等着他的女子,才是唯一真正对他好的人吧?
回想曾经,她是那样的似水柔情,笑是那样的莞尔羞涩,说话是轻声细语的,举止是温婉动人的,一切都是那样的柔软好似一朵云花,轻飘而软绵。
而他一直不珍惜她,认为这样柔性的她太令人乏味了,就像是在喝淡水,没滋没味的。
可而今他才懂得,人渴了的时候,也之后白水最能解渴。
烈酒入喉,只会灼燥,而不会有任何的通体舒畅。
因为宋夫人的死,今日在场的妃嫔全逃过了一劫。
上官羽因为宋夫人的死,而受的刺激不小。
太后也因此被吓得不轻,毕竟宋夫人的兄长是中将军,她的母亲又是安家的女儿,她一死倒是了之,留下来的烂摊子,她可不好收拾了。
本来之前就失去了玉家这个娘家做后山,而后皇后的事一出,江家也不怎么支持他们母子了。
而今若是宋家因为宋夫人的事而要追究,那到了最后,他们母子便又会失去一股势力支持。
唉!真是世事难料,人心难测。这个平素软性子的人,怎么突然发起狠来,便能狠成这样呢?
秦夫人也暗松了口气,若是她今日受此大辱,那以后她儿子还怎么坐上太子之位?
夏夫人是最感到庆幸的,因为那个死去的男子,竟然是她请进宫来的那人。
真不知道,到底是谁杀了他?
是夜
当所有人以为出了白天的事后,上官羽便会因为宋夫人之死,便多少会伤心个几日,好让她们心里有鬼的人,能做点准备,清理下证据之类的事的。
可谁曾想,上官羽在宋夫人死后,不止没伤心的沉痛几日,反而在当夜让人突袭搜了个个妃嫔的住处。
而所搜出来的人,和所审问出来的事,都气的上官羽吐了一口血。
太后也震怒的下令杀了那群贱人,真是全都该死,竟然将宫里变成了养野男人的污秽之地,该死真是该死啊!
夏夫人很害怕这事会查到她身上来,可好歹是没事的,因为她养得男人已经死了,而且都泡浮肿了,谁还能认出他是谁来啊?
秦夫人听闻楚良人,惠美人,常长使,刘良使等等多人,有的是养男人,有的是与殿前侍卫有染,甚至还有一位刚封的夫人,竟然不知和那个野汉子珠胎暗结了。
而将她拖进掖庭去审讯后,两个多月的孩子都流掉了,她也还说不出孩子的父亲是谁。
最终的审讯结果,被上呈给了上官羽过目。
上官羽看完后,便大怒的打死了一个小宦者,掐死了两名无辜的宫女。
因为审讯的口供上写着,那位新封的小夫人,竟然是扮作宫女与男人偷情的,而她偷情也只是为了聊解寂寞罢了,并没有去管那些男人都是谁。
而这位新封的小夫人,便是南忌初次献给上官羽两名女子之一。出身自然不高,乃为歌舞坊的花魁。
只不过,进了宫后,便无人认识她们,她们才能凭借一身媚功,哄得上官羽封了她们姐妹名分。
上官羽在一通发泄后,便怒红着眼睛吩咐道:“去把另一个贱人带来。”
“喏!”高远低头小心翼翼应一声,便退着要下去,可这刚一转身要,便看到了南忌,他拱手行一礼道:“见过南公子。”
“请且稍等。”南忌微笑对高远说一句,而后便举步走过去行礼道:“草民见过皇上!皇上若是生气,将她打发去军营便是,何必再多见她一面糟心呢?”
上官羽此时正坐在地上,背倚靠在柱子上,抬头看向南忌,看着对方良久,他挥了下手道:“就按南公子所说的,将那贱人给朕送去犒赏三军。还有那群没死透的贱人,全给朕送去犒赏三军,他们既然那么想男人,朕便让她们一个个的全死在男人身下,贱人!贱人,全都一个个的背叛朕,该死!南忌,她们都该死!该死!”
高远已被这样的上官羽吓的腿都软了,见南忌背后面的手示意他快走,他心里感激一番南忌,便忙转身退下去办事了。
上官羽此时用双手抓着南忌的衣领,将本来拱手行礼的南忌,已经是拉跪在了地上,当见南忌微皱下眉心,他便好似一瞬间清醒了般,忙关心的问道:“你没事吧?膝盖是不是受伤了?”
南忌拒绝了上官羽要为他检查伤势的好心,他缓缓站起身来,后退了几步,才又重新双膝跪坐下,望着对面形容狼狈的君王,他微笑淡然道:“草民无碍。”
上官羽望着那永远都神情平静的南忌,纵然是谄媚赞扬他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微笑淡然,让人瞧着便心里舒服。
南忌见上官羽盯着他瞧,他便拱手俯身道:“皇上若是心情不好,不如便去九华殿吧!在哪里,草民为您准备了一位特殊的美人。”
“美人?”上官羽虽然是有点想要南忌,可他却也不敢去要,因为南忌若是成了他的人,说不定因为争宠,便不会为他搜刮各色美人了。
南忌行一礼后,便起身来,伸手请道:“皇上,请!”
上官羽伸手出去,意思是让南忌拉他起来。
南忌虽然很厌恶接近这个昏君,不过,他还是走了过去,拉起来了上官羽,不等对方对他放肆,他便退开三步,伸手再次请道:“皇上,您请!”
上官羽看了南忌一眼,便向着内殿走去,沐浴更衣。
南忌随之退下,出了宣室殿后,他便给一个宦者使了眼色,让对方先走一步,去看看初夏的药劲儿上来了没有。
说起来,在郦邑大长公主府买的那两个男子,还是惜文比较识时务。
而那个叫初夏……唉!实在是太倔强不听话,非得逼他用药。
上官羽沐浴更衣好后,便坐着垂纱羊车去了九华殿。
南忌在将上官羽送到九华殿后,便伸手请对方进去,而他却止步在了殿外。
上官羽觉得南忌今儿有点神神秘秘的,说不定,这九华殿里,南忌还真为他寻了一个妙人呢!
初夏被下了药,他深知自己中的是什么药,以往在那种腌臜之地中,对付不听话的公子姑娘,那些个老虔婆,从来常用的便是下药。
当人身不由己的时候,就算再不甘愿接客,也会在药劲儿上来后,淫荡不堪的投怀送抱让男人去玩弄。
上官羽刚进来内殿后的寝宫中,便听到一声又一声压抑的呻吟……
当看到那幔帐挂起的床榻上,一名只穿着件宽松衣袍的少年,正在身子扭曲的呻吟着,因他过分的挣扎而衣袍半褪,这半遮半掩的风景,可比脱光了诱人多了。
初夏还有一丝理智尚存,当看到那名身着龙袍的男子到来时,他便想要立刻咬舌自尽,也绝不再受辱第二次,这次被下药,又让他想起了当年被罗言欺辱的事。
回忆如潮水,可却没有一件美好的,全都是肮脏不堪,全都是令人生不如死的……
上官羽已在那初夏要咬舌自尽时,便一个箭步上去,单手捏住了对方的下颔,低头瞧着他怀里媚色诱人,且羞愤落泪的人儿,他勾唇冷笑道:“你都到了这儿了,难不成还想逃脱朕的手掌心不成?小美人儿,放聪明些吧!你想死不容易,想生不如死……朕倒是可以成全你。”
当时的皇后可比这少年强硬多了,还不是被他糟践成那样,都没能咬舌自尽死掉吗?
初夏是想推开对方,那怕是奋力一搏,他也要试着能不能一头撞死。
可南忌给他下的药太厉害了,他清醒了一瞬间,便彻底被药物所控制了。
上官羽对于这个药劲儿上来的少年,他一点不在意对方不是自愿的迎合,他只要对方乖乖听话就好。
南忌不知何时已入了殿内,不过,他没有靠近去看什么春宫图,而是站在一根柱子后,听着那些不堪入耳的淫靡之声。
他就是要让初夏恨,等初夏变成一个心中充满毒汁的魔鬼后,那便是上官羽的死期了。
而上官羽死于郦邑大长公主的男宠手里,蓝田郡主又和上官浅韵走的很近,这样一引人深思来,那便是大将军府联合郦邑大长公主府,一同谋害了一国之君。
如此绝妙的计划,也只有他那位狠毒的姐姐能想到。
而他……被逼无奈,一切不过也只是为了生存罢了。
上官羽还在疯狂的暴虐着被下了药的初夏,而南忌却已是不忍的离去。
他做下这么多的罪孽,将来死后,定然会下十八层地狱吧?
将军府
凤仪阁
上官浅韵派持珠去找花镜月,可花镜月却被他父亲急召回唐氏了。
这下好了,没人可以保护洛妃舞了。
展君魅对此事本就不想管,可他家媳妇儿总这样温声软语安慰洛妃舞,把他丢在一边可都将近一日了。他受不了了,所以,他出了个好主意道:“不如,让墨曲保护蓝田郡主吧。”
“墨曲?这个……似乎也行。”上官浅韵虽然觉得墨曲很不靠谱,不过,那人武功还不错,保护洛妃舞应是绰绰有余的。
既然已决定让墨曲保护洛妃舞了,小气的展大将军,自然是要赶紧派人去请墨曲来了。
墨曲被持珠再次毫不温柔的拎来,没进门他便有怨气颇深道:“持珠,姑奶奶,祖宗,下回能不拎着我吗?我有脚,自己会走。”
“进去!”持珠才不和他废话啰嗦,直接伸手将他推了进去。
墨曲被推的差点栽一个大跟头,进去后见到洛妃舞在,他这习惯在美人面前风度翩翩的墨君,倒还不忘整理下衣服,而后才摇扇很风流倜傥的走了过去。
持珠在后面很想给墨曲一脚,都什么时候了,他还有心情招蜂引蝶。
墨曲过去坐下后,便发现他们三个的神情都很凝重,好似发生了天大的事情一般,不由好奇问:“出什么事了?那昏君驾崩了吗?”
他们三人看了墨曲一眼,他们倒是想上官羽驾崩,可……人家现在恣意快活着呢!难死!
上官浅韵摇头叹声气,望着墨曲,神情极其凝重道:“明渠死了个男人,那男人是后宫妃嫔养的,现而今除了我们几个,其他王爷公主,全被扣在宫里出不来了。”
“什么?上官羽当了绿王八?好事啊!你们怎么还一脸不高兴的啊?”墨曲一合扇子高兴道,可话说一半,就发现他们几个有点不对劲了。
上官浅韵也不打算瞒着墨曲什么,直言对他说道:“上官羽瞧上了洛表姐,这次若不是我带着洛表姐闯宫,恐怕洛表姐……我虽然有父皇的旨意做免死令,可凡事也不能做的太过分,毕竟我是公主,他是君王,我总不能一次次的公然违抗圣旨吧?”
墨曲懂这个,就是摆明官大一级压死人。不过,上官羽要真非是皇室血脉,上官浅韵这个正经的嫡长公主在其下,的确是挺憋屈的。
“那件事已有了点眉目,不过……要找到人,并非是一两日就能办到的。而要废帝另立,也不是说说那般容易的。”上官浅韵一直为此顾虑太多,所以做事便显得很畏手畏脚了。
她不能因为太后一人的罪,便害得她父皇被天下人耻笑,人已死,她如何也要保住她父皇的圣明。
展君魅看出了她的顾虑,他伸手揽着她肩,对她温柔笑说道:“其实,这事不用我们亲自去办。南露华,可已开始部署,更是在摧毁着上官羽的身体,只要我们耐心的等待,不用多久,上官羽便会死在南忌的手里。”
“对!君魅说的对,我们现在该担心的是另一件事。”墨曲用扇子一拍头,才想起来一件大事,看着展君魅便是一脸严肃道:“君魅,南忌买走了郦邑大长公主府的初夏,想利用蓝田郡主与将军府走的很近的事,来栽赃你们夫妻一个谋害君上的罪名。”
上官浅韵之前真被墨曲一脸严肃唬住了,可当听了墨曲说的事后,她便一副兴致缺缺的转过头去,问着洛妃舞明早想吃点什么?她好让人提前准备好了。
墨曲见他被上官浅韵无视了,他便盯着他家师弟看,想让他师弟知道,这事很严重,请看他认真的脸。
展君魅伸出修长的美手,端起青釉茶杯,淡定非常的浅抿一口茶水,缓缓抬眸看向他师兄,启唇淡淡道:“这些事,龙儿早已事先想到了。”
墨曲本来还在欣赏他这喝茶如一幅画的师弟呢!可是……他师弟说什么?这些事上官浅韵早事先预测到了?
上官浅韵被墨曲太过灼热的眸光盯的浑身不自在,她转头看向那瞪着眼睛打量她的墨曲,她伸手纤指在杯子里沾点茶水,便弹指向墨曲,让这人清醒清醒。
展君魅圈着杯子的手指紧收,要不他身边的媳妇儿早出手,他这一杯茶一定泼到墨曲脸上去。朋友妻不可欺,兄弟妻更不能想,他难道不知道吗?
墨曲的确清醒了不少,见他师弟又打翻了醋坛子,他终于忍不住的翻了白眼道:“君魅,你难道没听过一句话吗?各花入各眼,天下那么多的花,不是谁都和你品味一样的。就公主这样的,美则美矣,可缺了点精神头,瞧着病怏怏的,一点也经不住打好吗?”
经不住打?怎么,他墨曲娶媳妇儿,就是用来打着玩的吗?上官浅韵脸色很不好看,因为墨曲这话说的,等同骂她是个空有其表的花瓶。
持珠在后给了墨曲一脚,在墨曲抬头要发火之时,她便刷的拔出剑,架在了墨曲的脖子上,面无表情冷声道:“对公主无礼者,死!”
墨曲这回倒没怕持珠宰了他,而是望着持珠看了好久,抿着嘴憋半天,才摆出很心痛的样子悲声道:“在你的心里,是否我连‘她’的一根头发丝也不如?你说啊,你是不是一点都不在乎我?我对你那么好,你不珍惜我的真心也就罢了,为什么还要在我心上捅了千刀万剑啊?你说,你说啊!”
上官浅韵一开始还被墨曲悲伤的气势吓到了,以为持珠这一剑出鞘,真把墨曲给伤着了呢!
可后面……墨曲这人属泥鳅的,剁成八段都死不了,她何必担心她被伤残至死呢?
洛妃舞这位性子冷淡的大美人,也差点因墨曲后面的话,而身子一歪倒。
辛氏在一旁忙扶着她家郡主,她也是幸运的,因为没有进宫,所以才会在宫里出事后,她便随着郡主坐凝香长公主的马车来了将军府。
展君魅此时看墨曲的眼神,更是嫌弃了。这么丢人的师兄,他必须过几日,便踢他随穆齐尔一起回匈奴去。
持珠倒是淡定的很,在墨曲这样一番声泪俱下的谴责后,她便手腕一转刀锋锐利,削掉了墨曲一缕发丝,挑在剑尖上给他看,再敢瞎嚎嚎,她下一步就削他的脑袋。
墨曲看了那剑尖上的一缕发丝一眼,而后抬眸看向持珠笑说道:“你要是想问我要定情物,那早说啊!就我身上的东西,你随便挑,想削掉那个当定情物都行,当然,头发也很好,可以绣个香囊塞里面,贴身藏着,已做时时刻刻的相思物。”
持珠耳朵根儿已经红了,可她脸上还是平静到无情道:“我看削了你多出来的一块肉当念想更好,你说呢?”
“多出来的一块肉?那块肉是多出来的?”墨曲听了持珠的话,便低头去在他身上找着,他这身上的肉都是该长的,那有多出来的?
上官浅韵已红了脸,对于持珠的话,她自然是明白的。可是……持珠怎么知道这些的?这孩子可还未出阁,在哪里学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墨曲找了一半后,恍惚间明白了什么,抬头惊讶的看着面无表情的持珠,哆嗦着嘴唇半天,才深呼吸后,尽量平静的微笑道:“持珠,一个好姑娘,是不该知道这么多的。”
持珠看了墨曲一眼,便收剑回鞘,面无表情的转身离去,走到门口时,她回头看向上官浅韵解释道:“以前拿死尸练剑术,我不知道那多出来的肉是什么,而现在……公主,我知道了。”
上官浅韵望着持珠淡冷从容离开的背影,她多想事先告诉持珠,这些事真不用向她解释清楚的。
墨曲不敢看上官浅韵,却转头看着他家师弟,摇头叹一声:“君魅,以后你们休息的时候,能换个人守门吗?持珠还小,我不希望她这么早学坏。”
展君魅望着墨曲离去的僵硬背影,他想墨曲此时是极难受的。毕竟,被自己喜欢的姑娘说要自己的那个,是个男人都会被撩的有反应的。
洛妃舞面纱后的脸也羞红了,低头淡声的说了句:“不打扰你们休息了,告辞。”
辛氏伸手扶起她家郡主,对于这对小夫妻,咳!年轻人,感情好,是好事。
洛妃舞离开后,便想着,她明日还是搬离凤仪阁吧!否则,人家夫妻可要不好意思……总之,她在这里住着不合适,人家夫妻年纪轻轻恩恩爱爱的,总不能因她而要一直素着吧?
上官浅韵在目送走所有人后,便转头瞪着展君魅撂下一句:“这段期间,你回竹轩去住。”
展君魅莫名被连累,他放下茶杯,便起身跟在他家媳妇儿背后,很委屈的道:“夫妻同房,乃为周公之礼,圣人都不觉得这是坏事了,为何龙儿你却觉得这是罪事?还因此要这般残忍的惩罚于我,为夫觉得很不公。”
上官浅韵只知道他最近在看书,倒是不知道他都看了些什么,今儿听他如此的能说会道,便一个转身看向他,极其严肃的道:“墨曲说了,你要吃药,房事不宜太多。所以,最近你给我老实点,好好去吃药膳,治病。”
展君魅被她一番话堵的,心里恨起墨曲来。都怪墨曲胡说,才会被他家媳妇儿拿来当了真。
“近来不会太平,持珠之前和我说过一件事,夏春香在宫里养了一个精通房中术的男人,之前只是用来派遣寂寞的,可到了最后……她想要个孩子,所以便一直暗中给那男人下药,那男人是真的虚脱而死。”上官浅韵说着话,便来到了床边,展臂伸手,回头看着为她宽衣解带的男人。
展君魅觉得他在她的眼神中,看到了……如果你也不节制点,下个****的人就是你。
上官浅韵倒不是不想和他同房,只是她觉得应该节制一点,省得他真的精气不足,而因此坏了身子。
展君魅为她脱好衣服后,便也展开双臂,让她为他宽衣解带。
上官浅韵对这个耍脾气的男人,她无奈的伸手为他宽衣解带,心想,明明自己会脱衣服,却还让她帮着脱,真是……幼稚。
展君魅在她转身去放衣服时,便跟着她身后走,而后自后双手抱住她,弯腰将下巴搁在她肩上,很可怜的商量道:“龙儿,一夜一回也不行吗?”
上官浅韵脸颊飞红,声音却淡冷道:“不行。”
展君魅打横抱起他向床边走去,将她放到床上后,俯身看着她继续可怜巴巴商量:“那隔天一回呢?”
上官浅韵都要被他气笑了,可她还是板着脸摇头道:“不行。”
展君魅见装可怜没用了,他便双脚离地上了床,俯身以压倒的姿势,双手撑着她身侧两边,俯身望着她,语气很危险的问:“那三天呢?”
上官浅韵被他这样困在身下,她暗磨磨牙便要摇头,可这男人竟然以压倒性姿态威胁她,她脸一红咬牙道:“成交。”
展君魅虽然很不满意三天一次肉,可有的吃总比干素着要好。所以,他在得到他满意的答案后,便直起腰来去伸手放下了幔帐,而后……
“姓展的,你不守承诺!”幔帐中,传来上官浅韵的怒声,是那样的咬牙切齿。
“承诺我一定守,今晚之后,我会断肉三日。在我没调理好身子前,我一定遵守承诺,三日一次,绝不逾越,除非龙儿你想要,为夫才会勉为其难抛开承诺不管,好好让公主殿下你宠幸。”展君魅呵笑一声,说着无耻之极的话。
“谁要宠……唔!”上官浅韵气话刚出口,就被一吻给堵回了去。
夜色深深,外面是那寒风凛冽,细雪纷飞。
然而暖阁之中,却是春色无边,一室旖旎风光。
洛妃舞回去后,便洗漱了准备早早的睡了。
可辛氏却坐在床边,和洛妃舞说道:“郡主,大长公主可不是打您主意一回了。就算凝香长公主好心肠救你一次两次的,可以后呢?您毕竟还未出阁,怎好长久住在将军府?这可不是被人说两句闲话的事,而是会彻底坏了您的名誉啊。”
洛妃舞知道她乳娘也是为了她好,可她现而今除了这大将军府,她也再难找到容身之所了。
上官羽可是一国之君,他想要什么人,那还有要不到的吗?
也只有这大将军府,也只有上官浅韵这位嫡长公主,才能让上官羽畏惧一二,而不敢来这里强抢她入宫了。
“可怜的郡主,您怎么就这么命苦呢!”辛氏也不再多说什么,只是将洛妃舞抱在怀里。这是她喂养大的孩子啊,是被她当做女儿看待的孩子啊,她怎能不心疼她呢。
洛妃舞知道,在这个世上,待她最亲的不是那个生她的母亲,而是这个照顾她长大的乳娘。
记得小时候,她一直以为,亲娘就该是她母亲那样的,而乳娘就该是对她万般疼爱的。
直到后来,她偷偷出过一回府,才知道,天下的母亲无论如何打骂孩子,到事后,都会抱着孩子万般疼爱。
可她的母亲,却从不曾抱过她,更不曾对她有过什么疼爱。
而当别人的母亲,为了救孩子,甘愿被马车撞飞,自己受伤时,她的母亲却在一旁嗤一声:真是傻子。
而等那日城外去上香归来,他们遇上坏人时,她母亲果然聪明的躲开,推了幼小不过十二岁的她出去。
她母亲到底知不知道,她若落在那群男人手里,必然是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
“郡主又想起当年之事了?”辛氏在一旁,伺候着洛妃舞躺下,而后坐在床边为她拉了拉被子,低头叹了声:“当年若不是月公子路过,郡主您……唉!若是月公子能娶郡主您该多好,郎才女貌,多羡煞旁人。”
洛妃舞已躺在了床上,望着床边坐着的辛氏,她苦笑道:“乳娘,他当年拒绝了我,而今多年后,我想要随他天涯海角,他还是拒绝了我。我不知他身上到底背负着什么使命,我只知……我没勇气再被拒绝第三次了。乳娘,我是怕的。”
“郡主……”辛氏对这个蜷缩在被子里闷哭的孩子,她真的很心疼,很想去找上花镜月问问,到底她家郡主哪里不好,竟然配不上他一个神棍的弟子?
在她看来,什么国师,不过是个会胡言乱语的神棍罢了。
洛妃舞哭着哭着便睡着了,没有人会知道,人前那般冷若冰霜的蓝田郡主,背地里脆弱的竟然像个无助的孩子。
翌日
皇宫中昨晚闹了一夜,被处置了不少人,今早起来,还能闻到飞雪中掺杂的血腥气。
人来人往的宫道上,再无人去和熟人打招呼,一个个的缩着脖子低着头,闷不吭声的往前走。
九华殿
上官羽一夜快活后,还是很精神,便一早起来拉着南忌去上林苑赏雪。
南忌心里是不愿意的,不过……安排的一处好戏,若是他不带这昏君去,岂不是枉费了他多日的辛劳了?
上官羽不喜欢被宫人近跟随着,便命人远远的藏身跟着保护就好。
南忌撑着伞,陪在上官羽身边,上林苑的雪景是美如画,若是能有个佳人相陪,或有至交好友相伴,那一定是这冬日一大美事。
可惜!他身边这人太煞风景,只要看着这个昏君,他所想的皆是腌臜污秽之事,那还有什么欣赏美景的好心情?
上官羽赏着雪景,看着细碎的雪花,在望着身边的友人,他忽然笑感慨道:“南忌,这一生能有你这个友人,朕真觉得很庆幸。你瞧,那假山与雪,像不像你我,我是巍峨的山,南忌你是落在山上的雪,唯有你我在一起,才能画出这样天地造化的美景。”
南忌心里虽然冷冷嗤笑,可表面却是低头垂眸,很是恭敬道:“草民不过一介布衣,怎敢高攀皇上这座高山?再者说了,落雪最是无情,融化了便流失了,草民若是雪,待将来,终会离皇上您而去的。”
“啊?落雪无情?那这个比喻不好,南忌不要做雪了,还是和朕一起做山吧!这样便可以依靠着在一起,绝对不会分开的了。”上官羽也不知道是真不舍得南忌,还是怕南忌那日离开后,再没有人帮他安排美人了。
“草民遵旨!”南忌低下头,眸底满是冰冷的厌恶之色,和他一起做山?哼!那他宁发生一场地震,将他这座高山震塌震碎了。
上官羽和南忌向着假山走去,可在路过一片假山景色时,却听到了一些细微声音。
南忌一见上官羽脸色大变,他便低声请示:“皇上,要叫人来吗?”
“不必,朕亲自去看看,看到底是何人敢……”上官羽咬牙怒红了脸,可说到此处,他却如何也说不下去了。
南忌撑着伞,伸出一只手扶着上官羽,和他一起弯腰进了假山,那伞自然被丢在了外头。
上官羽一进入这光线微弱的假山中,刚开始眼睛还不适应,可当适应了后,他便在前摸索着假山内壁,向着前方声源走去。
“皇上小心脚下。”南忌这状似的关心话,实则是让上官羽小心点,别碰到石子,惊扰了那白日大胆偷欢的人。
上官羽却听着南忌关心的话心里一暖,不管这人是不是谄媚,有人关心他,都是一件令他高兴的事。
而在假山一处,此时可正上演着活春宫,女子是夏春香,男子却是个陌生的雄壮男子,那虎背熊腰肌肉发达的,一瞧便是孔武有力之人。
夏春香脸上有不正常的红晕,衣衫半解,与那男子相拥,正行苟且之事。
那男子双眼也泛着不正常血丝,低头望着这个天上掉下来的美人。
的确是天上掉下来的,他走着走着忽然晕倒后,醒来就看到一个衣衫半解的女人
夏春香本来在披香殿熟睡,等感觉一阵燥热行了后,醒来后,便发现自己在假山里,身边躺着一个男子。
之后,二人一个在药发作的不由自主下,一个色心大发,便行了这苟且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