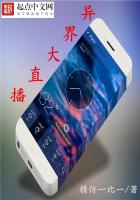永巷东南角有一个宗人院,这里是不规矩的宫女们犯了错,或者是寺人被责罚的一个地方,院子不大,进了这个院子,便是一片湖面,里边长满了芦苇,这里也是外面的宫人进入宫中之前必须在这里先干上一年的粗活儿后的垫脚石,或者叫它跳板也行。一般常有几个寺人守着,女令官们常常在这里教新来的宫人宫里的规矩和礼仪,这也是文妫结束三年不语后按陈宫规制特别设置的一个地方,后来,永巷令便将这个地方和宗人院合在了一处。
第二天,文妫还和往常一样,在楚宫里四处走着,她刚走到这里,看到一个寺人正在向那些宫女们分放着该洗的衣物,宫女甲拿着王上的一件下朝时穿的便装对宫女乙说:“你看,好好的衣服,挂掉了一只扣子,连扣门儿都扯坏了……”
宫女乙:“肯定是王上打猎,在山上挂的呗,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宫女甲:“”谁大惊小怪了?人家只是好奇,上一次洗时还是好好的,上次洗过后就过年了,王上什么时候打过猎?”
文妫走了进来,那些下人一见文夫人来了,急忙跪倒:“太后。”
文妫说:“都起来吧,把那件衣服拿来,让哀家瞧瞧……”
宫女甲将衣服递了过去,文妫看着,果然连扣门儿都撕坏了。
文妫问:“你确定这件衣服不是在山上挂的吗?”
宫女甲回道:“这件衣服,从上一次奴婢洗过之后,就该过年了,奴婢也是瞎说,王上去没去打猎,奴婢也不知道。”
文妫不经意地将它交给钗环:“带回去让哀家修修再洗吧。”
宫女们一起躬身:“喏。”
文妫回到兰台,将王上的衣服反复地看着,这是迎面第二个扣子,扣子是兽骨磨制而成,就算打猎被挂,那也多是腿上,怎么可能是前胸呢?什么东西挂着了而且有这么大的力度?如果真是被树技挂住,只要回一下身子便可摘下,为何还要硬拽呢?会不会是在骑马时被树枝挂住,或着是在追赶猎物时来不及回身……这么大的力度,人还能在马上坐得住吗?树枝既然能挂住前胸,那他的双手又在哪里?她突然闪出一个可怕的念头,会不会是被太后抓的?这个念头虽然只有一闪,却使文妫出了一身冷汗,她不敢再想下去……
文妫病了,钗环让寺人去请太医,那位院判匆匆来到兰台,钗环将闲杂人等都赶了出去,那院判直至榻前,文妫将手伸出来,那院判在文妫手腕上铺了凌绢,静心切脉……
文妫问:“你确定太后之死是摔倒的吗?”
太医不动声色地回了一个字:“是。”
文妫又问:“你确定是她自己摔倒的吗?”
太医挑选着词句:“这个,小医不知,只知道太后的头被摔了两次?”
文妫惊问:“两次?何以见得?”
太医回道:“回太后,人和动物一样,都有自我保护的能力,就算在完全失控的时候,她也会自觉地避开要害部位,老太后第一次头触地时偏右,因为这个地方骨质较厚,由于自我保护,第一次较轻些,第二次是直上直下,却很重。”
文妫:“也就是说,第二次再碰地的时候,也就没有了意识。”
太医:“按理是这样。”
文妫:“如果按常理推断,人在摔倒之后,有可能连碰两次吗?”
太医:“有可能。但第二次只会比第一次轻出许多,一般不会致命,可太后却不是,第二次反而是致命的。”
文妫将一件衣服从帐里推了出来,她问:“见过这身衣服吗?”
太医拿起来看了看:“好象王上穿的和……和这件差不多……不,小臣眼花,认不准了。当时王上穿的那件也和这一件的颜色一样,只是小臣没有细看。”
文妫在里边又说话了:“这件衣服扣子没有了,扣门坏了,姑姑,你指给他看。”
钗环拿过衣服将衣服的破损处拿给院判,太医接过来上下看着……
文妫又问:“你看到了什么?”
太医看了看说:“是,是扣子没了,扣门儿坏了。”
文妫:“这两处你有印象吗?”
太医摇了摇头:“没有印象。”
文妫:“给哀家开副镇静失眠的药吧,这几天哀家睡眠不好。我问的话不许和别人提起,你明白吗?”
太医:“医者只带医道,余者,什么都不带,请太后放心,小臣告退。”太医走了几步,又退回来从药箱里拿出一个小盒递给钗环:“小臣这另有一副药,也许管用,让太后先吃着。”
初春三月,宫里的桃花如期开放,簇簇桃花爬满了干枝,不仔细看,你很难看到躲在下面的绿芽、小叶。除了去年少有的一层薄冰,过了春节不久,这些冰便都不见了,而楚宫里的小溪,却比往年更加清澈碧绿,就连早晨的风也开始温吞吞的,充满了暖意……
午后的阳光格外明朗柔和,文妫带着钗环来到太后的住处,虽然老园丁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可是那些寺人还是沿袭着老太后的习惯,把院子整得井井有条,他们除去了多余的杂草,将海棠、迎春花、映山红按时令划分归类,这是老太后在世时的布局,有几个寺人在这里守着院子修剪着花草,院子还是那么干净,一尘不染。
文妫走了进来,屋子里仍然像太后活着时候一样,透着庄严和温馨,就如同婆婆还在一般,仿佛她正笑呵呵地看着文妫进来,那么熟悉,那么亲切。婆婆在时,她象闺女一样地疼自己,护着自己,整个楚宫只有婆婆不弃不离地挡在自己面前,挡着那些从不同方向射向自己的明枪暗箭。如今却恍如隔世,只有这所大房子,还是和过去一样,就是门眉上方用刀刻的几个字“万寿宫”,虽然用生漆描过,却有些略微脱漆,更显得年代久远……
前殿有太后的坐榻,下面的席片按规制摆在那里,这是自己带着三个夫人问安时坐的,在太后的左手不远处是一个青铜铸就的香炉,平时里边燃着从陈国购买的陈香,现在依旧香烟袅袅,因为自太后离世,万寿宫里的供给一直没断,一切与太后生前是一样的。绕过前殿,后边就是太后的卧寝,太后生前爱好清洁,所以这里仍然是规规整整,用手一摸那些用具,你会发现,上面已经有一层薄薄的灰尖,显然这里很少有人进来。文妫的眼泪无声地流了下来,她来到太后躺身的榻前,用手按了按,摸了摸,上面似乎还有婆婆的体温,她突然看到在一个角落里,扔着一个被子,这是婆婆出门时盖腿用的,文妫拿起来看时,里边却有着一溜血迹,血离被子边沿有两乍多宽,文妫突然心头一动,这也就是说,婆婆死前出去过,或着可以说,婆婆是在外面死的,是后来抬回万寿宫的,只有这样,婆婆才会死后四个多时辰方去报请太医,而婆婆真正死的地方又会在哪呢?
就在文妫胡思乱想之际,只听外面喊了一声:“王上驾到……”
王上来的好快呀,文妫用眼神让钗环将那个蒙腿的被子藏起来,钗环经验老道,她不慌不忙地将被子卷了卷,放在文妫坐的地方,当作靠背锦垫。
堵敖慌慌张张地进来了,向文妫大礼参拜:“儿臣参见母后。”
文妫神情安娴:“王上请起。”
堵敖这才起身。
文妫指了指右手边的席子说:“坐吧。”
堵敖坐下:“儿臣到兰台去看娘亲,他们说,娘亲出去了,儿臣找了半天才找到这里,母后,你怎么会到这儿来了?”
文妫笑了笑:“娘老了,总想着以前的事儿,就走过来陪你奶奶说说话儿,娘在想,王上大了,也该有自己的后妃了,娘想把兰台让出来,搬到你奶奶这里来。”
堵敖笑着说:“母后还不到三十,哪里老了。即便将来儿臣大婚,儿臣另选别宫不是也很好吗,母后只管在兰台住着,用不着为儿臣操心。”
堵敖陪着母后走了出来,钗环将那个卷起的被子依旧拿在手上,文妫坐上辇轿时,钗环又将那被子塞在文妫背后。堵敖用眼神示意外面的寺人,寺人心领神会,等文妫他们一离万寿宫,那些寺人便将太后的宫里又翻了一遍,见确没有留下任何东西,这才算放下心来。
堵敖伺候着文妫向兰台走去。
文妫告诉钗环:“开春了,天气转暖,有空你让宰伯派个人来,把兰台的桃树浇浇,这一水浇过后,花期会长些,花也会比往年更水灵更好看些。”
钗环点了点头:“这个请太后放心,我这就去请宰伯商量。”
堵敖说:“用不着姑奶奶跑腿,寡人一会儿让人支会他一声就是了。”
回到兰台,文妫问了一些朝廊上的事,那堵敖推说还有事要处理便告辞回去了。堵敖还真是上心,没过多久,那宰伯便来了。
钗环迎了出去:“太后在里边,请进去吧。”
那宰伯也没有多想便走了进去,躬身:“太后……”
只听文妫呵道:“跪下。”
宰伯吓了一跳,不知出了什么事儿了,急忙跪下,忐忑不安地问:“太后叫奴才来,不知有什么吩咐?”
钗环端着两样东西进来了,将它放在宰伯面前,一个是酒壶,一个是三尺白凌,那宰伯一见先就打了一个冷颤,跪在地上连连叩头:“太后……太后……”
文妫心平气和地说:“昨晚我做了个梦,想让你帮哀家圆圆……,昨晚我梦见了太后了……”
宰伯吓得身体微微打颤:“太……太后……”
文妫:“对,太后,她老人家对哀家说,说她死的屈,死的冤啊……”
宰伯:“屈……冤……”
文妫:“太后还说,说他根本就没有死在万寿宫,死的地方她说,你最清楚……这两件东西你挑一个吧。
宰伯结巴起来:“不……不不,太后,我……我……我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哇,梦……梦……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梦……太后你千万不可深信……梦……梦……太后饶命,太后饶命呀……太后……”
文妫拍案:“不能深信什么?是不能深信你还是太后!你看看,这是什么?”将那个朦腿扔了过去:“你认识它吗?”
宰伯看了看忙道:“这……这是太后的蒙腿。”
文妫呵道:“那为什么会蒙在太后头上!蒙腿什么时候改蒙头了?”
宰伯辩白:“没……没……没有哇。”
文妫平静下来:“当时太后嘴里流血了对吧?”
宰伯:“那……那是摔的。”
文妫:“你翻过来再看看……”
宰伯急忙将蒙腿翻了过来。
文妫问:“看到什么了?”
宰伯瞪着死一般的眼珠子:“血。”
文妫厉声问道:“哪来的血?”
宰伯嘴里说不出一句囫囵话来:“是……是……是太后嘴上的血?”
文妫阴阴地问:“太后死前去哪儿了?”
宰伯急忙摆着手:“她就在自己宫里,哪……啊也没去。”
文妫:“那这蒙腿上的血是哪来的?”
宰伯脸上的汗不住往下流着:“……我……我……奴……奴才不知道哇。”
文妫:“你是说,太后在冤枉你?”
宰伯急忙以头触地:“奴才不敢……”
文妫:“看来只有请你到那边亲自去和太后说了。来人。”
几个寺人闻声走了进来。
文妫一指案上:“把这壶酒给他灌进去。”
一个寺人上来搂住宰伯的脖子一只手扭着宰伯的头,另一个拿着酒壶就要往他嘴里倒酒。
宰伯吓得杀猪一般大叫着:“太后,太后,老奴说,老奴说呀……奴才知道,奴才什么都知道……”
文妫将手一挥,几个寺人退了出去,文妫静静地望着宰伯……
宰伯说:“奴才进去时,太后就已经倒在了地上……”
文妫:“什么地方?”
宰伯:“是……是曲苑……”
文妫:“曲苑?齐姜的曲苑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