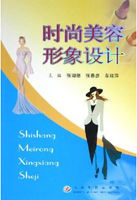两人浅谈深谋,不觉已至黄昏,天色渐暗。盖天韫道:“贤弟,天色已晚,我也要告辞了。”
秦琛祯听了一惊,道:“怎么仁兄要走?仁兄这样千里迢迢而来,小弟我还没有设宴款待……”
盖天韫“贤弟千万别出此言,如今非常时期,我呆得越久,你我危险愈大,我们也不要顾那么多礼仪了。”
秦琛祯一听盖天韫的话知道留不住,叹怨道:“没有想到你我兄弟一场,情深意重,这样好不容易见上一面,又要匆匆告别。盖兄远道而来,为弟的都不能亲自设宴款待,还要让盖兄饿着肚子赶路。真的是对不住盖兄了。”说着眼中似要溢出泪来。
盖天韫听了也觉心中悲戚,站起身来走到秦琛祯身边,握住他的双手道:“贤弟,莫自责,怪只能怪这乱世道。怪这无常绪的朝廷,唉……”顿一顿,他又说道:“只是,——我们这一别不知是否与贤弟再相见。”说着也是满眼含泪。
那秦琛祯听他说得如此颓废消极,更觉心酸悲哀起来,道:“仁兄是福大命大之人,何出此言,你我定有相见之日,那时再把酒言欢,共庆胜利。”
“但愿如此吧。”秦琛祯无奈地说。
盖天韫慎重点头作别,欲要照原路出来。
秦琛祯道:“天韫兄,随我来。”引着走过另外一条隐秘小道,道路两旁皆有树木相伴,藤草掩映。淡淡的月光透过森密的树叶,星星点点照射在地上,微弱得如同白色的鳞片。让人恍若置身于另外神秘世界。过了几道暗门,看见一个半月门,这就是出口了,秦琛祯道:“仁兄,从这里出去,直接通到正街大道,右拐个弯就到了火车站口,现在夜幕,无人注意,趁此快行。”盖天韫点头应答,两人挥手道别。
那盖天韫趁着夜色,便急急去了。
秦琛祯送走盖天韫,才满腹心事地回到府中正厅。管家胡侬正急得团团转,看见秦琛祯,忙上前禀报道:“老爷不好,苕昉姐儿不见了。”
“什么?”秦琛祯一怔,道:“早上我出门时,苕昉不是在我的书房么,怎么会不见?”
胡侬言语慌乱地回答道:“是的,苕昉小姐一开始在书房看书,后来,到中午我去叫苕昉姐儿吃饭,可是书房里根本没看见她。直到现在都没看见苕昉姐儿的踪影哪。”
“我去看看。”秦琛祯三步并做二步,跑到书房打开门一看,房中寂静无声,一抹月色斜照进来,铺泻在地上,如凝结的冰霜雪寒。他掌开灯,灯光如雪,照得房间里更是雪亮一遍,光影叠加着月影,更加衬得房间里一遍寂静幽深。
秦琛祯不由得打了个冷颤,脸色一白,沉着地喊一声:“苕昉。”
“苕昉姐儿。苕昉姐儿。”胡侬跟着喊二声,嘴唇都微微颤抖起来。
“去院子里看看,到处找找。”秦琛祯嗓子有些嘶哑。
“老爷,我都找过了,我都找过好几遍了呀。”胡侬看主子那情形失了主意,心里也更加多了几分惧怕。
“不可能,不可能,怎么会呢?”秦琛祯竭力回忆和女儿在书房的情形,他下意识里看了一眼放玉碗的抽屉,抽屉似乎没有关好,微微的露出一截黄绸绢来。
“不好。“”秦琛祯嘴里喝一声,趋步急促向前走几步走到书柜前,炯炯盯着那抽屉,抽屉竟然没有锁!他急忙打开那抽屉,露出破碎的玉碗碎片。
“天啊……秦苕昉,你!你打碎了文成公主玉碗!”秦琛祯两只手剧烈地颤抖,他两眼恨恨地盯着碎片,“这可是我们秦家传了几代的东西,居然被这你贱丫头打碎了。”秦琛祯气得两眼僵直,抖抖索索要摔倒一般。
“老爷,老爷……”胡侬连忙一把搀扶住他,又害怕他气噎而住,急急拍打着他的背。好一阵,秦琛祯缓过气来,脸已经气得煞白,坐在太师椅上喘气不已。“快,快,找到那贱丫头,狠狠责打。”
胡侬道:“老爷,这天黑了,去哪里找苕昉姐儿啊?”
“这败家子,死了才好。”秦琛祯大骂,一掌锤在书桌板上,不解恨,又连锤几下,锤得桌子咚咚吽响。
胡侬站在一边看着秦琛祯震怒不已的样子,不敢劝又不敢不劝,只是嘴里喃喃念道:“老爷,你消消气,玉碗已经打碎了,苕昉姐儿一定是害怕躲起来了,只是她是个十几岁的女孩子,如果躲在外面,怕不安全啊。”
这个秦琛祯不是没有想到,只是这秦苕昉竟然背着他偷拿并且打碎了秦家传家之宝,秦琛祯实在是气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