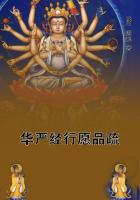“怎么可能呢?苕昉,你不要胡思乱想。我们现在不是每一天走在一起吗?”见苕昉静静地看着他,又说:“这一段,迟家班事情太多,师傅也不开心,过一段时间,这些事情过去了,我就去找师傅,和他提我们的事情,师傅同意了,我再回家去禀报我娘,找一个好的媒人去你家提亲,我们就可以永远在一起了。一辈子在一起,生生世世到永远。”他说着那样的话,满眼憧憬和希望。他这样认真让她看见希望和前途。
清风阵阵吹过,殷红的紫薇花落瓣如雨,他们沐浴在花雨之中,那样幸福和快乐!
两人喃喃私语,不知觉走到院子尽头,眼前是一半月门,出了半月门就是外巷街道了。外面街道的车声人声隐约传进来,齐润峙忽然兴趣大发,说:“苕昉,我们现在也无事可做,不如我带你去吃云南米线,我知道有一家云南米线是最好吃的。”
“云南米线听说是最好吃的,可是我却从来没有吃过。也不知道哪里有这样的馆子。”秦苕昉也表现出相当的兴趣。
“我现在带你去你就知道了。”
那守后门的张老头给他们打开木门,两人携手出去了。他们沿着街道向北走,走了好几条正街,然后才拐一弯进入一条小巷子。巷子有点旧,不像着正街那样繁华,但是人依旧是多。
“看,快到了。”两人正说话,迎面走过来一个人,看见他们似乎愣了一下,走过去又回头看。
秦苕昉被他看得心里毛毛的不安,低声问:“润峙,这人是谁?好像在哪里见过。”
“是很眼熟。”他一想到他赫然在目的塌鼻子,猛然道:“哦……对了,在火车站站台那个塌鼻子的人……”他俩一起回头看那人,那人正回头看他们,六目相接,都愣了一下神,又倏的回过头去。
“润峙,他不会是棠继仁的手下吧。”秦苕昉问。
齐润峙想一想,道:“不像。要他是棠继仁的手下早就应该有所动向。”
“可是,我心里还是不安。”秦苕昉本能的把手按在胸前的玉珏上。一颗心噗噗嘭跳着。
“苕昉,我倒是想到一个主意,只是不知道行不行?”齐润峙有些紧张而不自信,他喃喃不安地看着秦苕昉。
秦苕昉看他极其不自然的样子,微微一笑,道:“什么主意,你只管说。”
“我脖颈上也戴有一块玉,这块玉是我们家祖传下来的,现在我把它和你的玉交换戴着,这样他们就是找到你也无法得到玉珏。他们万不会想到戴在我身上。你也就安全了。”
“嗯,润峙,你这个办法不错。”
“可是……”齐润峙又狡黠一笑,道:“苕昉,我这块玉有特别的意义。”
“什么意义。”秦苕昉看齐润峙神情已经猜到几分,只是装傻弄痴自己不肯说出来,所以故意问。
齐润峙不知道秦苕昉故意弄痴,傻白呆地还在卖力解说,道:“因为我脖颈上这块玉是齐家祖传,自然以后是要传给齐家下一代,所以如果现在佩戴它,定然是齐家的儿媳妇。”
他这话一出,秦苕昉脸已经红到耳根,口中说道:“你使坏,不和你说了。”
齐润峙看她女儿做做之态,亦嗔亦怒亦娇羞,他心中甜蜜自然不必细说了。过了一会儿,他又问:“苕昉,这究竟是一块什么玉,为什么这些人穷追不舍,从上海追到千灯镇,又从千灯镇追到上海,一块玉有这样大魔力,只怕事情不简单呢。”
“是啊,就连我也不知道那些人为什么千方百计想得到这块玉。在很小的时候我父亲给我戴上这个块玉,叮嘱我说:这玉很重要,不要轻易让人看见,其他的我就一无所知了。不过,据胡侬说,上海三大帮派为了这块玉几次发动内讧,很多人也因为争夺这块玉丢了命。”
“哦。这样。”齐润峙脸色凝重,更加觉得换玉的必要性。道:“苕昉,我们下一次再来吃云南米线,现在先回去吧。”
秦苕昉见他神情谨慎认真,想到玉珏,点头同意。
齐润峙和秦苕昉说的塌鼻子的路人就是高巍,也就是朱启盛。朱启盛在附近正街的一家门面上开了一家典当行。这日偶尔从这条旧巷子路过,正好对面相碰了齐润峙和秦苕昉。对于秦苕昉的秘密他一点不知道,只是每一次见到秦苕昉他本能地感觉到她与众不同,冥冥之中会觉得她身上有一种吸引他注意的东西,但是细细要去追究是什么却又茫然。因为这他才会多看她几眼。他自己并不知道他使她的不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