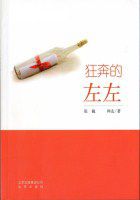歌手站在舞台,汗流满面。她用一只手轻抚胸口,她感觉心脏变成燃烧的炭。很小的舞台,她往前跨出几步,就碰到离她最近的桌子。桌边歪着三个男人,喝着酒,顿着酒嗝,打着拍子,眼睛里射出浑浊的光芒。正是上座高峰,每个桌边都坐满了人,桌上的啤酒瓶密密麻麻。音乐声震耳欲聋,歌手把嗓音扯得很高——她感觉嗓子深处已经开裂。
歌手是两年前来到这个城市的。之前她参加了很多比赛,试考了很多学校,可是却总是被无情地淘汰。于是她想到酒吧,想到站在狭小简陋的舞台上,面对着慵倦或者疯狂的酒客。每天她需要演唱一个半小时,可以赚到一百块钱。一百块钱,她把它抖出喀嚓嚓的脆响,那是她全部价值的体现。
男友是在酒吧认识的,留长长的头发,眼睛挑着,弹一手好贝斯。男友喜欢叫她“蜜糖”,有了他,歌手在城市里并不孤独。一个月前男友为她介绍一位朋友,三十多岁的单身女子,开着一家公司。那女人很时髦,很漂亮,身段窈窕,谈吐优雅。那夜歌手喝多了酒。歌手问你们认识多久?男友说半年。歌手说可是你以前没有替我介绍。男友就不说话了。他低头抽烟,鼻翼如大理石般坚硬和苍白。几天后男友去了女人的公司,他说他想试一份白天的工作。白天的工作,男友说,白天里有阳光。
今夜歌手又喝多了酒。她唱了《山歌好比春江水》,唱了《甜蜜蜜》,唱了《欢乐颂》,唱了《好心情》,唱了《牵手》,唱了《卡门》,唱了《To Be Loved》……有人发出尖叫,声音高亢刺耳。有男人跑上舞台,用极绅士的姿势递她一瓶啤酒。她接过,笑笑,音乐的轰鸣声中,一饮而尽。不喝行吗?当然不行。唱酒是节目的一部分,或许是最为重要的一部分。对酒客们来说,歌手喝酒,远比唱歌刺激。
又有人跑上来,又一瓶啤酒塞到她的手里。一曲终了,她脖子一仰,一瓶酒再一次喝光。她喝酒的速度很快,因为伴奏又响起来,她得为酒客们唱下一首歌。
喝到第六瓶的时候,她开始感觉到晕。仍然有啤酒源源不断地送上来,那是酒客们乐此不疲的游戏。她将很多啤酒洒到胸前,她感到酒液的阵阵凉意。她穿着单薄的白色丝质演出服,尽管又蹦又跳,可是她仍然感觉手脚冰凉。是岁末,街上正飘着雪,她却不知道现在离过年,还有几天。
她已经喝掉九瓶啤酒。她感觉天旋地转,整个人即将爆炸。她知道自己现在很不成样子,狼狈得就像酒店里醉酒的陪吃小姐。有男友在的时候,她会把酒递给男友一瓶,男友便会在一片尖叫声中替她喝掉。现在她找谁呢?狭窄的舞台,她找谁呢?暗仄的酒吧,她找谁呢?偌大的城市,她找谁呢?拥挤的世间,她找谁呢?有时候,喝得慢了,酒客们便会跟着架子鼓的节奏齐声高喊:一二三四,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诺大的城市,拥挤的世间,她找谁呢?
她不记得自己喝下多少酒。她只知道胸前湿成一片,嗓子钻心的痛。她踉踉跄跄往外走,她感觉自己在一个半小时里苍老了很多。冷风让她一连打了几个寒战,她将风衣裹紧,整个人更加单薄娇小。到处白皑皑一片,她认为自己是遗忘在雪地里的一只舞鞋。
晕。她扶住一棵树剧烈呕吐。有男人在不远处盯住她看,雪地里如同无所事事的鬼。似乎她吐了很久,她感觉吐出了自己的胆汁。
喝得不少?男人走过来,问她。男人有着粗短的脖子和臃钟的身躯,镜片后的眼睛闪出蓝幽幽的光。
她看男人一眼,抹抹嘴角,笑笑。她迈开腿,有雪片落进她的脖颈。
你,多少钱?男人在身后问她。
什么?
我是问,多少钱?男人跟上来,与她并肩。男人的表情并不猥琐,甚至带着几分清澈和腼腆。男人是认真的。城市里有太多这样的男人。他们有事业心,有责任感,可是他们并不拒绝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子。
她明白男人的意思了。她想大骂男人几句,可是她张了张嘴,终未开口。男人有什么错呢?有错的是她自己。她不该喝这么多酒,她不该如此狼狈。她不该孤身一人,她不该当一名酒吧歌手。甚至,她不该来到这个城市。可是,如果不来这个城市,她怎么能够,认识她的男友呢?
想到男友她笑了。她知道她将度过十几个小时的幸福时光。男友会在他们租住的小屋里等着她,或许为她冲一杯咖啡,或许为她榨一杯解酒的萝卜汁。更或许,什么也不说,只是给她一个结结实实的拥抱。寒冷的冬夜里,他的胸膛,就是她的天堂。
她打开门,却僵住了。屋子里空空荡荡,似乎孤寂百年。一盏灯摇曳不止,光影浮动,屋子里的一切似乎凝上冰霜。写字台上留着一张简短的字条,一把漂亮的贝斯斜倚墙角。
“我喜欢阳光。分手吧。”
歌手看一眼,发出一声短呼。再看一眼,双手便捂了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