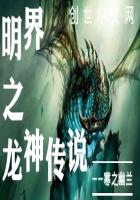马蹄声和着铃铛轻响,把那条无人问津的小道变成了战场,一点寒芒,那人挟万道银光而来,如落雪入林,点缀了银装素裹,铁槊微微一震,嗡得一声,天地为之一白。
枪势起于那座下白瑞兽的一跃之间,兵锋直指石堂主的头颅,虽是一人骑行,却仿佛千军万马。
只是一息,杨兴便进了身前,手中铁槊一晃,分成三道影子,直向石堂主刺去。
“来得好。”只见石堂主的黄眉微微一挑,左手握拳,向正中间那道槊影轰去。
一声巨响,那望月白瑞兽发出一声嘶鸣,连着向后退了几步,后腿支撑在地,立在半空,扬起了前蹄,便要往那石堂主脸上蹬去。
“马猴儿”一声大喝,那大马猴应声而动,同样是右爪握拳,黑色的拳头带着狂啸的风。
“孽畜休伤我兄弟,且吃我一刀。”不知何时,杨业离开了胯下那匹正胭脂枣红马,潜至那马猴身侧,一声大喝,用的是佛宗正雷音,内含深厚内家气息,十二字绝响,连成一片炸雷,惊起林中的群鸟,只震得四周草木不住摇晃。
话音未落,刀锋便起,杨业手中那杆三尖两刃神锋逆着拳锋而上,铛得一声,如中铁石,溅起一片火花,带着点点血光。
那马猴先是被杨业的一声大吼乱了方寸,接着爪上便中了一刀,伤口虽然不深,却传来阵阵刺痛。
那三尖两刃神锋上传来的气劲蚀骨销魂阴森毒辣,直往那马猴儿的经脉深处钻去,瞬间便麻痹了它半个身子。
“莫慌。”石堂主朗声说道,想要稳住那马猴儿的心神,反身一跃,五指并拢,以手为刀,向杨业头顶劈去。
杨业将神锋在头顶上一横,架住那只手掌,口中大喝道:“槊。”
那手掌起势极缓落势极沉,仿佛千钧,轰然而下,只砸得那刀杆如弯月一般,吱吱直响。
石堂主这一掌运足了十二成力道,心思也全都放在杨业身上,只求在短时间内击溃那把三尖两刃神锋,然后再去会那铁槊,却把后背留给了别人。
铁槊再起,疾若闪电,杨行那一身银光闪烁,仿佛真能刺瞎人的眼。
石堂主丝毫不退手上存了万般力道,此时一并迸发出来,终于劈断了那杆三尖两刃神锋。
噗得一声,刀柄断裂的同时,铁槊再进,扎中某物,溅起无数鲜血。
“马猴儿。”千钧一发之际,马猴儿用它那未受伤的右手护住了石堂主的后心,自己却伤得更重,右手被那铁捅了个通透。
刀柄断了,杨业就地一滚,却仍没有躲过那落下的掌势,头上那火红鸟羽被劈中,连带着赤铜护鼻盔,被掌风削去一半,吐了口鲜血,耳朵中仿佛千面锣鼓齐鸣,气血上涌动,脚步虚浮,自然是受了极重的内伤。
杨兴见一击不中,急忙抽槊下马,几步抢回兄弟身边,横槊于胸,护在杨业身前。
斗了几个回合,两边暂且偃旗息鼓,各自退后了几步,相互望着。
“木堂主再不出手,你们可就真的输了。”杨兴未被对方击中,身上衣着仍如先前那般明亮,只是离了白瑞兽,人少了些英气。
“被我一掌劈断了刀,还有脸说胜负?”石堂主双手横在胸前,褐色袍子上不染半点尘埃,扬着黄眉,脸带讥讽,显然还有余力。
杨业很是狼狈,被人劈坏了头盔,自个又在地上打了滚,大红袍和火麟甲上都沾满了泥土,更别提他受了极其严重的内伤,半蹲在地上喘着粗气。
忽然,那马猴儿惨叫了一声,翻到在地,蜷缩着身体,扭着脖颈,一双爪子在身上不停得挠着,丝毫不顾两只手爪上的伤痕,左边身子渐渐变得通红,连同那黑色的毛发一起,仿佛火烧,右边的身子则蒙上了一层薄薄的白霜。
“看来你们最初的目标便是这马猴儿。”一直沉默着的木堂主终于开口说话,自战斗开始时,他便从马猴儿的背部滑下,坐在道边的一块大石头上,安静地看着,仿佛眼前发生的一切皆与他无关。
“不错。”杨业答道,站起身,提着那断了刀柄的三尖两刃神锋,握在手中,当作一把长刀,抬起左手,手心一片暗红,却不住散着黑气,阴沉得仿佛来自九幽,对着木堂主微微一笑,说道:“我修的,是阴火。”
一旁,杨兴换了左手持枪,抬起右手,和杨业的左手并排举着,只见那手掌如丰年瑞雪般透彻,白得清明,四周生出淡淡的柔光,却暗含着一种刚烈的生气,脸上无定风波,眼神清冷,轻启唇齿,说道:“我,阳雪。”
兄弟二人配合默契,话语相合间,那一白一红两种气息交织在一起,如梦般美妙绝伦。
木堂主点了点头,极其缓慢地抬起了手,拱手,然后深深鞠躬,腰弯的极低,仿佛要将自己的头埋入双膝之下,声音很是诚恳,低声下气地说道:“二位只与我俩有仇怨,可否放过这可怜的马猴儿?”
“不行。”兄弟二人答得很果断,甚至连解释都没有。
“即便是现在,你们二人还是没有手刃我的可能,依旧得在这儿等着我那三个老混蛋兄弟,”兄弟二人的反应并未出乎木堂主的意料,他抬起头,眼波如水,却不是暗送秋波,而是在商量,在乞求:“若是放他们一条生路,我便不再抵抗,任由二位处置。”
“不可。”石堂主吼道,但他的声音还是没能盖过那只躺在地上的马猴儿的呻吟,所以,他反驳的声音渐渐的轻了,握紧了的拳头开始渗出鲜血,心中亦已成一片战场。
杨业杨兴兄弟二人没有大话,面无表情,手中的兵器却在微微颤抖,已然是动了心思。
“若是把那猴儿杀了,我等便让这块老石头离开。”一道声音从不远处传来,循声望去,有两位老者站在路边齐腰高的枯草丛后,一个高瘦,一个痴胖。
那声音满是调笑的味道,自然不是那两个老者所发,只见有双粗糙的手掌自草丛后伸出,分开草叶,露出了那人的身形。
“矮子,你可终于来了,来的如此急切,就不怕跑断了你那一对小短腿。”石堂主开口,丝毫没有给那人留面子,更没有掩饰眼中的恨意。
“为何要为难那猴儿?”见到来人,木堂主的嘴角露出淡淡的笑容,若是细细品味,便有苦涩的味道。
“因为杀了那马猴儿能让你伤心能让你难过。”声音很是无情,来自那个矮子,他是前秦五齐堂堂首,亦是当今大梁三丈院的兵老头。
“事到如今,我还是要叫你一声大哥,”木堂主的脸上露出了黯然的神色,抬头望了望天空,那儿有几只飞鸟,天色却已经晚了。
“我却不会再认你这个五弟。”
“我究竟做了什么,让你如此记恨。”
“你还看不出来么,他那不是记恨,而是嫉妒,谁让你是我们五个人中天赋最高,武学修为最强的那个呢。”石堂主站在一旁,拍着马猴儿的背,却不能缓解它的伤痛,一双黄眉褶皱在一起,混杂着伤心与怒意。
“我们还在前秦时我便常说,老三的性格直爽却太过偏激,只愿相信那些自我认同的事实,”兵老头个子很矮,所以当他看向别人时都像是在仰望,目光停留在石堂主的脸上,有些无奈,说道:“为何到了现在,你也不肯相信,是他负了我,而非我辜负了他。”
“当年我们五人刚到江湖上混迹,他救过你多少回,后来,闯出了名头,立了五齐堂,他捧你做老大,为了你连破镜的机会都不要了,你倒是告诉我,他如何负的你?”
“如何负我,人在江湖,一笑泯恩怨,唯有三仇不共戴天,亡国之奴,杀父之仇,夺妻之恨,三者之中他占了两,你告诉我他是如何负我的?”兵老头胀红了脸,举高了手,仿佛要跳起一般。
“杀父之仇我是知晓,他也膑了双腿,去了膝盖骨还你,但这夺妻之恨,又从何说起?”
“三哥,这事你不必再问,我的确是负了大哥。”将目光从天空中收回,木堂主的脸上多了点暖意,似乎是想起了那个女子的名字,他轻声说道:“如是她之所以离开,是嫌弃你是个矮子。”
“可你是个残废。”怒吼,往往体现了内心的彻底失衡,兵老头那紫红色的脸抽搐着,五官扭曲到了一块。
“所以说我辜负了你。”
什么是闲事,在生死面前谈女人便是闲事,杨兴对这场无聊至极的谈话失了兴趣,将铁槊插在地上,上前,身后带着千点寒霜。
“什么意思。”兵老头问道。
“你们五人的旧事我不管,此番前来,只为求个结果。”
什么是结果,结局便是结果,故事的结局可以是相逢,也可以是离别,而人的结局却只有一个,死亡,杨兴所求的结果便是木石二位堂主的结局,是他们的死局。
很少有人敢如此要求兵老头,即便那些压力只是隐隐而来,但还是能在其中看到那个皇帝的身影。
沉思了许久,兵老头做出了决定,开口说道:“我的仇是陈年旧恨,终究是要带到坟墓里去的,而你们却是年轻人。”
“所以?”
“三个之中挑两个,了去这段怨,平了这份债。”话音刚落,兵老头和他身后的金铁二位当家一起出手,三只手掌一齐向石堂主袭去。
“乌龟儿子王……”石堂主还没有骂完,便中了掌,毕竟他只有两只手,对上的却是三只手掌。
中掌后,石堂主软软地到下,一旁是那马猴儿幽幽地抽泣,众人望向木堂主,却见他已张开了双臂,那是一个诚挚的邀请,邀请死亡的降临。
“槊。”一声轻啸,寒芒再现,鲜血溅在杨兴白净的脸上,迷了他的眼,脸上露出一个得偿所愿表情,满足。
“另一个呢?”当那铁槊刺穿木堂主的胸膛时,兵老头的眼睛微眯,眼角多了几道皱纹。
杨业上前,举起那把断了刀柄的三尖两刃神锋,劈下,血如泉涌。
血光消散,马猴的黑色脑袋滚落在地,双眼渐渐无神,咯咯咯三声从嘴里发出,带着血沫,那是它最后的悲鸣。
“好选择。”兵老头赞道。
没有理会那个矮子发出的称赞,兄弟二人跨上各自坐骑,潇洒利落,不一会儿便消失在道路的尽头。
“我们也走吧。”叹了口气,兵老头三人转身离开,一眼也没看那倒在地上的石堂主。
终于安静。
“像他那么飘逸的人物不该因那个矮子的嫉妒而死。”回长安的路上,一身火龙鳞的杨业突然开了口。
“所以我故意偏了分毫,动肺腑,却没伤心脉。”披着千点寒霜的杨兴答道。
“很好。”很中意弟弟的选择,杨业点了点头。
战斗结束,没有花上特别多的时间,月亮便升了起来,绕一圈月晕,没有星星,道路上,石堂主早已没了踪迹,马猴儿的尸首依旧淌着鲜血,木堂主倒在那儿,生死不知。
忽然,有了动静,叮叮当当,是环佩轻响,古道上来了位女子,一身青衣,仿佛她的名字。
牵着马,跨过马猴儿那悄无声息的尸体,她走到木堂主身前,将他托起,放上马背,顺着道路向南走去。
“大梁皇帝,想得真长远,”月光下,她的声音青翠欲滴,想到独处深山的师傅,以及马背上快死了的男子,摇头叹道:“世上男子,都不是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