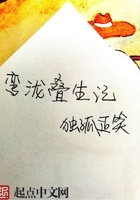确实,现在我无法猜到确切的未来,但是我能看得到大概。
如同看得到——我什么时候将闭上麻木的双眼。
`
人们都认为占卜师是一个很神秘危险的职业,但是在这所学院里我却觉得自己比任何一个人都显得安全,至少我不懂任何杀伤性的东西,只能每晚独自陪着塔罗牌在空荡的自习室中看日光灯的影子。
直到后来我才明白了,原来,我从不是一个人,因为她总在我身边,就在我身后的三步之遥,从未靠近,而我也从未回头。
这所小小的学院很奇怪。人们学的都不是一些正常的东西:炼金学、五行学、神语学、灵力贮存工程、元素逻辑、黑生物……我感觉与这些东西格格不入,可是我又确切的身处其中,在高等技能系当一名特殊的学徒。
她是动学系的学生,我看得出来。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会和我共用一间自习室,这间没有窗户的教室似乎是专为我而设的,布下了院方红色等级的隔离结界。据说除了我有进出的权限,没有其他人能够进入。
他们总这样,为我设置了专门的寝室,专门的餐厅,专属的导师,甚至是专一的思想。
我没见过自己的父母,也从未走出过这所小小的学院。我知道它很小,但塔罗牌上没有告诉它外面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的,牌面的含义每当涉及到这个问题都会显得模棱两可。他们跟我说外面很危险,出了学院他们就没办法保护我。
我还是一个人。我曾想过和导师以外的人交谈,比如偶尔碰见的学生,他们或者大我几岁,或者和我差不多年纪,只不过他们似乎都很忙,连说话的功夫都没有,只对我笑,意义不明。
每天晚上,当我睡不着,我都在看日光灯,等待着它有一天突然熄灭,令这间明亮的自习室瞬间陷入无边的黑暗,似乎这样我才失去看护。
才能回头看她。
耳旁回绕着她练习折纸的声音,窸窣的,很好听。我很小的时候看过一名动学系学生做着同样的练习,他们将一张卡纸平放于课桌上,在不接触这张纸的前提下通过动术将其折成一只纸鹤。那时候我觉得这很好玩,就仿佛桌上的纸自己变成美丽的纸鹤。
但是后来我知道了,这种强制性的扭曲也能作用在人的身体上,而他们正是在学习这个。
一个人久了很累,就算什么都不用你做,只需要活下去,你还是会很累。渐渐的,我明白了这种感觉就是人们常说的——孤独。
才发现原来这么可怕的词就是用来形容我的。
渐渐的,我的世界只剩下她。
渐渐的,我的双眼再也无法合上。
渐渐的,我觉得日光灯像一道枷锁,锁住了我的视野。
但我还是不能回头。
因为我知道,只要我一回头,发现身后其实什么也没有,我就会失去活着的理由。
`
我决定做最后一次占卜,用来帮我决定是否回头。
那时腊月刚过,完整意义上的冬天即将过去,初春的风依旧料峭。空荡的自习室没有窗户,我无法亲眼看到更多的东西,只能通过感觉。当你一个人呆久了,你便会发现每个季节带给人的感觉都不一样,即使它和你有几乎无法逾越的间隔。
毕竟,你们属于同一个世界。
我做了一个深呼吸,将课桌上杂乱的塔罗牌收到一起,看着一张张相同的背部图案重叠再重叠,像是我的思绪。我知道我现在的占卜状态不太对劲。
我不愿再等。
耳旁的折纸声依旧清晰,似乎在说,其实身后确实有一个从来不说话的她存在,而不是我自己的幻觉。
洗牌,切牌。
我静静的,感觉折纸声更大了一些,几乎充塞我的脑海。自习室里飘荡着旋律,很惬意,不像是死亡的征兆,而是母亲的轻语,在告诉我随时可以闭上麻木的眼睛。
我打从心底涌出一股笑意,笑自己这么细腻的错觉。
`
在翻牌的瞬间,整间自习室陷入了一片黑暗。
`
我的心跳停了一拍。
自习室外响起了爆炸声,夹带着远处人们的呼喊,还有电流的紊乱攒动,让某种类似于耳鸣的感觉传递在每个人身上……外面很乱。
黑暗。
黑暗中我第一次有了看见光芒的感觉,彷如沉重的窗帘被掀开了一角,而早晨的第一缕阳光恰好照进。
来不及犹豫,我就已经转过头,面无表情看向身后三步之遥——
黑漆漆的一片,什么也看不到。
`
自习室外的混乱还在继续。我想占卜一下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黑暗中我连自己的手都看不到。
静静的听着那些吵闹,那些所有不应该发生在这个学院里的声音,我突然开心得想大笑,似乎从有记忆起就没有过这种该死的好情绪。
我闭上麻木的眼皮,很快就感觉到了如潮水般涌起的酸楚,憋得我眼泪直流。原来流眼泪是一种享受,和吃喝拉撒相同,都是人必须做的事。原来身体里有一些东西只有用眼泪才能带走。
记得更小的时候,看到身边的同龄人,因为老师的责骂或者是同学的嘲讽而放声哭泣,我总是会鄙视地走过,因为我认为哭泣是一个人懦弱的体现。每当遇到相同的情况时,坚强的人应该一个人默默承受,然后做得更好,我一直都是这么去做的。现在我才终于明白,懦弱分为很多种,其中一种叫做不敢哭泣。
你害怕哭了之后你会显得更懦弱,更无助……
更需要人陪。
`
混乱很快就漫延到这间自习室,能清楚的感觉朝向广场的那面墙开始升温发烫,呈现一种让人悚然的腥红。我睁开眼睛,等待着脑海中出现的接下来的爆炸场景,奇怪的是这个爆炸似乎并不会殃及到我,所以我依旧安静的呆在座位上看着。
在爆炸发生之前,自习室的后门率先被打开了——这是我没有预见到的。
门的打开带进了外面晃动的火光。门口逆光站着一个人,虽然被火熏得几乎睁不开眼,但还是努力看清了这间黑暗的教室,并锁定了我。我也看着她,这时有一阵强劲的气流从广场吹进,掀动她金色的长发以及衣摆,并使一些火星打到她的身上,像是点缀。
她在气流中站稳。
我对她说:“小心。”
我指的是接下来的爆炸。
她好像也在最后一刻发觉了,因为在我说完话后,她回头看了一眼火光熊熊的学院广场,就变了副表情冲向我,并将我扑倒。
爆炸紧随而来,似乎有什么东西砸到了墙上,令整面墙洞开,着火的碎石横飞,其中一块就砸在我刚才坐着的地方,仍然燃烧着。
借着这块火石我终于看清了她的脸,和我想象的有点出入,至少不是那种折纸鹤的文静感觉。她有着蓝色的眸子,但是里面却闪着火,那是打她心里存在的东西,或许是仇恨,或许是伟大的抱负,总之是富有动力的。除了眼睛之外,脸庞还算平常,虽算不上精致但也细腻伶俐,就像你不可能要求一把厮杀的用剑如同挂饰一般华丽。
她没有注意到我在观察她,因为广场上发来的下一个天火术已经要砸中处于自习室中的我们。
我没有任何动作,看着她做出我脑中想到的每一个动作——
她站起身,在双手间唤起一道水流,并将其扩散成一堵墙挡在我们前方。
天火轰然砸下。水墙破碎的同时她正满手是汗的把我拉到她的身后,防备着随时可能飞来的碎石。
我想叫她不用这么紧张,因为我脑中看到碎石四散飞出却没有一块打中我们。但是等我开口说完她已经能亲眼看到结果了,于是我趁着这两秒钟欣赏了一下她金色的头发,在跳动的火光下闪着美丽的柔光,就像水。
她应该还只是一名学生,看起来年纪比我大不了多少,也就十七岁左右的样子。
被一个陌生的女孩深深吸引住的感觉很奇妙,可能是由于她出现的契机。我试图想象她安静练习动术的样子,但很显然,她是一名水系学生。
`
自习室的结界完全没有发挥作用,或许在陷入黑暗的瞬间就失去了效果。经过两发天火术后,整间自习室已经只剩下残垣断壁,能清楚的看到外面的情况。原本平静有序的学院里现在随处都有冲天的火光,无数的火焰痕迹将地面划得支离破碎,各栋建筑都不同程度的受到损坏,有的甚至已经塌陷,例如那座二十米高的先驱者雕像,威武的他现在只剩下一截小腿还伫立着。很多人在奔跑,更多的人在使用他们的能力,有学生,有教师,还有学院看护者,以及一大群从未在学院中出现过的人……地面的混乱一直漫延到天空才停止。
冬末春初的夜空静静的,没有任何东西。我抬头试图看到一颗能让我做出点判断的星象,但没有,只有被火光照红的漆黑在向我笑。
仿佛是我在策划这场华丽的混乱。
我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
是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