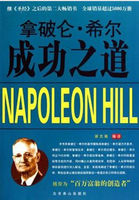星期天,当我帮着妻子把家务收拾妥当,抽身出门时,已是十点半了。在公交车上,我打电话问杨秀清在哪里碰头。杨秀清回答说:“雷家坡。”我心中暗想:这家伙,把珂家当自己家了呀!
到了雷家坡巷口,没有看见杨秀清。正在我左顾右盼时,却见马路对面有个时髦的女娃儿在对我又挥手又喊叫。我定睛一看,那不是王旎吗?由于过往的车辆太多,听不清王旎在喊些什么,但从她的手势来看,是叫我到她那边去。好在前面有一个地下通道,我就往前走去。当我钻出地面时,王旎站在我的面前,身边却多了一个杨秀清和一个皮肤白皙,带女娃娃相的小男生。王旎一把拉过那男生,介绍:“李成虫,我表弟,CD来的。”
“李成虫?”疑问还在我脑袋中打转,就听那男生气哼哼的说:“我叫李成龙,不叫李成虫,你不要乱说!”
“哦。”我向小男生点点头。
“他就是那个表侄,来渝州寻找余世乾老屋。”杨秀清说。
“今天我们三个保护他,免得龙龙遭劫色。”王旎猛踩小表弟。
“你们女娃娃才要遭劫色。”
“我们渝州的黑社会凶哦,你这种长得乖的娃儿,口袋往头上一罩,弄到山区去,一个要卖两三万!”王旎继续恐嚇李成龙。
“好了、好了,不要嚇人家了。”杨秀清排解两个年轻人“时间不早了我们出发吧!”
大家正欲抬脚,王旎一剁脚:“遭了,手机忘拿了!”杨秀清皱皱眉头,说:“还不快去拿,我们等你。”
王旎对李成龙说:“龙龙,陪姐走一趟吧!”
“我不,各人去拿!”看样子这个龙龙对王旎很是不满。
“走嘛,今晚姐陪你玩魔兽世界。”
“你?”李成龙一脸的不屑。
“你啥子你,姐是玩这个的高手!”说完,扯着李成龙就走。看着两个大孩子扯扯绊绊的走进地下通道,我和杨秀清不禁相视一笑。我对杨秀清说:“这样的事,怎么叫一个小孩子来?”
“这事难道很难?”杨秀清反问“不就是一个找到后拍拍照的事,何况还有我们帮忙。”
“也是啊,”我同意杨秀清的说法“不过,找到后的确没得啥子事,但关键是如何去找到。从时间上看,这座老屋经历了晚清、民国,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汶革,还有解放后的旧房改造,所以这老屋是否还存在,不好说啊。”
“这些古老的建筑被毁掉真的很可惜,它们身上蕴含着特殊的文化、特殊的人文精神,这些都是不可复制的。”杨秀清说。
“现在的高楼大厦,也是文化和人文精神的载体,但它的失败就在于从总体来看是重复的、雷同的。从渝州到深圳是一个样,从深圳到沈阳还是一个样!”
“也许再过几千年,人类面孔都是一个样了。”
“呵呵,那岂不是很可怕!”
一会儿,两个大孩子回来了。王旎一见我,就问:“林叔,我给杨叔叔淘的这套衣服怎么样?”王旎这一问,我才仔细打量杨秀清。只见他,一身时尚的休闲打扮,头发焗了油,面部皮肤紧致,双眼有神,一扫我在医院见到他时的那付萎靡神态。我拍拍他肩:“爱情的力量伟大啊,令我刮目相看喽!”王旎挽起杨秀清的手臂,骄傲地说:“那是哟,我妈凶得很!”(注1)
“不过,”我对王旎说“这套衣裳的确霸道,但是你杨叔经这样一打扮,太显年轻了,小心那些有大叔控的女娃娃把你杨叔勾走哟”王旎一听,竖起眉毛,举起拳头,问杨秀清:“你敢不敢?”杨秀清笑着连连摇头:“不敢、不敢!”我也学着王旎,做出一付凶恶状,举着拳头对杨秀清说:“你要是这样做了,我就把你打倒在地,踏上一支脚,叫你永世不得翻身!”许是我和王旎的表情太凶恶了,竟把李成龙嚇着了,他弱弱的说:“你们,你们……”杨秀清忙安慰他:“不要怕,不要怕,他们闹着好耍的。”我也安慰他:“我说的是汶革体,我和你杨叔年轻的时候,流行的就是汶革体。”
“****的时候你们就这样说话呀?”两个大孩子不解了,眼巴巴的望着我。杨秀清看着时间不早了,就说:“我们边走边聊吧。”于是,我们一行四人就离开雷家坡,向下半城走去。途中,我向两个年轻人解释汶革体。我说:“汶革体是一种说话的风格,具体表现就是激昂、粗俗、凶巴巴罢了。”杨秀清补充:“汶革体常说:打倒、砸烂、横扫。”王旎说:“你们那时候说话岂不是很费力?那样的词句非得吼出来才有劲。”我说:“是啊,是啊,中国人说话声音大,就是那时候养成的。”王旎说:“是吗?你这个说法有点意思哈!”
没走多远,我们就进入下半城了。渝州这座山城,其风格与平原城市迥异。古时候的人在进入这片两江环绕的山区时,都是选择有舟楫之利,取水方便的江岸居住,所以沿江两岸人烟密集、渡口码头繁多。即使进入近代,渝州开埠,外国资本和炮舰侵入渝州也是在江边设洋行、建兵营。当然,城市是发展的,人口越来越多,后来的人、穷的人就只好向山顶寻求安身之处。再往后,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有钱人也逐渐移居山顶,长此以往,也就形成了上半城。而江岸就顺理成章的变成了下半城。
注1:凶。在渝州话中,凶既可以作凶恶解,也可以作有能力、能力强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