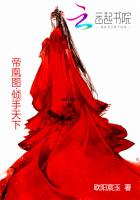老房是那种老式的五柱草房,静静地斜倚在大山深处,已经有好几十年了。有些板壁已经脫榫,有的柱子已开始朽坏,从上到下,房里房外,每一个地方都显示出破败不堪的样子,只有门前丛生的野树杂草,每一种都用它的绿叶青枝展现着生命的旺盛与倔强。尤其是那株枝桠交错的接骨树,每到盛夏,便伸开宽大的叶片,层层铺盖,精心编织,蒙古包似的撑在头顶,一个院坝几乎被它遮去了半个天空。坐在树下,尽可以无忧无虑地享受老房的宁静与岁月的美好。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做什么就只想什么,整个身心都仿佛被生命的绿意与真实浸透。满月的夜晚,沐浴着凉凉的微风,揣起一支竹笛,猴子似的爬到树上,一个人如痴如醉地吹上一曲《鹧鸪飞》,或一首《江南春色》,忧愁也好,困惑也好,都会在飘飞的音符中流淌得无踪无影······
父亲病重的日子,我每次回家,都要把他扶到树下坐坐,然后把香蕉一个一个剥好递到他手里,再把桔汁一勺一勺地喂进他的口中······在滴翠的绿荫下,在飘满槐花香气的风里,我就这样陪着年迈病重的父亲,陪他闲谈,陪他静坐,陪他十分钟二十分钟,陪他半个小时,让他在自己用手挖出来的、用背背出来的院坝里,尽情地享受着对他来说已是为时不多的天伦之乐。让他多看一眼自己栽下的那些银松,刺槐,泡桐和接骨树······那些日子,我总是要无话找话地问父亲:“爸,你想我吗?”他看看我,毫不含糊地说:“想。啷个不想?”我说:“那你就不要病吧。”他听我如此说话,竟然在转瞬之间伤感起来。这也许是他陪伴我三十多年时光中的第一次伤感,当然也是最后一次伤感。他哽咽了一下,停了一会,有些无可奈何地说:“啷个不病?人老了,没办法的事。”当我们说着这些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话时,我的眼睛早已一片潮湿,我的心也溢满无尽的苦涩。
在家里,我是父亲的次子,也是父亲最小的孩子。因此,记忆中的父亲特别慈爱,特别疼我。在他抚育我的漫长岁月里,从来没有责备过我,也没有呵斥过我,至于“棍棒底下出孝子”的故事,对我来说简直是一个遥远的传说。我做错事的时候,或是不听话的时候,倒是被母亲大加责罚,有时甚至用带小丁的竹枝抽打我光光的脊背,打得我一点也哭不出好声气来。
父亲是一个典型的贫苦家庭出身的人,十多岁就跟爷爷一起在煤洞中做苦力,进学堂读书自然是不敢奢望的事情,但意想不到的是,父亲竟有许多正宗而资格的故事。所谓正宗,是故事并非农村那种低级下流的插科打诨是的笑话;所谓资格,是说这些故事都源于中国古典小说的精彩片段。比如说比干挖心,比如说孙猴子大闹天宫等等。而父亲说得最多的,当然要算《三国演义》了。
农闲时节,天气晴朗的夜晚,父亲便找条凳子在院坝中坐下,把我叫到身边,揽在怀里,一边吮着那有些闷人的烟杆,一边跟我讲三国的故事。讲刘关张在桃树下磕头喝酒,讲司马懿吃了三个饼子后就收拾了魏蜀吴,讲曹操人马下江南,半边萝卜都吃不完······讲到精彩之处,父亲便会用一种奇异的腔板唱起歌来。时至今日,我依旧十分清晰地记得那些好听的唱词:
“盖世将军赵子龙,手提长枪好威风。
怀抱阿斗小太子,曹兵百万一扫空。”
那个时候,我也曾忽发奇想,自己要是能像赵子龙那样英勇无敌该有多好。
后来,我读书了,父亲便把他卖鸡蛋凑来的钱给我买了一部《西游记》和一部《三国演义》,他说还要给我买一部《封神》,但由于街上没卖,所以终于没有买成。这两部书,虽也像那间老房似的破败不堪了,但我始终舍不得把它丢掉。直到现在我仍然很好地把它珍藏在自己十分拥挤的书柜里。每次打开书柜,我总要把它抽出来翻翻,翻阅它,就像翻阅一段我今生再也不会多有的记忆······
父亲一生清苦,几十年奔波忙碌仍无半分积蓄,直到去世时也只留下一间破败不堪的老房。老房太小,一进两间。大哥成家之后,我就只得搬到楼上去睡了。那年月,父亲为了供我上学,穷得连床也买不起,所以我就在楼板上铺一层麦草,用荞壳装个枕头,加上一床补了又补的被子,就算我夜晚的栖身之所了。父亲想我,他怕老蛇吓着我,怕耗子咬着我,就不顾年迈体衰腿脚不便,爬楼下楼陪我睡觉。每天晚上,他都要叮嘱我把枕头放平,把被子盖好。到了冬天,只要我一上床,就把我冰冷的双脚捂在他温热的怀里······
时值今日,父亲虽已离我远去,但那间与他几十年相依为命也为我遮风挡雨的老房依旧倔强地横卧在高原深深的山里。在老房中,还住着我白发苍苍的母亲。每到周末,无论多忙,我都要回去看看,看看那间老房,看看步履蹒跚的母亲,给她背两缸水,和她说几句话,陪她吃一顿饭。在那棵巨伞一般的树下,有我,有我和母亲雕塑般的身影,在大树旁边,还有我父亲一般的老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