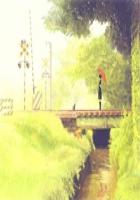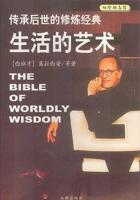“什么?非正常?为什么?”她呼吸渐渐急促。他靠在沙发上,右脚搭在左脚的膝盖上。“医院的病历,死因不详。检查结果是呼吸器官衰竭,其它器官较健康。”说着,他不确定地抬头望着她的眼睛,想确定她是否接受得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奶奶一个练武强身的人会器官衰竭致死。”她倔强地抬着头,眼里没有任何害怕,更多的是坚定,是勇敢。她眼里有泪,有难过,但更多的是坚强,是信念,是勇气。他看到了的,他看得到的。所以,他决定告诉她一些事情。
可就是现在这一个倔强的女孩,在几个小时之前还是那样一个在门前哭得眼红等待帮助的女孩,却在这几个小时之后成熟成长了起来。是什么?或许,是她在这几个小时之内,失去了自己最有力的依靠。
“来,到二楼来。”他再次看向她清澈的眼眸,希望从中找出一丝不愿意。依旧没有。她没说好,也没说不好,就那样淡淡地跟着他的视线。
他直起身,拿起桌上的纸包和瓶子,一路走,一路往纸包上喷液体。她只默默地跟着,不再说话。反倒让黎明感到奇怪,犹豫自己该不该告诉这个女孩人性最丑恶的一面。就是她这种表现,让他觉得后悔了。就这短短的一段楼梯,他回头看了她几次,她只是低头走路,不再说话。
走到房间门口时,整层房间的香甜味道已经被另一种香味所覆盖,虽然都是香味,可却都截然不同。她比较喜欢黎明手上的那种香味。
“要进去看看吗?”他边戴手套边问。语气里带着一丝小心。他看着她的眼睛,依旧没有任何波澜起伏,默默地,点了下头。
她安静得让他出乎意料,也让他有些受不了和担心。她低着头看他帮她套上手套和鞋套。感受到她冰冷的手之后,他狠狠地皱了皱眉头。
尾随他进去,不大不小的房间里布置得很简朴。当时,门是反锁着的,锁显然是坏的;窗户是从里面关起来的,窗台上放着一盒用完的熏香;床上的被褥叠得很整齐,床单也没有褶皱,显然没有人躺过,床脚下也放着一盒熏香,香分子还在缓缓运动;床头有一个梳妆台,上面规矩地放着一把复古的木梳,上面还残留着几根银发;靠墙的一边放着一个大衣柜。
“现在你知道为什么我说是非正常死亡了吧?”他得意地看向她。“嗯,”她仿佛找到了寄托和希望,终于愿意说话了,“门窗都是从里面反锁的,说明奶奶就是在室内死的;床上的被褥叠得很整齐,说明奶奶是在睡之前或是醒之后遇难的;但如果奶奶是在睡之前遇难的话,她应该没有点熏香就已经死了,那么在现场就不会有情景中出现的正在燃着的熏香了,那如果奶奶是在醒之后死的话,一切都说得过去。可凶手忽略了一点,那把梳子,奶奶是不会用来梳头的,那可能是对她很重要的东西,平时她都用来把玩,从不会用来梳头。所以,他只是为了给我们一个自然死亡的假象。我说得对吧?”她双手托着下巴,问一边专心搜集证据的黎明。
“嗯,目前来说就是这些,你很聪明嘛!可以作我的秘书啦!”他把窗台上一些白色粉末用镊子引到袋子里,“更为深入的,还要看这些。”
“可是,凶手怎么出去的呢?我解释不了。”林清涟嘟着嘴巴问正在下楼的人。
“如果你以上推理是正确的话,那么凶手应该是在我们走后出去的吧。”他到门边专心地寻找线索。
“诶,怎么?你会认为一个杀人犯在大白天会从大门光明正大地走出去不成?”她看似漫不经心的一句话却说到重点了。
“这里还有没有可以直接出去的地方?”他站起了,直愣愣地看着她。
“有啊,有个天窗,在楼顶。”她指了指头顶。一个人影立马从她身旁掠过,直奔顶楼。
她连忙追上,“等等我!”待她气喘吁吁地叉腰站在他身边时,就发现他在对着一个打开的天窗发呆。她随着他的目光看去,一个钩绳安静地躺在那里,已经没有了人影。
他什么也没说,也没有叫她,自顾自地下去了。他三阶三阶地上,却一阶一阶地下。直接倒在沙发上,闭目养神。
她以为他累了,然后就说:“你累了的话就睡一下,我烤蛋糕给你吃。”走过去系上围裙,将披散着的长发用橡皮筋束起来,又精心地剪了指甲,仔仔细细地洗了手。然后开始熬糖浆。
沙发上的人突然就坐起来,到底少了什么?到底忽略了什么?哪里没有想到什么?想着想着又重新去了一遍楼上。
下来时满眼杀气,一个房间里的两人各怀心事。一个认真地切芒果,另一个也仔细地对照指纹和研究。安静得不像样子。
“林清涟!”一声怒吼打破了宁静。她抬起头来看着情绪多变的狮子,明明他刚刚还在……
“你到底有什么目的?为什么那盘熏香上有你的指纹?那些粉末是干冰对吧?可以加快气体挥发,这样就可以让那盘有毒的熏香在天亮之前燃完,对吧?你说啊!你告诉我你奶奶从不用那木梳梳头,把它当宝贝是为自己开脱对吗?可你知道吗?那木梳上很多脏东西和密密麻麻的指纹,要是把它当宝贝,不会用水或酒精擦拭的吗?你一直干扰我到底有什么目的?”可能因为自己经历过太多背叛,所以对于这些十分敏感。
依旧安静。她背对着他,端着盘子的手狠狠地颤了颤,强忍住难过,默默地站着。她曾那么信任他,可他……
“你说话呀!我说对了吧?”他冷笑。
林清涟一惊,手上的盘子最终掉到了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