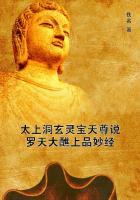“不止我们,这些是所有医疗保健系统共同面临的难题。”他说,“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过去十分擅长保持较低的开销,但是正因如此,医疗的质量很低。人们要求缩短看病等候的时间,要求改善癌症的治疗方法,因此开销也大大增加。我们的公共医疗服务系统尝试了各种方法去支付医生和医院费用,有些很成功,也有些失败了,但不断尝试是非常重要的,不只是对英国而言,对全世界来说都是如此,因为其他国家可以从中学习经验。”
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总是依靠税收来支付医疗费用,这在将来可能成为一项难题,因为你不可能再提高税收。其他国家,包括美国,面临的困难甚至更大,因为他们的医疗效率太低。
“美国(国家老年人医疗保险制度、医疗补助计划等)比英国在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上的支出更大,而且我们的体系涵盖了所有人群,而美国只向老年人和穷人提供医疗保险。”皮尔森先生说。
“这是因为英国在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上的开销比美国更有效率。在英国,私立医疗服务并不是很多,目前英国拥有世界上最公平的服务体系,不论病人是穷人或富人,他们得到的医疗服务都是类似的。”这是一位英国急诊医生的观点,他的笔名是尼克·爱德华兹医生。在他的《忍俊不禁:一名急诊医师生活中的起起落落》一书中,爱德华兹医生说真正有需求的病人都会得到很好的服务。他记录了一位50多岁的老人在心脏停止跳动13分钟后,被送到急诊中心的案例。老人做了手术,打开被堵塞的心脏血管,装进了一个心脏起搏器,为防止他的心脏再次停止跳动,还有家庭医师和一组物理治疗师为其进行后续的不断护理。爱德华兹医生在他的书中写道:
“十年前,他就可能死了。现在,由于医疗技术的进步和公共医疗卫生服务更多的资金供应,他能够过完完整的一生。在此情况下,我们就不会质疑病人有没有保险,或是有没有能力为他的治疗支付费用。我们不会在意他是百万富翁还是靠领取救济金生活。我们所想的就是让病人能够好好地走出医院,不仅是活着出院,而且要让病人重新过上正常生活。”
每年有300万人使用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就医。调查显示,人们通常很满意自己得到的照顾。但是由于健康保健预算的压力和工作的削减,有些服务项目已经面临压力,一旦出问题,后果可能很严重。格兰瑟姆的一位年轻妈妈米凯拉·史莱尼认为,她的儿子两次被地方医院拒绝就应归责于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削减开支。
杰登,一个七个月大的小孩生了病,腹泻发烧,米凯拉送他到急诊就医时,被一个接待员拒绝了,他说小孩不需要看医生。
“所以我把他带回了家,因为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她回忆说,“第二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杰登躺在那里,一动不动,眼窝深深地陷了下去。”她赶紧又带他去了医院,但还是没能得到治疗。“医院的借口是,这是个复活节的周末,医院人满为患,他们很忙,人手不够,而这就是杰登无法得到治疗的原因,他们太忙,没空管他。我真的是在祈求帮助了。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医疗保健服务。你站在那里哭着说‘我的孩子生病了,能不能帮帮我?’然后他们说‘不’。”
第二天米凯拉终于找到一位医生给儿子看病,这时他们才发现杰登病得不轻。“医生晚上十一点的时候到的,他说孩子已经脱水很久了,他的身体就要停止运转了,这就是他一动不动、眼窝深陷的原因。而我只能瘫在那里,看着我的孩子一点点走向死亡却无能为力。”幸运的是,杰登恢复得很好,现在是一个健康的两岁孩子。但米凯拉还是对自己的遭遇深感气愤。“你不会想到你会被拒绝。从小到大,你总是认为如果你出了事故,或是感觉不舒服,你可以去看医生和去医院,我们一直都是这样认为的。现实却是我求他们帮助我,他们说不。”
由于上述原因,中央政府提供的综合医疗保健服务在西方将不能长久地存在下去。人们不仅不满其开销,还不满由大型非个人官僚政治控制的较低服务效率。但对于那些享受过1948年前医疗卫生服务的人来说,这一服务的质量显然是有所提升的,且价格更低廉。向前看,我们能够预期医疗服务回归本地化,当地政府负责筹集资金,并组织本地医疗服务,这样做对市民也更加负责任。另外,政府还需要想办法管理人们的期待值,在未来,人们可能需要自己购买保险,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从治疗普通感冒,到整形手术都是免费的。
安东尼·丹尼尔斯(AnthonyDaniels)
安东尼·丹尼尔斯是一位监狱医生,也是一位精神病学家。他以西奥多·达尔林普尔(TheodoreDalrymple)为笔名,在美国和英国的医学期刊和报纸上发表过多篇文章。他还写过很多书,包括《底层生活:导致下层社会产生的世界观》。
福利和世袭阶级文化
在威尔士的小镇拉内利,唯一的经济活动就是对贫穷和失业人群的管理。拉内利管理者的主要职责就是处理社会问题。你走在大街上,见不到任何一种形式的经济活动,也没有人试图改变这种情况。让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拉内利的一个人说:“我要去烤蛋糕,而且不仅烤蛋糕,我还要在拉内利镇中心卖我烤的蛋糕。”在多长时间内会有人将他拖走?十分钟,或是十五二十分钟?要不了多久,这种形式的经济行为就会遭到种种条条框框的扼杀,自然而然人们的反应要么是绝望要么是充满仇恨。
根据政府的宣传册子,他们没有任何憧憬,也没有丝毫恐惧。请问,当一个人没有希望、恐惧和甜点的时候,生命还有什么意义?如果你觉得自己做的任何一件事都不会带来任何的改变,那还有什么动力?我是说,之所以英国2011年夏天出现暴乱分子并不是因为他们一无所有,而是他们认为他们没有资格拥有任何东西,多么可怕啊,因此我很同情他们。
英国社会一直都是非常讲究阶级的社会,但是现在它给我的感觉是一个如同印度种姓制度的社会。打个比方说,我的父亲出生在一个受轻视的阶级,但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别人的帮助,还是获得了一定的成功。
但那是20世纪50年代的事了。如今的现状是,社会流动性好的证据在于穷困的少数人群如何通过奋斗和适应获得成功。《卫报》的一项调查显示,许多少数民族群体在英国生活得都非常好,尤其是锡克人和犹太人。这两个族群的人们——有着非常相似的历史——他们来到这个国家,并不很受欢迎,虽然制度上法律上没有歧视,但人们普遍对他们持有偏见。他们作为移民来到经济上相对开放发达的英国社会,经过一代人的艰苦创业他们在经济上文化上都提升到一个非常高的层次,取得了各种各样的成就。
我亲眼见证了这一点。伯明翰的贫民窟有一家锡克人——我觉得这是个英雄成长的故事,非常典型——这家锡克人,英语并不流畅,他们经营着一家卖酒的商店,在那样一个地方经营商店我相信一定很不容易,很可能常常遭到欺侮。而如今他们四个孩子都长大成人:一个是医生,一个是核物理学家,一个是某家医院的护士长,还有一个是会计。我觉得这些父母和他们的孩子一样有智慧有天赋,但他们牺牲了自己的一生来换取他们的孩子在我们的社会中获得成功的机会。
为什么这样的故事在传统的英格兰米德尔斯堡(英格兰的一个城市,那里的人们大多依赖福利救济,犯罪率也很高)不能复制呢?当然,这可能是智商的问题,但更多的原因在于头脑和心灵上的枷锁。如果你认为自己所在的社会是一个不公平又封闭的社会,你就不会试图改善你的情况,社会就会变得更加封闭和没有公平。
我曾经有一次乘坐非洲的公共交通从桑给巴尔岛到廷巴克图旅行,一共花了六个月的时间。我在那里看到了英国贫困地区人们所没有的人格尊严感。我觉得这和英国的贫困地区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贫困不是物质上的贫瘠而是精神上的。所谓精神上的贫困就是没有方向感,看不到改善和努力的必要,毫无进取心,也什么都懒得做。
我曾在伯明翰一个比较糟糕的地方的一家医院工作过,那里的社会病态程度和失业率都非常严重。我们这里曾经有很多实习生和年轻的医生,大都来自菲律宾或印度。他们一开始觉得我们的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体系非常好——即使最穷困的人也能得到最好的医疗服务。但是很快他们便意识到这些人所受到的精神压制比孟买或马尼拉的人们更为严重,总体而言,我们的社会还不如他们的社会,因为在这里人们缺乏自信、尊严,也不具备应该和能够对自己负责的最起码的意识。
我父亲在伦敦东部出生的时候,该地的平均寿命为47岁,他所在区的婴儿死亡率为千分之一百二十四,比现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还要高。即便当时的社会条件非常不好,但是人们很有目标,他们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终会有所收获,他们属于一个有信仰的国家,不管这是好事还是坏事,人们的确相信自己的国家是个很好的国家,能够将法治理念介绍给他国的国家,一个先进的国家。
大卫·格林(DavidGreen)
大卫·格林是成立于2000年的西维塔斯智囊团的理事。
他曾经任职于经济事务研究所,该研究所在20世纪80年代对撒切尔首相和里根总统有着很深的影响。他的著作有《合作的利己主义者:教育和福利改革》等。在他最有影响力的《重塑公民社会》一书中,大卫·格林指出,过去的福利和社会安全体系虽然也存在缺陷,但比现在这个将过去取代的福利国家体系更有效也更公正。
福利国家如何瓦解人们的责任感
长期以来,地方社区和协会出现后都会承担各自的责任。大家都认为济贫法(福利体系的雏形)出现在伊丽莎白时期(17世纪),但事实上,更早的时候已有相似的法律出现。有些人甚至追溯到盎格鲁-撒克逊时代,那个时期我们都属于某一个社区,社区有责任保证没有任何一个人陷入赤贫。这种责任感非常强烈,和现代社会中福利权利的思潮完全不同,在现代社会,福利就是给你一定的补贴,足够你生活,只要你活着,不管你做什么都可以。所以,换句话说,从伊丽莎白时代晚期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直都存在一个国家维护的安全网络,使得人们可以对自己的生命负责。在济贫法的规定中,福利是社区的责任,由地方执行。为了提高福利水平,人们自己还成立了互助协会。
互助协会有一位主席、一位副主席,还有执行人员及其他成员,任何人都有机会成为组织中的一员。比如你有一份非常平凡的工作,可能是工厂里劳累的工人,当然许多人都从事这样的工作,而到了晚上你去参加每两星期一次的政策例会时,你就成了个人物,你的领班不再能够对你呼来喝去。你成了官员,有自己的职权和职责,这种认同感和重要感是非常重要的。这丰富了人们的生活,也加固了一系列道德原则,因为这和人们独立自主息息相关。那时,大多数人都有自己的家庭,如果一个男人抛弃了自己的妻子,人们就会对他嗤之以鼻。所以互助协会的作用很广泛;它是个人责任和相互作用相互关系的结合体,它打造出能够取得巨大成就的人才,结果也确实如此。
互助协会尤其能将社会中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因为它能够发挥个人能动性,也容易让人接受。互助协会可以防止许多人面临失业、生病、无法工作,以及防止个人承担所有和医院有关的费用、医疗护理等风险;还负责保障失去丈夫的妻子和成为孤儿的孩子等。人们曾经认为防止这些可能性都是个人的事,但对很多人来说,这根本不可能实现,所以他们创建组织,共同合作。这不仅增强了个人责任感还加固了相互关系,通过唯一的途径,即相互作用加固了相互关系。由此看来,我们已经失去了太多。这都是统一福利和集中福利这一变化对英国社会造成的结果。
一位著名的记者去米德尔斯堡和那些要求福利的人谈话,他们说觉得自己有权利要求福利。记者说:“但是你本来可以去工作的。”这些人回答说:“好吧,但工作并不值得我去花费时间。如果我去工作,比如四十小时,我就能赚很多英镑,但那样我每天早上六点十分就要起床,一个星期我就赚十英镑,也就是说我这样辛苦就只是为了那十英镑。”
这是一种非常自私的态度,这是在利用体系为自己攫取更高的利益。人们没有任何责任感,觉得自己不应该去工作,而且没有任何羞耻心,人们总是想着:“如果每个人都持这种态度,我持不一样的态度合理吗?只有我去工作这样好吗?”如果你想从互助组织得到福利的话,你得先得到分支机构的许可,这些机构的人就会说:“可是你本可以去工作的呀!”
现在劳工党内部正在探讨是否应再次回到贡献式福利的老路上来。你必须为组织创造空间,首先这些组织必须为人们所需要,如果不被人们需要就不会出现。如果我们要再次创造贡献式福利,就得有对其的需求,并由地方进行管理。那么相似的机构就会再次出现。
实际上,要回到曾经的社会体系并不容易,因为现如今,我们希望国家能为我们做任何事。所以如今的集体行为就是要求别人做事。人们仍然会参加各种各样的协会,但这些协会都不是集中力量、通过自己的努力解决自己的问题的协会。这些协会要求政府做事,是施压的组织而不是自我帮助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