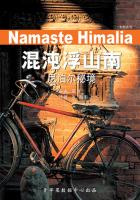我倒了两趟火车才来到阿格拉。可能是旅游业太发达的原因,阿格拉街上到处都是油嘴滑舌的“皮条客”,还有追着要卖你明信片的小孩。我从车站搭了辆三轮车去旅馆,司机堵在门口拼命向我兜售旅游线路,我比任何时候都感觉自己像一个“行走的美元”。一个印度人问我要烟抽,我给了他一根,他点燃后猛吸几口朝天喷了一口烟,咧着嘴说:“在这里,有钱就能办任何事。”这些让我对阿格拉的印象非常差。
然而当我在旅舍的阳台上第一眼看到泰姬陵时,却震惊了。纯白的泰姬陵就这样屹立在天地间,和周围破烂颓败的环境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它美得如此不真实,美得不可方物,美得让人不敢相信它是一座坟墓。
泰戈尔说泰姬陵是“永恒面颊上的一滴眼泪”。泰姬陵因爱情而生,17世纪莫卧儿帝国的皇帝沙·贾汗在他的爱妃阿姬曼·芭奴的死讯传来后,悲痛无比,动用全部国力花了22年时间为爱妃建造了这座绝美的陵寝。沙·贾汗本想在朱拿木河对岸为自己再造一座同样的黑色陵墓,然而晚年他被儿子奥朗则布篡去皇位,软禁在阿格拉堡,每天他只能透过小窗,孤独地眺望泰姬陵在河里的倒影,最后他在阿格拉堡郁郁而终,被合葬于泰姬陵,葬在阿姬曼·芭奴的身旁。
早上6点不到我就出门了,想赶在游客大潮涌来之前静静看一会儿泰姬陵,然而泰姬陵门口早已排起了长龙。我掏了到印度以来最贵的门票钱,外国人门票750卢比,折合成人民币约100块,前面的一个印度阿姨拿着票朝我龇牙一笑,她的票上赫然印着“20卢比”,印度人只用付两块五毛钱!我气得跳脚,恨不能把脸涂黑披件纱丽去买票。
走过高耸的红色拱门,整个泰姬陵还罩在一层迷雾里。庭院里树木郁葱,一条清澈的水道通往宏伟壮观的白色陵寝,浑圆的洋葱穹顶,四周四座细高的尖塔和方形的殿堂一起托在高高的台基上,它们的存在如此和谐,就像建筑的每一部分都在互相呼应。水道前摆了一条长凳,戴安娜王妃曾经在这里坐过,后来所有游客都想在上面坐坐。走过庭院,赤脚踏上白色的大理石,天已泛出微蓝,太阳慢慢爬出地平线,泰姬陵不再只是白色的了,它像一块冰雪,在阳光的刺射下颜色纷呈,绚丽夺目。我贫乏的语言是不足以形容泰姬陵的美的,它的美只能你亲身去看。
我摸着雕花的大理石,绕着殿堂转了一圈又一圈,跑到沙贾汗和他爱妃的石棺前凭吊了一下。一个美国人跟我说,当她第一眼看到泰姬陵时,她的泪水夺眶而出。我也努力想为沙·贾汗和阿姬曼·芭奴的爱情掬一把感动的泪,却发现这个很难,这里的游客实在太多,非常不利于培养情绪。7点一过,殿堂里就人挤人了,8点,泰姬陵已经被游客和相机的咔嚓声淹没了。我心愿已了,一刻都不想多停留,马上收拾包袱搭车去斋浦尔。
印度菜的精华:把一切捣成糊状
印度人总是说“马上就到了啊”,结果车子开了8个小时,到斋浦尔的时候天已黑,我和车上的一堆傻老外站在街头,马上成了旅馆“皮条客”的目标。
我试图弄清楚自己在哪里,一个老外掏出手机使劲刷谷歌地图,指给我看,“我们在这里!”“棒!那去旅馆街怎么走?”我问。他摇摇头,我白了他一眼。皮条客说:“20卢比就带你们去很棒的旅馆。”
老外单纯啊,他们噌噌地跳上车,我不得已,只能跟他们同去看看再说。我们一窝“猪仔”被押到一间开在路边的吵杂旅馆,单人间要价400卢比。
我看了一眼扭头就走,在路边拦了一辆人力三轮车,指着指南书上推荐的一家旅馆说:“我要去这里。”
车夫满口应承:“好好,30卢比就够了。”我跳上车,结果车夫骑都没骑,只是推着车子走了几步,跟我说:“到了。”我抬头看,还真到了!我恨恨地把车钱丢给他,他还在后面叫:“再给点小费嘛!”
我成功地在巷子里找到了一家廉价旅馆,单人间150卢比,房间宽敞又干净,还有热水洗澡。旅馆老板的弟弟没事就在二楼的平台上放风筝玩,经营着一家几近倒闭的银饰店,他卖得那些镶嵌着各类“宝石”的银戒指,都只卖200卢比一枚。他卖的太便宜了,便宜得我都忘了到斋浦尔干吗来了,天天就泡他店里选戒指。不过跟他买东西也十分痛苦,他是穆斯林,经常杀价杀到一半,他就跟我说:“你先出去一下,我要做祷告了。”
巷子口的一家饭馆看起来生意很好,不管在哪,找热闹的饭馆吃饭总不会错。我进去点了一份黄油鸡。印度人做鸡肉特别好吃,尤其是烤鸡,烤得外焦里嫩,蘸着盐巴和柠檬汁吃,美味极了。结果这黄油鸡一端上来却吓了我一跳,盘子里一摊厚厚的红色糊状物,我扒拉了好一会儿,才把埋在底下的鸡块找到,我想大概全世界只有印度人能看出来这是什么,别的国家的人会把这个当作一盘呕吐物。印度人做什么吃的都喜欢捣成烂泥,在印度餐馆,你是看不到绿叶子的,因为所有蔬菜都被他们捣成了糊糊,如果你点了蔬菜咖喱,那么端上来只会有几颗绿豆子还依稀可辨。这黄油鸡也是如此,所谓印度菜的精华,应该就是糊状。
因为满大街的房子都刷成了粉红色,所以斋浦尔又被称为“粉红之城”。这座城市最著名的建筑物应该就是风之宫了,我拦了一辆电动三轮车,习惯性地准备杀价,结果司机拿出一张表,指指计价器,乖乖,我还是头回在印度坐到愿意打表的三轮车,斋浦尔的印象立刻加分。
风之宫与其说是一座宫殿,还不如说是一块屏风,或者说是一面墙,这面墙上密密麻麻开了九百多扇窗户,这一定是为什么它叫风之宫,因为很通风……据说这些窗户是为了给古代的宫女们偷看外面的花花世界用的,厚厚的红砂岩墙壁上凿满了八角形的小窗格,我躲在一扇窗户后面,看着楼下车来车往的街道,据说在古代,从风之宫往外看,就是一个热闹的市集。多数的旅行者到了粉红之城斋浦尔都会再往西边的沙漠走,去往“蓝色之城”焦代浦尔和“白色之城”乌代浦尔,我却从斋浦尔折回了新德里,我在印度已经待了太久,觉得是时候离开了。
我要去哪个国家呢?在新德里那一个星期徒劳的奔波使我认识到,如果继续试图去敲各个大使馆的门只会浪费我的时间,我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找一个能落地签的国家。我在网上查阅了一大堆资料,想要找一个进入中东的突破口,最后锁定了一个国家,那就是黎巴嫩。
我几乎是咬着牙才把机票买定的,因为虽然持中国护照可以落地签黎巴嫩,但这个落地签是有条件的,它需要离境机票、2000美金的现金和酒店预订,我在网上查到,一些人说他们飞黎巴嫩落地签,结果在机场却被拒绝登机,或者原机遣返。我既没有离境机票,也没有足够的现金,意思就是,我的机票也很有可能打水漂。我只能放手一搏。
我在新德里给京苏发了封邮件,说我要离开印度了,结果她连夜坐车从瑞诗凯诗赶回来,要给我送行。我在新德里并没有闲着,我用电脑软件做了一张假的离境机票,还换了30张面额10元的美金,我把它们整齐叠好,夹在两张百元美金中间,用透明的塑封袋包好。正常情况下,我会在明天飞抵迪拜,在迪拜转机,后天到贝鲁特,又得去睡机场了。我只能祝自己好运。京苏一听我要去黎巴嫩就咯咯笑,对她来说去黎巴嫩这种国家的想法真是太奇怪了,她问:“世界上那么多国家,你为什么要去黎巴嫩呢?”我只能语重心长地回答她:“我的护照就只能去那么几个地方。”最后一晚在印度,结果我却开始腹泻,几乎虚脱,完全没有力气,京苏看着我躺在床上,她比我还焦虑,跑前跑后给我端茶倒水,还给我买药和食物。我说“:京苏,我已经没有卢比可以给你了。”她笑着说“:这是给你的礼物。”我和京苏从尼泊尔到印度,一路相伴,她是个脾气特别好又特别仗义的人,有时我会因为一些小事火冒三丈,而她总是在一旁默默地笑着看我发火,她是我在旅途中收获的最亲密的一份友情,她的善良和忠诚让我感到受之有愧。
再见了,我的朋友。再见了,印度。关于印度,我特别喜欢《地球步方》上的一段话“……印度——‘众神与信仰之国’……但是,如果那里是天堂,我们所在的就是地狱吗?如果将那里称为地狱,我们这里就是天堂吗?”印度,上一秒钟你恨死它,下一秒钟你爱死它,所谓印度的诱惑是也,如果说人有一生中必须要去的一个地方,那我觉得就是:印度。
PS“离境机票”蒙混过关
新德里机场,在阿拉伯航空的柜台办登机手续的时候,值机人员问我要离开黎巴嫩的机票,我双手奉上用软件自己PhotoShop的“机票”,这是一张从黎巴嫩飞往伊朗的假机票,他起身拿着这张“离境机票”去问领导,我努力告诉自己要镇定。不一会儿他回来了,把双程机票都给了我。托运行李时他提醒我说:“行李是直接运到贝鲁特的,你确定你要这么做吗?”我想他是在暗示我有可能会在迪拜被拦下来。“确定。”我回答他。
这班飞往迪拜的航班就只有我一个背包客,其余全是一些看似贫穷的印度人,估计都是去迪拜做工的。飞机预备降落,我透过机窗,看到地面上沙漠里整齐划分的街道,矗立着的形状怪异的高楼,迪拜看起来就像一座科幻之城。飞机降落在沙迦机场,离去贝鲁特的航班起飞还有十几个小时,沙迦机场还真的是破啊,看起来连国内某个二线城市的航站楼都不如,我逛了一圈,发现一瓶水都要卖5迪拉姆(约8元人民币),快渴死了,为了买水喝不得已换了5美金,结果回来就找到了水只卖1迪拉姆的自动贩卖机……心都碎了。如果说有什么让我意识到自己来到了中东的话,那就是浑身都罩在大黑袍子(布卡)里的女人,有些把脸也遮了起来,只露出了一双眼睛,更有甚者,连手上都戴着黑手套。她们每个人都把自己遮得严严实实,看起来毫无特征,我几乎无法辨识谁是谁,我心想,就算迪拜再有钱,服装产业在这里也是毫无用武之地的,因为每个人都穿得一模一样啊!然而一进到盥洗室我就发现我错了,她们掀掉黑袍子和面纱,露出精心修饰的波浪卷发,脖子和手上都套着亮闪闪的首饰,对着镜子涂着口红,台面上最新型的手机叮铃铃地响着。她们梳洗完毕,又重新罩上黑袍子,迈出盥洗室。机场的每间盥洗室边上都有一个祈祷室,里面暖和安静,地上铺了地毯,这倒是个睡觉过夜的好地方。虽然我知道这么做不靠谱,但是脸皮的厚度和旅行的长度成正比,慢慢地人就豁出去了,我找了块布把自己一包,往角落里一缩,心想能蹭几个小时是几个小时。里面还坐了几个黑袍子女人,其中一个在柜子里翻出一本中文的经书递给我,我接过经书就顺手往头下一垫,她们看着我,脸上一副恨铁不成钢的表情。
刚开始她们还在很虔诚地祈祷,不一会儿也横七竖八地躺下了,一个女警模样的人冲了过来,站在门口冲她们大声嚷嚷,我从她的手势看出来,她的意思是“这里不许睡觉,都给我出去”。那几个女人不甘示弱,和女警互吵,先是说着我听不懂的阿拉伯语,后来突然时空转换两边都说起了英语,女人说:“阿拉在看着你!”女警也说:“阿拉在看着你!”我爬起来,默默地离开了祈祷室。
我在大厅里躺了一宿,夜里数次冻醒,这是我这一路睡过的第三个机场。终于等到去贝鲁特的航班起飞,登机口的一个工作人员把我拦住了,他看了下我的护照,问我:“你有现金吗?”他问得非常有礼貌,我掏出我包好的那叠美金递给他,他只是捏了一下就还给了我,“这里有多少钱?”他问。“大概1500吧。”我面不改色地回答,其实我这叠美金只有最外面的是100美元的,中间的全是10美元。我就这样登上了从迪拜飞往贝鲁特的航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