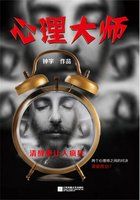李守文个子不高,身材比例也不协调,头大腚肥,身长腿短。李守文挑着货郎担子走街串巷的时候,远远望上去,就像个吊线木偶,因为腿太短,看不出他在走路,只觉得他整个身体在往前平稳滑行。李守文祖籍丹阳,读过两年私塾,后来跟着他舅舅到上海做小本生意,并由舅舅介绍加入了共产党。入党之后,组织上安排李守文去陕北根据地,在那里接受了一系列的培训,从跟踪到反跟踪,从侦察到反侦察,从枪械射击到徒手格斗,从传递情报到密码编排等等。数年之后,做小买卖的李守文被磨炼得有胆有识,知进知退,已经成长为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的一员得力干将。当日本铁蹄在中国肆虐之际,共产党人也在积极布局,于敌占区成立了无数个小分队,负责敌情侦破、情报传递,关键时刻也可以直接参与对敌作战等任务。李守文是安阳小分队的队长,建队两年多来,从未办砸过任何经手任务,深得上级器重。自从文官村出土了后母戊鼎以来,上级的情报指示一条接一条,先是从河南临时省委划拨来了五千块钱,让李守文购买下铜鼎,然后就地藏匿并实施保护。这几年来,李守文虽说见多识广,但是从未见过这么多现钱,而且拿这么多钱去买一只铜炉子。随着上面过来的情报越来越多,他方才明晰,铜鼎里面蕴藏着一个惊天秘密,是晚商时期三代帝国的财富藏宝图。李守文对于铜鼎是一幅藏宝图这个说法,一直将信将疑,觉得像是小时候听老人们讲过的故事。而上级的情报部门似乎也不太确定,只是说从日本方面得知,该铜鼎乃晚商三代帝王的藏宝图……上级只确定了一点,那就是务必保证此铜鼎不得落入日本人手中。如今,罗宝驹竟然亲自驾着马车,把铜鼎送到了日本宪兵队,这让他如何对上级交差。
罗宝驹对李守文印象不错,便耐着性子,把事情来龙去脉说了一遍。李守文倒也豪爽,说:“八条人命当然比个破铜炉子值钱,可这个炉子不是普通炉子,如此大的物件,堪称国之重器,绝不能因为我辈无能,落入东洋倭寇之手。另外,我这边得到的情报,说这个铜鼎是一个藏宝图,日本人急于得到这笔财富,用来扩充军费。所以,此事非同小可。”
“俺没有想那么多,就是觉得中国的宝贝不能让日本拿走,俺正在想办法,没准到时候还需要李先生出手帮忙哩。”罗宝驹说。
李守文抓着罗宝驹的胳膊,说:“如今,这个铜鼎已不是你一个人的事了,它成了咱们全中国人的事了,你下一步有什么想法得说一声,我脑瓜子里就算是个空心球,仨球总比俩球强吧。”
“既然李先生这么爽快,俺以后麻烦到你,也不用不好意思了。”
通宝街上,罗宝驹的弟兄们又开始干起往日的勾当。安顺子盯上三个日本人,已有小半天。在一个僻静处,安顺子走上前去,从怀里掏出一个康熙粉彩盘子,一个留小胡子的日本人伸手接过盘子,在放大镜下看了一会儿,扬起手来把盘子扔上半空,“啪”的一声掉在地上摔个粉碎。安顺子也不气恼,笑嘻嘻冲着小胡子伸出大拇哥,说日球真鸡贼!另一个穿西装的日本人一把抓住安顺子的衣领,问他为何骂人?安顺子急忙解释,说自己夸赞日本人眼光贼,就是有眼力。另一个戴眼镜的日本人稍显温和,劝开了穿西装的日本人。安顺子又从怀中掏出一个物件,说:“看你们都是识货的人,就给你们点真宝贝瞧瞧,看!明朝的日本短刀,怎么样?”
三个日本人同时眼光一亮,这竟是一把日本武士佩戴的短刀。小胡子拔出短刀,发现的确是手工碎锻的复体暗光花纹刃,刀身上刻着五个字:“山口刀锻冶”。西装日本人和眼镜日本人盯着小胡子的眼神讨结论,小胡子用日语说:“这不是短刀,而是介于打刀和短刀之间的胁差,这个中国人是个骗子,说这是明朝的日本短刀,简直是胡说八道。”
眼镜日本人问小胡子,这刀是真的吗?小胡子说,这把胁差不会有假,中国没有这样的锻造工艺。西装日本人问小胡子,这把胁差值钱吗?小胡子说:“比明朝的日本刀值钱多了,山口是宝历年间的一位制刀大师,曾经为桃园天皇打制过太刀,经他手制过的刀都刻着‘山口刀锻冶’,距今也有两百年历史了。”
就在这时候,一个半大小子跑过来,伏在安顺子耳边嘀咕了几句。安顺子脸上顿现惊喜色,从小胡子手中一把抢过短刀和刀鞘,跟着半大小子撒腿就跑。三个日本人好不容易相中一个物件,岂肯放过,跟在后面追了过去。半大小子和安顺子不快不慢,刚好够三个日本人能跟得上。半大小子和安顺子七拐八拐,经过一片空场子,几个农民模样的人正在挖地基。三个日本人追至此,已经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安顺子跑没了影。三个日本人弯腰扶着腿捯气儿,小胡子干脆坐在地上喘,刚喘匀了气,就开始咒骂安顺子。骂着骂着,小胡子突然收声了,他看到旁边挖地基的土堆上滚下了一个物件。他抓起物件擦掉泥巴,发现是一个钧瓷的笔洗。小胡子急忙掏出放大镜,对着笔洗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另外两个日本人凑过身来,问是真是假?小胡子头也不抬,说绝对的真货!这两个日本人一听是真货,急忙爬上土堆,发现五六个农民蹲在地基坑里,围着一堆瓶瓶罐罐,大多数还埋在土里,只露出个边边角角。西装日本人迫不及待地问农民:“你们出个价,我们全要了。”
其中一个农民说不行,给东家干活挖地基,挖出来的东西应该归东家。西装日本人掏出两封没开封的银元,扔给那个农民。西装日本人说:“东家把东西拿走了,你们一个子儿也捞不着。”
几个农民嘀嘀咕咕商议了一会儿,其中一个说:“俺们不懂行情哩,一会儿东家还要带人过来施工,等他给你们出个价吧。”
农民们说完,开始挖地基坑里的物件,大大小小的瓶瓶罐罐挖出来九件。小胡子说,你们把东西递上来给我看看。农民说不行,这是东家的东西,得让他来看。西装日本人又掏出两封银元丢了下去。农民还是摇头。三个日本人凑在一起,把口袋里的钱全部掏出来,数了数四百多块。西装日本人掂着手里的银元,对农民说:“加上那两百块钱,总共是六百五十块钱,全都给你们,我们把东西拿走,如果你们还不同意,我们就把宪兵叫来,你们一块钱也别想捞到。”
几个农民又凑在一起嘀咕,其中一个领头的说:“拿了钱,俺们就得走人,要不一会儿东家来了,俺们拿着钱也走不了。”
西装日本人说:“走吧走吧,拿着钱滚蛋。”
几个人爬上坑来,领头的农民是个麻子脸,他接过银元掂量了一下,一把夺过小胡子手中的笔洗,说:“六百五十块钱买这么一大堆宝贝,这个小玩意儿,俺就留着做个念想吧。”
说完,几个农民急匆匆散去,转头的工夫就没人影了。
躲在远处的罗良驹笑着对安顺子和半大小子说:“宋小六真是个抠门的种,钓上来鱼,还得从鱼嘴里把鱼饵抠出来。”
安顺子说:“宋小六还没生下来就骗他娘,在娘胎里待了十二个月。”
罗宝驹坐在院子里的老槐树下愣神,拿眼神直勾勾地盯着罗良驹给瓷胚挂釉,脑子里想的却是后母戊鼎。苟耀才穿着便衣闪进院子,罗宝驹问他脸上的伤哪里来的?苟耀才说前几天喝醉了酒摔的,他问罗宝驹着急找他什么事儿?罗宝驹说他明知故问,让他赶紧落实日本人把铜鼎藏在哪里。苟耀才嬉笑着说,问问樱子不就知道了。罗宝驹说樱子跟他哥哥来安阳的目的就是找这只铜鼎,她怎会跟我说实话?苟耀才说日本人防备心很强,铜鼎现在是宪兵司令部最高机密,外围人不可能得到确切消息。罗宝驹说,你尽管去打探,消息真假我自会辨识。苟耀才称是,说最近手头上比较紧。罗宝驹把早已备好的两封光洋递给他,说省着点花。苟耀才点头称谢,揣上钱走了。
苟耀才离开不久,敲门声又响起,老梁头从门房里钻出来,绕过影壁墙前去开门。影壁墙后传来樱子“嗒嗒”的高跟皮鞋声,罗宝驹起身迎她,她却被罗良驹手里的活计吸引,凑到瓷胎前东问西问,罗良驹一一作答。罗良驹对樱子没有偏见,他觉得这个女人做自己嫂子挺合适,至于她是不是日本人没所谓。罗宝驹一直拎不清自己和樱子的关系,他曾问过弟弟:樱子咋样?罗良驹说,日了人家就娶回来吧,咱家里该有个女人了。罗宝驹还是拎不清,说日了就娶,咱哥俩得把展春园的窑姐们都娶回家。罗良驹说,女人多了太吵,俺就娶小桃红一个就中。罗宝驹笑骂道,你个信球真要娶个妓女回来?罗良驹说,俺就跟小桃红得劲儿。
罗宝驹连拉带拽把樱子弄进屋,罗良驹冲着老梁头使个眼色,笑着说:“还没开春,我哥就撩骚哩。”
樱子甩开罗宝驹的手,说,你不怕弟弟笑话?罗宝驹说,我有正经事儿问你哩,见到铜鼎没有?樱子说见到了,在地下室陪着哥哥待了一天一宿快闷死了,所以才跑出来透透风。罗宝驹问,哪个地下室?樱子似乎发现自己走漏了口风,急忙岔开话题,说你对铜鼎还是死心吧,龟田次郎把这个铜鼎看得比命都重,一旦拿到手,任谁也别想夺走。罗宝驹看樱子嘴巴封得紧,就改口问道,你们兄妹俩把铜鼎上的事儿琢磨透了吗?樱子说还没有,龟田次郎已经申请日本陆军总部,可能要把铜鼎先运回日本,再慢慢研究。罗宝驹说,天下的贼都一个球样,得手后溜之大吉。樱子脸色涨红,辩白说,我和哥哥在进行史学研究,不是贼!两个人想着各自心事,一时间沉默下来。最终还是樱子先开了口:“我知道你不甘心把铜鼎交给日本人,我今天来特意告诉你,千万不要想着把铜鼎抢回来。”
“什么意思?”
“龟田君担心中国人硬抢,他让日本的爆破专家,在地下室通道里装满了炸药,如果发生意外,一颗子弹就能引发爆炸,地下室通道立刻会被封死。”
老梁头在院子里高声问道:“大少爷,樱子姑娘晌午留下吃饭吗?我也好出去买点像样的菜。”
罗宝驹还未来得及答话,樱子抢先回道:“梁叔,我不在这里吃,我还要给哥哥送饭去。”
樱子说完,不理睬罗宝驹,站起身来推门走出去。罗宝驹这才回过神来,随后跟出去送樱子。樱子走到院门口,突然“哎呀”一声,左腿一软摔在地上,罗宝驹急忙上前把她搀扶起来,发现樱子高跟鞋的鞋跟踩进一个土窟窿里。老梁头闻声,也从门房里钻出来,说:“是地老鼠,俺昨天就看见这个洞了,还想晚上在洞口放个老鼠夹子,没想到让姑娘吃了这个亏,都怪俺……。”
罗宝驹突然眼神一亮,把樱子的一只胳膊交给老梁头,说:“梁叔,你帮俺送送樱子。”
罗宝驹说完,转头就回屋了。樱子怒气未消,对着罗宝驹嚷嚷:“你什么时候陪我去天宁寺烧香?”
罗宝驹在屋里喊道:“二月初一去!”
樱子前脚离开,罗宝驹穿上外套,后脚也跟着出了门。老梁头问他晌午回不回来吃饭,罗宝驹头也不回,甩下一句:不回来吃了,你给二爷炖只鸡补补。罗宝驹出了门,叫上一辆黄包车,直奔马家胡同。他在胡同口辨认了一会儿,敲开一户人家,问是不是安阳商会葛会长家?开门的像是个女佣人,问罗宝驹找葛会长什么事儿?罗宝驹让她通告一声,就说罗宝驹前来拜见。女佣人进去不大一会儿,便出来引着罗宝驹进屋。
葛会长六十多岁,面色红润,体态微胖,留着三绺山羊胡子,一副有钱有势有教养的派头。原来,葛会长与罗宝驹他爹罗万通是朋友,葛会长家里古董甚多,经常找罗万通修补器物,两家人慢慢熟络起来。罗万通刚去世那几年,葛会长也会找罗良驹修补器物,世交关系继续维持着。后来,随着罗宝驹在安阳城的名声越来越大,尤其听说他经常半夜进盗墓贼家里,把盗墓贼挖来的货抢劫一空,葛会长就慢慢与罗家疏远了。原因是葛会长收藏的古董能顶半条通宝街,这些物件祖传下来的少,盗墓上来的多。如果按照罗宝驹的行事惯例,盗墓上来的物件都得归他,葛会长岂能不忌惮。近几年,安阳收藏界流行一个说法,说安阳有两条通宝街,一条是现有的通宝街,这条街上有一半是假货赝品。另一条通宝街,是葛会长和罗宝驹,两个人家里的物件加起来能顶一条通宝街,且件件都是真货精品。
进屋后,罗宝驹葛叔长葛叔短寒暄了几句。葛会长亲热地招呼罗宝驹落座,让佣人看茶。对于罗宝驹突然登门,葛会长心里有些诧异,因为两家已多年不走动,他心里七上八下打着小鼓。罗宝驹收起寒暄,脸色一正,说想问葛叔借样东西。葛会长心里暗想,果不其然,怕鬼鬼就到了。但葛会长还堆着一脸热络,说:“贤侄不必客气,看好葛叔家哪样物件,尽管拿走就是。就算是看好这座寒舍,葛叔也二话不说,明天俺就扛个铺盖卷走人。”
罗宝驹闻听此言,急忙起身肃立,说:“葛叔误会了,侄儿一肚子下水就算是狼心狗肺,也不敢到葛叔家里来耍信球,俺来其实就想借葛叔家里一张图看看,看一眼就立马走人。”
“一张图?”
“一张图。”
“什么图?”
罗宝驹重又坐下来,把声音放缓,说:“葛叔,日本人把安阳商会霸占后,你不是把商会里的家什都搬回家来了吗,那里面是不是有一张商会布局制图?”
葛会长说:“有,有,早些年破损了,是你爹帮着修补装裱的,也没问俺收工钱,说是一张纸片子不值钱。”
“收没收工钱,俺就忘了,侄儿只记得修补完了,俺爹打发俺给葛叔送到府上的,半道上俺还打开瞅了一眼,要不也不会知道有这么一张图。”
葛会长将信将疑:“侄儿要看这张布局制图?”
罗宝驹点了点头,神情颇为谦恭。葛会长的心放下了大半儿,因为他早已耳闻文官村出土了一件旷世神器,而且知道把舵人是罗宝驹,还知道罗宝驹亲自驾着马车,把这件国宝巨鼎送到了日本宪兵司令部。作为安阳首屈一指的收藏大家,愿意为葛会长提供这类信息的人,遍布整个安阳地界。罗宝驹突然登门造访,要借安阳商会的布局制图看,意图再明显不过了,他这是要对日本宪兵司令部下手啊。葛会长沉吟片刻,端起茶杯来,让罗宝驹不要着急,说他理解喜欢收藏的人,看到一个心仪物件,恨不得立刻占为己有的心情。罗宝驹说,葛叔意会错了,那件神器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就能吃得下,且不说文官村里的一帮股东们,现在除了日本人之外,国民政府、八路军,还有林虑山的土匪们,都想伸把手揩点油。葛会长说,既然都想进来分一杯羹,那贤侄准备跟谁合伙呢?罗宝驹说,包括葛叔在内,只要是出过力的,人人有份。葛会长笑道,葛叔年事已高,物欲寡淡,就不分贤侄这杯羹了。葛会长放下茶杯又说,如今大半个中国都是日本人的天下,那么大的物件,就算贤侄有本事把它从宪兵司令部弄出来,又能安置它去何处藏匿呢?葛会长接着说,如果谋划不周,只恐怕是误送了性命,也会牵连众位股东哩。罗宝驹笑了,说葛叔不要绕这么大的弯子,铜鼎的事儿既然由俺把舵,出了事儿当然由俺一人兜着,罗宝驹在通宝街上混了十二年,都知道俺不是溜肩膀,不管是大事小事,还是砍头掉脑袋的事,全由俺一个人扛着,绝不牵连一个外姓旁人。葛会长干笑了两声,显得有些尴尬,说既然贤侄敢作敢为,俺葛某也不是怕事之人。说罢,葛会长上前一步,捉住罗宝驹的手,说贤侄随我来。叔侄二人牵着手,出门穿过夹道回廊,进了后院。走到一间黑洞洞的厢房前,葛会长“哗啦啦”从腰间掏出一串钥匙,试了三把钥匙才打开门锁。拉开灯绳,罗宝驹看到屋子四周摆满了敞口大立橱,看样子都是安阳商会里的家什。葛会长一个橱子接一个橱子看着编号,随后打开其中一个立橱的上半拉门,在里面翻找。接着又打开下半拉橱门,从中抱出来一大摞纸卷,摊在一张榆木条案上,一卷卷打开来看。
“就是这张了。”葛会长把一张裱糊过的图纸平铺在条案上。
罗宝驹一眼就能认出来,的确是他爹曾经修补过的那张安阳商会布局制图,他问葛会长:“葛叔,商会里面有几个地下室?”
葛会长指着图上一座三层小楼,说就一个地下室,在这座楼下面,折深很大,有这间屋子三倍大小。罗宝驹说:“葛叔,侄儿到家里来看图的事儿,千万不能对第三个人提及,侄儿在此谢过,俺这就告辞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