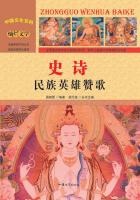醒来了就在一个大房子里面。下床想四处找寻,想找个人来问问。可是这个房子空旷得很,根本就没有人。
我走出房屋,回头看,这房子有四层楼高,几十个房间。我来到大门口,黑色的大铁门显得格外高大沉重,上面的锁也是坚不可摧。想爬到大门上翻过去,刚碰到铁门就感到一阵眩晕,颤抖得整个人仿佛往地狱里面下坠。我跪趴在地上,右手捂住心口,另一只手扶着地面急促地喘息,恍惚间,感觉一个人站在铁门外的不远处。抬头,不远处的道路边上,一棵大树后面站着一个年轻的男人,他穿着黑灰色条纹连帽衣服,帽子戴在头上遮住半张脸,他的眼睛是一双单眼皮眼睛,深邃而忧伤。此刻的我脑中迅速闪过很多幅类似的画面,上次的上次的上次,他也是站在树下,就这样的看着我。只不过很多次,他只是停留片刻就又走开了。
这时候,房子里面出来一个女人,看样子她是个主事的。她的头发当中有一撮金黄色的头发,身穿白色带有粉色波浪花边的长袍,微拢长发。原本美丽的脸上左半边是一大块被烫过的疤痕。她身后跟着一群大约7、8个穿着白色长褂的女人向我走来。她热情地笑着,过来直接搀扶我的手臂,说是外面寒凉,让我进屋子里面休息。拗不过好意,顺着群人的簇拥,向大楼里面走去。
女人给我找了一间大房间,甚至大得都让我感觉到有一些空旷了。靠窗的位置摆放了一张贵妃椅。女人和随从们离开了之后,我就躺在了贵妃椅上,思考着,我为什么在这里。当我双手叠放在胸口,就感觉不对,低头一看,我原来已经怀有好似9个月的身孕,看样子即将临盆。这该如何是好?
我突然感觉嘴里有沙子,开始往外吐沙子,几个,十几个,黑色的沙子,越吐越多,我有些忍受不了嘴里的感觉,直接张大了嘴巴,黑色的沙子就喷涌出来,越喷越多,没有停下来。黑色的沙子掉落到地上,转眼之间开始动了,原来是一个一个黑色甲虫,甲虫们翻了个身,爬走了,四散开来。这时我开始剧烈阵痛。已经生过一个孩子的我,知道这是要生产了。因为疼痛我开始忍不住叫出声音。那些个女人们听到了,一连串地跑过来,往屋子里面搬了好多东西,我就躺在贵妃椅上,主事的女人来了,宽慰我不要担心,我也没有任何办法,一切都等孩子出生了再做打算吧。
生产的过程很顺利,我都没有感觉到太疼,孩子就出生了。女人把孩子抱走了。是个男孩。
女人们都走了,让我好好休息。我看向窗外,又看到那个男人站在铁门外。我叹了口气,移目之间,看到玻璃上自己的影像,我开始恐惧得颤抖了,甚至比在碰到铁门的恐惧更加剧烈,因为就在我凝视之间,我看到我正在由一个年轻的女人模样渐渐变成一个66岁的老妇人的模样,满脸皱纹,头发稀疏几乎秃顶,低垂的眼皮几乎遮挡了眼睛,再一看双手,干枯布满老年斑与皱纹。刚刚明明还是年轻的模样啊。怎么……
我哆哆嗦嗦地往门外走去,打开门,这时候的走廊里面人群熙熙攘攘,摩踵擦肩,个个欢天喜地互相道喜。没有人在意我一个老太婆在人群间穿梭行走。到处一片欢歌笑语,何等的讽刺!
在往房子外走的过程当中,有几个人认为我是乞丐,给我手里塞了一些零钱,笑笑就走开了。我手里握着这些零钱,愤怒瞬间燃烧,可悲的是,为了以防各种万一我还是将零钱揣进了口袋。
我残喘地走到大铁门前,回头看,那栋房子里面,灯火通明热闹非常。人们似乎都没有注意到我。只有一个身影站在房门口内,一动不动的看着我。
这时候大铁门打开了,是放我走了。我毫不犹豫地迈出脚步。
树后面的男人走了过来,搀扶我。到了我此刻的这个年纪,看见年轻的小伙子,心里有多欢喜?我很开心,他拉着我的手,随心地漫跑,越跑越远,我感觉越来越有力气,渐渐地,青春也回来了,皮肤充满弹性,甚至比生了那个孩子之前还要年轻。
男人带着我来到远处的山,穿过葱葱的树林,跑上山峰,跑下山坡,又跑向另一座山峰,再跑下另一个山坡,在山与山之间的山谷中,一座散落在山谷中的村庄中停了下来。
我并不是第一次来到这里了。如果不是我再一次来到此地,可能我永远也不会记起。
这个村庄很小,居民不多,每家每户都是二层的小楼,在居民的房子边缘处,有一片西红柿地,现在这个时候,远远地望去,红红的西红柿果实累累,就像一个一个小灯笼悬挂在田野之间。
村中的中心位置是一个类似于休憩用的小广场,有一个圆形的用鹅卵石铺就而成的地面。男人带着我走到村子的小广场,告诉我围绕着广场的这几座房子都是他家的产业。在这里,围绕着广场的这几处明显是用来商用的房子。每一处房子前面挂着看不清楚的牌匾。
男人念叨着“还有时间,还有时间。”就带着我,来到那片西红柿地前面的一片空地,拉着我的手躺在空地上。也不说话,看着星光闪闪的夜空,我原来不知道,我是有多爱这繁星的夜空的,宁愿时光就此停滞,永不离去。
天逐渐快亮了,有鱼肚白色天空出现,广场那边有公交车的声音传来。男人带着我来到公交车站,我上了车,掏出兜里所有的零钱,只有我一个乘客,男人目送我远去,没有挥手。我一直看着他,直到再也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