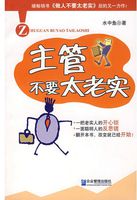这里就像是冰河时代。黑夜漫长寂静并充满危险。白天有一轮如现在的月亮的同等亮度的太阳挂在天空。是太阳活动减弱了还是人类过度消费地球资源造成的已经无从追问。这里没有万物,没有生机。到处都被厚厚的白雪覆盖着。人们早已经习惯了寒冷,三五一群的聚居相互照应。
我生活在一个村子里。丈夫是一个杀猪的屠夫。在当时如果是一个杀猪的,要比别人家生活条件更好一些。起码能经常吃到猪肉和内脏什么的。
丈夫是一个强壮寡言的男人。整天穿着油渍渍的衣服,一双破了洞的鞋在街上等着买猪肉的客人前来。他总是反戴着一个硬硬的皮质头罩,本来在眼睛和嘴巴的地方露出几个窟窿,因为他反着戴,窟窿里面露出的并不是眼睛和嘴巴,而是长长的黑色的毛发支出来,一撮一撮的,过了好几天总也不知道他到底长得什么样子。对他我还是惧怕的。有一天我看见他把面罩转向前面,可是让我心惊的是,露出来的依然是一撮一撮的黑色毛发。
没有光合作用,就没有食物。获取食物是非常昂贵的。很多人家食不果腹。我们家还好,总有些有钱人会来买肉,而我们家几乎每天都会有卖不出去的猪下水可以吃。也有时候猪肉也会剩下,但是我们不太舍得吃。村子里面总有来来去去的乞丐,乞丐会不分时候地来乞讨。即使是半夜里也有“咚咚咚”的敲门乞讨声。谁也不知道如果现在不吃上一口东西,下一秒死掉的会不会是自己。
我跟丈夫几乎是没有语言交流。有一天,家里来了一只雪白的猫,跳在灶台上不肯离开。我正想着它是不是饿了,刚要上前去抱那只猫。门就被野蛮地从外面打开,丈夫进来一下子把白猫吓得“喵——”的一声炸了毛,一跳老高,我伸手要去接住猫,丈夫一个条件反射从腰中拔出剔骨刀横手一挥。“啊——”的一声我的惨叫随即而出。我右手的四个手指被一下子齐刷刷地切掉了。鲜血不断地涌出来。我并没有去医院,把四个指头捡起来想自己缝合上,缝上了又掉,掉了又缝上……
我失去了四个手指,但是我并不难过。一天晚上,我看到有一个老妇人竟然为了一些肉,主动献身我的丈夫。当我听见声音,悄悄走过去查看的时候,正看到丈夫与老妇人交合的一幕。我只是又悄悄地回房沉沉睡去。我还是不难过。
我在村子里面寻了一个比较漂亮的二十岁出头的女孩带回家,作为伺候丈夫房事的女人,丈夫没有说什么话,但是我能看得出来他还是比较满意的。也好也好。从此以后不必相互忠贞。
时间一点一点地过去了。我在家中渐渐失去了地位。引狼入室也许就是像我这样吧。有一天晚上,丈夫冲到屋子里,用那把杀猪刀向我的胸前刺来,还没等我回过神来,我的不知道都有些什么内脏就被他摘了出去,一转身走到厨房,直接丢在了一锅沸腾的汤里面。桌上两副碗筷格外显眼。
我怕是活不成了,拖着巨疼的身体向门外爬去。丈夫看着我,即使看不到他的眼睛我也知道他的眼神有多冷。那个已经成为他的妻子的女孩,守在餐桌前。我就不去看她了吧。
丈夫可能并不相信我能活着爬出门口。当我来到门口,看到一个赶着驴车的人,他看着我,说时迟那时快,一个箭步,把我抱上车,拿出一个1.2X0.1X0.15米的长匣子,说了句什么,我一下子就进到了那个匣子里面。没想到里面的空间如此之大,感觉不到边际。
驴车剧烈地摇晃,如逃命一般。大约半天左右的时间驴车停了下来,那人把匣子打开,让我出来。并且安慰我,说会带我走的。还没有5分钟的样子,后面远远地看着丈夫带着人群追了过来。
那人回头瞥了一眼,紧接着眼前的山地开始剧烈晃动,时不时的有地面塌陷下去,接着整个驴车就跟着陷了下去。
等我醒来,我已经被换上了明黄色的袍子。走出房间,眼前就是一个亭子,亭子边上即是万丈的悬崖。头顶是厚重的泥土,这里没有太阳,但是依然看得清。身后的不远处也有一个穿着跟我一个颜色的袍子的男人站在那里,他没有向前走,我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