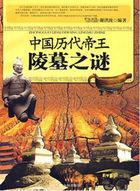张夜抓狂了,没有地契,后续的所有活动都要费力很多,如果要组建团练,吃喝用都要银子,这些银子还不得张夜出,失去了地主这个身份,张家连普通的佃户都不如,就不用提组建团练了。
张虬龙紧紧盯着坛子,一脸震惊道:“真是好宝贝,这味道!闻一口就醉了。”
“不就是一罐酒吗?”张夜还在烦躁。
“一罐酒?”
张虬龙声音提高了八倍,“整个洪叶乡找不出第二罐这样的酒,这可是清酒,还是琥珀色的。”
张夜看着张虬龙激动的样子有些好笑,这酒放现代也就是一般的白酒,可是唐朝时还没发明蒸馏技术,酒水都在坛子里酿,酿好了倒出来直接喝,这种酒度数低而且混浊,上面有各种漂浮物,所以被为浊酒,范仲淹的词里曾写到:“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
范仲淹喝的就是这种普通的浊酒。
至于过滤过比较干净的酒水被称为清酒,已经是比较高档了,如果酿的时候比较注意保持酒曲和酒液的纯度,酿出来的酒会呈现黄色,最好的酒是琥珀色,和现在的黄酒差不多,李白有诗云:“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可见李白的口福比范仲淹要好。
这种琥珀色的清酒,相当于典藏版的茅台,如果拿出去,不知道有多少人要打破脑袋。
张夜想通此节,心里终于好受点,起码还值点银子,实在不行卖了它。
张虬龙腆着脸道:“夜哥,这酒你一定要让我尝尝,否则我会难受死的。”
张夜想这酒奇货可居,可不能让他喝的太容易了。
见张夜不答,张虬龙索性拍了拍胸口,“以后用得着我的地方,我绝不二话,这样行吧!”
张夜嘴上不说,心里已经乐开了花,一坛酒如果能招来一条大汉,这可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
张松材开玩笑道:“龙哥看见好酒比看见娘还亲。”
谁知张虬龙是个孝顺的,当场黑了脸,喝道:“放你的狗屁,天大地大娘最大,拳头第二,酒第三。”
“没有娘,哪有我,没有这双拳头,哪来的酒喝。”
张松材被骂了一顿,也不敢吭声,张夜替他解围道:“虬龙话糙理不糙,有了这身武艺,天下哪里去不得,何愁没有酒喝。”
在旁边一直没有说过话的张光越突然开口道:“龙哥的功夫当真了得,那日里两个兵匪进村,烧杀抢掠,大家敢怒不敢言,只有夜哥不惧杀了一个,但是另一个却是被龙哥杀的。”
经他一提,张夜果然记起,那日是有两个兵匪的,自己只杀了一个,还有一个在外屋,不知怎么把这件事忘了,原来是他杀的。
如果另一个兵匪不死,张夜和梁画早就命丧黄泉了,如此说来自己还欠他一份人情。
张虬龙瞪了张光越一眼,似乎在嫌他话多,“这件事没几个人知道,你倒是清楚的很。”
张光越见他不悦,当即闭口不言,拉出一副苦瓜相。
“哇,原来是龙哥干的”,张户叫了起来,“大家都传张夜连杀二匪,就像被鬼附体了,我就说哪有那么厉害。”
张夜满头黑线,心想这话怎么听着那么别扭。
“原来受了恩却不知道,实在该死。”张夜一拱手。
梁画也向张虬龙福了一福,说道:“先前不知,多有怠慢,谢过张兄救命之恩。”
张夜眉头一皱,竟然连梁画也不知道这件事,别人不知道可能是误传,但是梁画这个当事人也不知道,就只能说明一件事:那就是张虬龙在刻意隐瞒这件事。
这是很光荣的事,他为什么要隐瞒呢?
难道是怕安匪报复?并不像啊!
张夜想不明白,余光看了张光越一眼,张光越低着头,看不见表情。
既然张虬龙不想说,张光越却把这件事抖了出来,这其中恐怕也有问题。
张虬龙打了个哈哈,对梁画说道:“小嫂子严重了,不值一提,不值一提,真要谢我就把这坛酒送我吧。”
“不给。”张夜微笑道,“不过可以请你喝,自古宝剑赠英雄,好酒配酒鬼,你又救了我的命,理当请你。”
“你们读书道理多,我不懂,有的喝就好。”张虬龙哈哈大笑,“我去山上打些下酒菜,回来咱们痛饮。”
几人就要告辞。
张夜又道:“还有一件事,希望各位帮个忙。”
张虬龙大咧咧道:“什么事,只管开口。”
张夜黯然道:“老天无眼,先生不幸遇害,后天就是头七了。咱们都是先生的学生,我希望各位都去祭奠一下,以告慰先生在天之灵。”
众人看了一眼梁画,都道:“这是自然,一定去。”
张夜又道:“周围村的同窗也烦劳大家代为通知。”
张光越点点头:“夜哥放心,跑腿的事交给我就行。”张柏林笑道:“你再能跑,自己也忙不过来,莲叶村那边交给我吧,我比较熟。”
几人商议定了,这才离去。
梁画从张夜手里接过酒坛,用绸布重新扎好口,蹲下身子放进筐子里,等她站起来的时候张夜发现她的眼角有了泪水。
“你怎么了?”张夜拉过梁画的小手,关切的问道。
梁画小声啜泣道:“谢谢你,我爹爹一定会高兴的。”
张夜心中有点愧疚,他召集同窗来其实除了祭拜先生,还有别的事,他准备作一个煽动性的演讲。
学生虽然不是中坚力量,但是学生觉悟高,一身热血,近代的革命运动最早都是学生发起的,所以张夜初步计划鼓动学生,在唐朝发起一场保卫家乡的革命运动。
在被害的先生墓前讲演,这个时机再好不过。
“好了,别说这么见外的话。”张夜刮了刮梁画小巧的鼻子。“先生要知道我这几天把你惹哭了这么多次,肯定要打我手心了。”
梁画破涕为笑,道:“该打!”
张夜笑道:“‘你舍得吗?”
梁画红了脸,低着头不说话,气氛顿时有些暧昧,张夜想,昨天晚上那么大胆的告白,今天怎么就害羞了,小丫头终究是脸皮薄。
昨天被表白,有种被逆推的感觉,张夜可是个大男子主义者,现在好像重新掌握了主动权,这让张夜感觉很好,看了看天色,张夜对梁画说道:“既然宝贝挖到了,那咱们走吧。”
梁画抬起头,看了一眼张夜,又看着篮子里的这坛酒问道:“这算什么宝贝?”
张夜于是把父亲和他说的话讲了一遍,又道:“其实我也不太明白,我还以为会是地契或者银两之类的,不过就挖出了这么个东西。”
梁画听完,抿嘴笑道:“原来是这样,只怕你挖错了东西。”
“怎么讲?”。
“你想想,伯父不喝酒,你也不喝酒,他怎么会留坛子酒给你,虽然这坛子酒值钱,也要卖出去才行,还不如直接留点银子。”
张夜点点头,“有道理,你继续说。”
梁画笑道:“所以啊,你恐怕挖到了别人藏的东西,就把它当成了伯父藏的宝贝。”
张夜越听越有道理,又看了看梁画,好像不认识她似的,这小妮子什么时候这么聪明了?
梁画被看的不好意思,问道:“怎么了?我说错了?”
张夜赞扬道:“没错,说的很好。”索性直接问道:“那你觉得应该藏在哪里?”
“柴房。”
“为什么?”
“因为柴和财的音是相通的,伯父也是想讨个彩头吧。”
古人的思维可能就是这样,张夜安慰自己。
说干就干,张夜寻到柴房的位子,奋力挖了起来,不多时,果然挖出一个铁盒子,打开来一看,张家四十亩地的地契全在里面,上面盖着官府的大印,还有一锭大银,足足有五十两。
发了,发了,张夜一下子跳了起来,兴奋的拉过梁画来在脸上亲了一口,赞道:“我的好媳妇,真是又聪明又能干。”
梁画被他突然的大胆举动吓了一跳,一手捂着被亲过的脸颊,居然有些不知所措。
两人虽然要好,也互相表白心迹,但是如此亲密的举动还是第一次,梁画心里既害羞又高兴,还隐隐有些害怕,他这么逾礼,我又不吭声,他会不会把我看的轻了,心中百味杂陈,实在难以描述。
等梁画终于忍住了羞涩抬头看时,张夜正站在刚挖出的泥土堆上,高举着地契对着太阳,此时的张夜正在筹备一件大事,更显得踌躇满志,神采飞扬。
梁画突然有种奇怪的感觉,某一刻他好像完全属于自己,而另一刻的他却无法把握,看似触手可及,实际却是遥远如隔天堑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