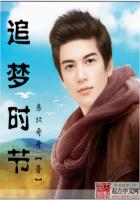我带着简单的行装,头也不回地和文上了一辆返程出租车。没错,都带着忍够了的憎恨。车上还有两个一对互相搂在一起的校服生,从名条上看,不是高三的。在这样的学校,看着挺新鲜。
“龙,你家在哪?”文坐在副驾驶回头问着。“新柳那面,你呢?”我望着车窗外路两旁金黄的水稻田。“我家在当代那。”
我眼睛一亮:“那不远啊!十一打算怎么过?上网吧么?”
“我在家上,回家你爸做什么好吃的?”文笑着问。
我却沉默了,每每说起我家,不管多开心的脸色都会马上沉下来,然后沉默不语一段时间。文看我不愿说,也沉默地望着路边的车马牛羊。
文先到了家,透过车窗一个手势,意思电话联系。双手抄着兜潇洒地走了。我留恋地望着这个日韩范儿美型男。
进了幽暗的无人的自己的窝,扔下行李就到彩票站找爹。“爸,我回来了,给我做好吃的!”20岁的大小伙子,站在乌烟瘴气的彩站门口,大声喊着。
“爸转过头一看是我,笑呵呵地扔下报纸甩手跟我出去了。”
“爸,我成绩上来了,提高了200名”。
“哎呀,挺好!怎么感觉你瘦了。”我爸看着穿校服的我和以前的吊儿郎当明显不一样了。
“东港那破菜,要么死贵,要么一点油水都没有。”我抱怨着附带着夸张的面部表情。
“怎么吃得不饱?”“吃饱倒是能吃饱,就是没什么味儿。清淡,太清淡!”我摇着头。“想吃什么说,我这就给你上市场买去。”我爸就乐意给我这么个大儿做好吃的。“软炸肉,鸡丁,还有偏口鱼……”
“这么多,你能吃了么?吃不了都放坏了。”爸提示着以前经常做了一堆就吃了一点。我挥着手不耐烦:“来来来,做多少都吃了!”
“我先给你买点里脊,明天再做鱼。”爹背着手走向市场。
我不满意地回了家,翻着电话本,都已是各奔东西上了大学。算了不找了。能见面的只有文。
“文,你干什么呢?”
“我在发廊呢。”我想起了文飘逸的发型。“发廊在哪?我过去找你。”甩上门,跟刚回来的爸留了一句:“我去剃头,菜做好放着就行,不用等我!”轻盈地朝发廊而去。
一个鼻子有点大的女老板把我迎了进来,又接续忙着手上的活。文正坐在她手下。“这是我同学,好好帮他设计设计。”文介绍着。“好,不过得稍微等一会,前面还有两个。”老板娘解释着。“没事,我有时间。”拿起一本杂志就胡乱翻着,边看,几个人边唠起了东港的奇葩见闻。让我耿耿于怀的就是梦的老板——流浪汉。突然对以前的女鬼班主任泛起无穷无尽的爱意。
拿出了电话不假思索地拨了一个号码,这是当年每次借故请假包宿时专用的号码。“喂,老师吗?”电话另一头再次响起温柔的声音“你好,请问是哪位?”
“我是龙。”
“啊,是你呀,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
“老师我想你。”一句话,涌出控制不住的泪水,就像受欺负了孩儿找到妈一样的感觉。
我拿着电话,进了里屋,坐在个没人的地方。“老师,东港二中……”,“我当年要是……”,“现在成绩……”,“可是语文老师太次了,上课……他半个月讲的,赶不上你一节课讲的多。以前同学们都说你课讲得好,没想到这么好……”原班主任红在电话另一头一直耐心地聆听着。足足一个多小时,一直到电话没电,也还有话没说完。
平复着心情,长出了一口气,抹着湿了又干的眼睛,走了出去。文已经走了,屋子里都空了。
坐在了镜子前:“走了也没打声招呼。”自言自语。
“我们都没好意思进去打扰你。”老板娘挺着个可爱的大草莓鼻子笑着。似乎他们都听到了电话里的内容。掏出了好奇:“东港二中真的……”
人,被泪水洗过之后,就会更加坚强。
沉默着理完了发,沉默着离开了发廊,低头走在回去的路上,习惯性地看了一眼路边随处可见的网吧,又低下了头。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到了家独自吃着老爸留好的饭菜,也越发心里不是滋味,想起了高一高二两年父亲顶风顶雪送饭的不易。我的眼泪随着饭菜一起咽进了肚里。